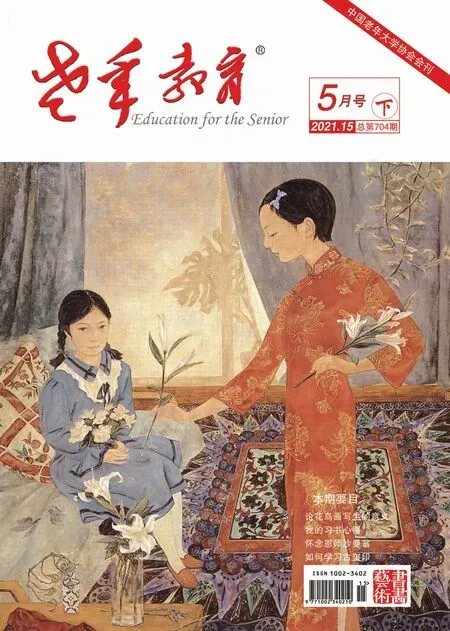孫過庭《書譜》 書學理論與寫法分析(十二)
□ 楊 勇
釋文:
所謂涉樂方笑,言哀已嘆[107]。豈惟駐想流波,將貽啴噯之奏[108];馳神睢渙,方思藻繪之文[109]。雖其目擊道存[110],尚或心迷義舛。莫不強名為體,共習分區。豈知情動形言[111],取會風騷之意[112];陽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113]。既失其情,理乖其實,原夫所致,安有體哉!
夫運用之方,雖由己出,規模所設,信屬目前。差之一豪,失之千里。茍知其術,適可兼通。心不厭精,手不忘熟。若運用盡于精熟,規矩于胸襟[114],自然容與徘徊,意先筆后,瀟灑流落,翰逸神飛,亦猶弘羊之心,預乎無際[115];庖丁之目,不見全牛[116]。嘗有好事,就吾求習。吾乃粗舉綱要,隨而授之,無不心悟手從,言忘意得。縱未窺于眾術,斷可極于所詣矣[117]。(橫線處為原作缺失部分)
譯注:
[107]涉樂方笑,言哀已嘆:語出陸機《文賦》:“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嘆。”

《書譜》(局部)唐·孫過庭
[108]駐想:凝思。流波:流水。啴(tān):和緩。噯:作“緩”。啴噯:即柔和舒緩。“駐想流波,將貽啴噯之奏”化用伯牙鼓琴的故事,《列子·湯問》:“伯牙善鼓琴,鐘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鐘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鐘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鐘子期必得之。”
[109]睢:水名。渙:亦水名。《文選·陳琳〈為曹洪與魏文帝書〉》:“蓋聞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游睢渙者,學藻繢之彩。”李善注:“《陳留記》曰:襄邑,渙水出其南,睢水經其北。《傳》云:睢渙之間出文章,故其黼黻(chī)繡,日月華蟲,以奉于宗廟御服焉。”李周翰注:“睢渙,二水名。其處人能織藻繢綿綺,有游于此者,亦將學其風土所為也。”藻繪:形容文章辭藻華麗。
[110]目擊道存:語出《莊子·田子方》:“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王先謙集解引宣穎曰:“目觸之而知道在其身,復何所容其言說邪?”此處形容王羲之書法境界高深。
[111]情動形言:《詩·序》:“情動于中而形于言。”指情感是語言的發啟,言語是情感的表達。感情是內容,言語是形式。
[112]風騷:指詩文與才情。風,指《詩經》之“國風”。騷,則指《楚辭》之“離騷”。
[113]陽舒陰慘:原意為陽氣舒展而陰氣慘淡。“陽舒”借指舒暢的心情和寬松的氛圍,“陰慘”借指愁苦煩惱的心情和壓抑的氣氛。漢張衡《西京賦》曰:“夫人在陽時則舒,在陰時則慘,此牽乎天者也。”“陽舒陰慘”,在此處形容書法用筆的舒展和收蹙(cù)。
[115]弘羊:桑弘羊,西漢洛陽人,出身商賈。武帝時為治粟都尉、大司農、遷御史大夫,創立食鹽、冶鐵、酒類等。其考慮事情細密周到。《漢書·食貨志下》:“弘羊,洛陽賈人之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
[116]庖丁之目,不見全牛:《莊子·養生主》有曰:“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嘗見全牛也。”
[117]詣:造詣。極于所詣:指書法達到所追求的最高水平。
譯文:
所謂慶幸歡樂時笑聲溢于言表,傾訴哀傷時嘆息發自胸臆。豈非志在流波之時,始能奏起和緩的樂章;神情馳騁之際,才會思索詞藻華麗的文章。雖然眼見即可悟出道理,內心迷亂難免議論有誤。因此無不勉強分體定名,區分優劣供人臨習。豈知情趣有感于激動,必然通過語言表露,抒發與《詩經》《楚辭》相同的旨趣;陽光明媚時會覺得心懷舒暢,陰云慘暗時就感到情緒郁悶。這些皆緣于大自然的時序變化。那種違心作法,既背離書家意愿,也與實情不符。從書法原本來說,哪有什么體裁呢!
對運筆的方法,雖然在于自己掌握,但整個規模布局,確屬眼前的安排要務。關鍵一筆僅差一毫,藝術效果便可相去千里。如果懂得其中訣竅,便可諸法相通。用心不厭其精,動手不忘其熟。倘若運筆達到精熟程度,規矩便能熟解于胸,自然就會縱橫自如,意先筆后,瀟灑流落,筆勢飄逸神飛了。就像桑弘羊理財(精明干練,計劃周到),心思籌措在于各方;又似庖丁解牛(熟知骨骼,用刀利索),眼中無牛了。曾有愛好書法者,向我求學。我便簡明舉出行筆結體的要領,隨后教授他們實用技法,因此無不心領神悟,默然領會。即使還不能完全領略各家所長,但亦可達到書法探索的最深造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