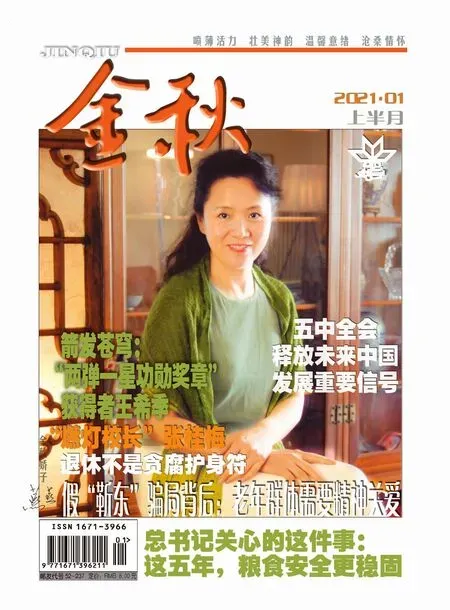我的父親母親
※文/韓亞維

我母親19歲嫁給我父親時(shí),父親還在內(nèi)蒙古當(dāng)兵,一年回家探一次親。我們家那時(shí)家大人多,規(guī)矩多,太祖父去世早,由太祖母一人管家,我爺爺兄弟7個(gè),每戶都有十幾口人。家里男勞都下地干活,女人除了干些簡(jiǎn)單農(nóng)活之外,主要是管娃、做飯。女人燒鍋?zhàn)鲲垥r(shí),太祖母就坐在炕上監(jiān)督整個(gè)做飯過程,你搟面撒得面撲多了,鍋底柴搭得多了,做飯時(shí)說(shuō)尷話了,唾沫星子濺到鍋里了,她都看得一清二楚;誰(shuí)犯下錯(cuò),輕則挨罵,重時(shí)太祖母會(huì)順手一拐拐打過去。我母親性格好,愛干凈,人勤快,話也少,還給我們這個(gè)缺少女子娃的大家庭里先后添了長(zhǎng)重孫女、長(zhǎng)重孫子,所以太祖母比較喜歡她。
父親在內(nèi)蒙古當(dāng)兵時(shí),因?yàn)楹脤W(xué)被部隊(duì)安排去重慶通信學(xué)院上學(xué),畢業(yè)后很受團(tuán)首長(zhǎng)器重。然而這時(shí)父親收到太祖母病危的電報(bào),父親在他同輩兄弟中排行老大,每次探親回家時(shí)都會(huì)把在部隊(duì)掙的錢、布票帶回家交給我爺,我爺則照數(shù)上交給太祖母。太祖母感覺自己老了需要有人幫襯,于是在父親準(zhǔn)備返回部隊(duì)時(shí),臥病在炕的太祖母流淚拉著父親的手,不準(zhǔn)父親走,無(wú)奈之下父親只好答應(yīng)太祖母回部隊(duì)后申請(qǐng)轉(zhuǎn)業(yè)。當(dāng)時(shí)團(tuán)首長(zhǎng)說(shuō)出了想提拔父親的想法,讓父親好好考慮一下再做決定,但父親還沒來(lái)得及考慮,家里又一次發(fā)來(lái)太祖母病危的電報(bào),父親覺得在部隊(duì)不能安心履職,這樣下去,有負(fù)于國(guó)家、首長(zhǎng)和戰(zhàn)友,故在幾天痛苦的思想掙扎后,最終向首長(zhǎng)遞交了轉(zhuǎn)業(yè)申請(qǐng)。
父親從部隊(duì)轉(zhuǎn)業(yè)回家沒幾天,太祖母就召集家門中所有男丁開了分家的會(huì)。大爺、二爺已去世,我的爺爺排行老三,太祖母說(shuō)自己老了,沒有幾天了,老七是聾啞人,娶了有點(diǎn)精神病的婆娘,她擔(dān)心老七沒人管,她要帶著,看誰(shuí)想跟她過。這時(shí)4位爺爺沒有人說(shuō)話,我爺只好說(shuō):“媽,您要不嫌棄就跟我過吧”。我父親接著說(shuō):“如果大家沒意見,今后我和我的兄弟5人就養(yǎng)活太婆、爹、娘,還有七爸、七娘”。父親回到家,向母親說(shuō)了分家的事,原以為母親會(huì)說(shuō)一些埋怨的話,沒想到,母親卻非常平靜地說(shuō)這是預(yù)料中的事。分家后的日子更難過,一大家老的老、小的小十幾口人,勞動(dòng)力卻沒有幾個(gè),但家里仍然保持著以前太婆的生活習(xí)慣,侍奉她老人家洗臉、梳頭、穿衣服、收拾房間,不管家里其他人吃什么,太婆炕上掛的那個(gè)饃籠子里總是有烙的或蒸的白饃,吃飯也總是先給她老人家舀第一碗稠的。太婆于1968年壽終正寢,享年93歲。
父親轉(zhuǎn)業(yè)后一直在縣民政局工作,他在辦公室經(jīng)常要接待一些需要救濟(jì)的貧困群眾,父親對(duì)每個(gè)來(lái)辦事的人都熱情和藹,落了個(gè)“老好人”的名聲。但他教育子女時(shí)卻有著軍人的要求,兒女在做人、做事甚至吃飯時(shí)都有許多“不準(zhǔn)”。我是家里的老小,父親對(duì)我相對(duì)寬容些。兒時(shí)記憶里,總是盼著父親回家,每到周末,我總是提前在門口等著父親,因?yàn)楦赣H自行車前面那個(gè)皮包里總藏著我期盼已久的桃酥、餅干或大白兔奶糖。平日里,母親一人拉扯我們兄弟姐妹4人。天不亮母親就去河里撈魚草,等我們起來(lái)上學(xué)時(shí),看到母親拉著滿車魚草正進(jìn)院門。母親白天在生產(chǎn)隊(duì)掙工分,晚上還要抽空為一家大小縫制衣裳鞋子。
為了改善家里的生活條件,母親很早就做起了“小生意”。親戚承包了村里的竹園,竹子砍了,他們不要帶葉的竹枝,父親和母親就把連葉竹枝拉回家來(lái),編成掃帚拿到集上賣。父親的戰(zhàn)友幫忙聯(lián)系紡織廠,把廠里裁剪下的邊角廢料買回來(lái),綁成拖把拿到集上賣,還賣拖把棍、棉線和秋衣等等。為了不影響我們學(xué)習(xí),父母從不讓我們參與勞動(dòng),總是說(shuō)我們的任務(wù)是學(xué)習(xí)。有時(shí)候,為了趕做定制的拖把,父母總是熬夜干到很晚。父親做任何事,總是把誠(chéng)信放在第一位,他做拖把從不偷工減料并講究質(zhì)量。由于拖把質(zhì)量過硬,時(shí)間長(zhǎng)了,一些單位、飯店和父親簽訂了長(zhǎng)期供貨合同。當(dāng)然,我們的生活也不斷得到改善:吃白饃,穿新衣,還有新書包、文具盒等學(xué)習(xí)用品。在我上小學(xué)三年級(jí)的時(shí)候,父母用積攢的一點(diǎn)積蓄在縣城買了莊基地,然后我們一家都搬到了縣城。一個(gè)偶然的機(jī)會(huì),母親接手經(jīng)營(yíng)了一間服裝門店,從此讓我們家的生活一步一步地好了起來(lái),也讓母親徹底打消了再搬回村里(因?yàn)榭h城的生活開銷既多又大)去生活的念頭。
父母生活一輩子,我們從未見過他們爭(zhēng)吵和打架,印象中再苦再難的日子里,也未見過父母抱怨和不滿,他們總是想方設(shè)法積極地面對(duì)生活,用勤勞的雙手改變困境,用母親的話說(shuō)就是:好日子誰(shuí)都會(huì)過,但要把苦日子過甜,那才是真本事。
2000年5月,父親被查出肺癌早期。在父親住進(jìn)西京醫(yī)院的同時(shí),我們四處找民間中藥偏方,一切能想到的我們都去做,祈求上蒼不要帶走我們的父親。父親得知病情后很坦然,說(shuō)他會(huì)像對(duì)待敵人一樣和病魔作斗爭(zhēng),他同病魔奮戰(zhàn)了6個(gè)春秋之后才最終倒下。父親走后,我們姐妹都爭(zhēng)相著要與母親同住,但母親卻丟不下自己的本宅。于是,大姐總是“騙”著讓母親作伴旅游;哥哥經(jīng)常把吃的用的整筐整箱地給母親買回家;二姐每隔兩天就回母親那兒一次,我也總是盡量抽時(shí)間回家看望母親。扶貧工作開展后,我因?yàn)楣ぷ髅Γ3<贝掖一丶铱纯茨赣H就走了。有一次晚上回家看母親,說(shuō)起了幫貧困戶申請(qǐng)危房補(bǔ)助蓋了房子、辦理慢性病卡、聯(lián)系就業(yè)等事情,母親聽后高興地夸我是行善。后來(lái),母親還把我們姊妹給她買的營(yíng)養(yǎng)品帶著與我一起去看望和慰問貧困老人。
父母在,如鳥兒有巢,父母去,如風(fēng)箏斷線。現(xiàn)在母親就是我們的精神支柱,我們則是母親的生活依靠。有母親的每一天,對(duì)我們來(lái)說(shuō)都是風(fēng)和日麗陽(yáng)光燦爛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