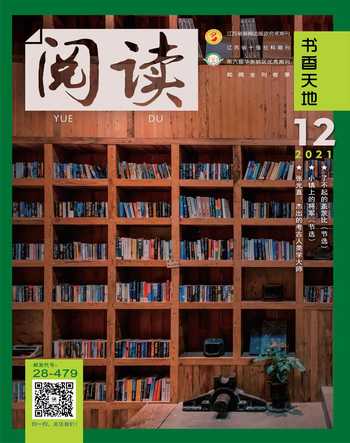我的兄弟王小波
王小平

冥想的小波
小波從很小的時候開始,就經常閉目塞聽,露出一副呆呆的表情,站在同齡兒童中間,十足是個異類,使人懷疑他的腦袋是否有毛病,連我姥姥和我媽都管他叫“傻波子”。我經常注意觀察他,發現在他發呆的時候,兩眼會固定地凝視一個地方。此時大聲叫他名字都沒反應,必須推他一把才能把他喚醒。在喚醒之后,問他剛才想了些什么,他總是語焉不詳,或顧左右而言他,總之,他這部分心理活動從不向他人公開。我猜他是像和尚打坐一樣陷入了冥想,而且他的智力沒問題。因為他在不發呆的時候,無論思想和行為都屬正常。但一個幾歲的孩子也會冥想,這未免有點太過驚世駭俗,所以我沒敢告訴別人,怕人家把我也當成神經病。
小波一副寡言少語的脾氣,和我們在一起時倒還有說有笑,到了幼兒園,就顯得不合群,喜歡一個人在一邊呆呆地想心事。當時流行的說法,是把孩子叫做天真活潑的祖國花朵,這一叫法嫩得讓人有點不好意思,對于小波更是全不相宜。站在幼兒園的孩子中間,他目光呆滯,像一個古怪的異類。幼兒園的老師告訴我們,他經常一個人蹲在籬笆下面呆呆地往外看,一蹲就是半個鐘頭,還問我們他是不是有什么毛病。我聽了心里很別扭,心想說你們為什么非得讓孩子們湊在一起,沒心沒肺地亂蹦亂跳,小波喜歡想心事又招誰惹誰了?難道小孩就非得心智簡單,像個單純的傻瓜才算正常?為什么小孩就不能想心事,甚至構造自己的獨特內心世界?我想小波的智力應該是毫無問題,或者比那些正常的孩子更高一籌也說不定。大人們老是低估兒童的心智。
作詩的年代
在我上三年級的時候,正趕上全民作詩的時代。我經常看人大校刊上刊出的大人寫的詩,覺得呆里呆氣的,一點不見出色。有一次,老師讓我們也寫些詩,放在黑板報上。我一時心血來潮,仿照人大校刊那些詩的樣子,作了四首十六字令,覺得比大人寫得一點不差,就交了上去。這些詩完全是虛張聲勢的套話,沒有真情實感,所以后來全忘了,只記得有一首的結尾是“革命烽火赤”之類。沒想到又被老師叫到辦公室去,審問了一通,問我是不是從報紙上抄襲的,使我感到極大的屈辱。
這段作詩的事情我跟小波閑聊時提起過,為此沒少受到他的嘲笑。他把這段大躍進年間寫詩的故事寫到了自己的文章里。按照他的說法,有一天他在廢紙箱里偶然發現一篇我的詩作。這首詩被糟改為:“共產主義,來之不易,要想早來,大家努力。”他看完之后就毫不猶豫地用它擦了屁股。這使我有一點忿忿不平的感覺,因為我的詩再不好,也沒差到那個程度。再說當時朝野的詩人滿坑滿谷,無非也就是我的水平,憑什么他們的詩就可以登在報紙上,從收音機里放出來,而我的詩就只能填進茅坑?這個道理找誰說去?回想起那年月作詩的事,完全是一筐子笑話。
小波肥碩的耳朵
有一天,小波自己跑去看煉鋼,一不小心被絆倒,摔倒在煉出的鋼塊上,把胳膊割了個大口子。那個口子相當深,割透了皮下脂肪。這是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身體內部,沒想到竟是這樣一些白花花的東西,大大吃了一驚,嚇得連哭都忘了。
于是被爸爸拎著耳朵上醫院。不知從什么時候起,手拎耳朵就成了我爸爸接觸小波身體的主要方式。有一天小波去理發,理發師撥開他稠密的頭發,說:看看,還是兩個旋呢。然后摸著他的頭頂,驚叫一聲,“來龍去脈絕無有,突然一峰插南斗”,這不知是在夸獎,還是在褒貶他的頭形。一個理發師懂得骨相學,這也許并不奇怪,可是他居然兼通舊詩,可見人大確實是個藏龍臥虎的地方。接著他就開始欣賞小波的耳朵,說這不是耳朵,是個秤鉤子,用吊車掛上能把人提起來。據小波說,在他受懲罰的時候,我爸爸最喜歡揪住他的耳朵往上提溜。于是他歪著腦袋,皺著眉頭,腳尖配合我爸爸的動勢盡力上蹺,以減少耳朵的受力。但把腳尖蹺到頭后,他的一切努力再也無法減輕痛苦,只好像技窮的黔驢一樣掛在那里聽天由命,牙花子不停嘬著涼氣。據說我爸用勁大的時候他兩腳都能離地。日久天長,他的耳朵在外力作用下變得肌肉發達,跟鐵鉤子一樣。他給我看他平常挨揪的左耳朵,確實比右耳肥碩若干。由此也可見,如果繼續揪下去,把他變得像劉備一樣雙耳垂肩也不是難事。
他后來把這一段遭遇寫到自己的小說里。他寫道:
“1958年我獨白從家里跑了出去,在‘鋼堆邊摔了一跤,把手臂割破了。等我爬了起來,正好看到自己的前臂裂了一個大口子,里面露出一些白滑滑、亮晶晶的東西來,過了好一會才被血淹沒。但是我爸爸揪著我上校醫院時,以及大夫用粗針大線把我縫起來時,我呆頭呆腦地忘了哭。大夫看了,關心地說:老王,這孩子腦子沒有毛病吧?我爸爸說沒有,他一貫呆頭呆腦,說著在我頭上打了個鑿栗,打得我哇的一聲。然后我就看到我爸爸興奮地搓著手說:看到了吧,會哭,是好的。后來我看到回形針在我的肉里穿進穿出,嚎哭聲一聲高過一聲,他覺得太吵,在我腦袋上又打一鑿栗,哭聲就一聲聲低下去,我又開始想自己是個被套的問題。我爸爸在很短的時間內生了六個孩子,正所謂蘿卜快了不洗泥,只要頭上打一鑿栗能哭出來,他就很滿意。這件事說明,外表呆頭呆腦,好像十分樸實,而內心多愁善感,悲觀厭世——這些就是我的本性。”
關于人的本性,當時我們也進行了很多討論。聽說人的本性可以從一些外部特征看出來,這足以引起人的濃厚興趣。正像那個理發師說的一樣,小波頭上有兩個旋,而廣泛流傳的口訣是:一旋橫,二旋擰,三旋打架不要命。那時小波已經開始上學,但頑劣之性未改,不聽老師的話,全不懂得尊師重道。老師姓慈,他就給人家起了個難聽的外號,叫什么瓷尿盆。人往東,他往西,人家打狗他罵雞,說得好聽點叫有反抗精神,說得難聽點叫倔驢,確實夠得上一個“擰”字。有一次老師把他叫起來回答問題,他站在那里,兩眼平視,一言不發,一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架勢,氣得老師夠嗆,又拿他沒轍,對他喝道:坐下,一分。他就這樣吃了不少一分。他那股無緣無故、百折不撓的倔脾氣,當得起一個“擰”字。
上大學
在高考之前,小波面臨選科的問題。一般人多半沒有這個問題,因為他們或者擅文,或者擅理,可以擇其擅者而從之。而小波兩者都擅長,而且兩者都喜歡,如何選擇就成了個傷腦筋的問題。當時小波已經在和李銀河處朋友,李銀河認為小波在文學上有極高天賦,力主他學文科,甚至跟他說,好好寫,將來諾貝爾文學獎是你的,但這一主張違背我們家的家訓。我父親在哲學界從業多年,那一陣子天雷滾滾,草蟲皆驚,整天在提心吊膽過日子。所以他鄭重地告誡我們:如果不是壽星老上吊嫌命長,盡量離意識形態遠一點。后來小波來征詢我的意見,我說首先,世上的學問有真傳和假傳之分。有句老話說,“真傳一張紙,假傳萬卷書”,如果得了假傳,在萬卷書間忙得屁滾尿流,還要當一輩子糊涂人。無論什么時候,理T科的東西基本上屬真傳,而文科則未必如此。誠然,今天的文科已經有了巨大改善,但在20世紀70年代末,文科基本上以假傳為主。如果上四年學,天天學一些糊弄人的玩藝,豈不是虛擲光陰。其次,人到世上來一回不容易,怎么也應該對世界上的事情盡可能多懂得一點。數理是世界結構的重要一環,如果在這上面有所偏廢,思想訓練不足,將來想起事情來就可能蒙查查分不清絲縷。最后小波終于聽從了我的勸告,選擇了理工科,考進了人民大學的商品學系。
在學校里他碰上了兩個好老師。一個是教物理的,書講得頭頭是道不說,還在規定課程之余,應大家的要求,用一堂課的時間把相對論捋了一遍。據說滿堂的學生聽得搖頭晃腦,懂了個七七八八。下課之前,老師說,連他自己都沒想到,他竟然只用了一個小時,就把相對論(我猜是狹義相對論)有頭有尾地說了一遍。
另一位老師是教數學的。有一天他跟同學說,“我今天要給大家講一個東西。這個東西,作為數學的一個領域,可能你們一輩子都用不上,但我還是要跟你們講,不為了別的,只因為這些知識是好的,應該讓你們知道。”我不知道他在那堂課上教了些什么,但聽小波說,光是這幾句開場白就讓他受益匪淺。小波從此得到了一個信念:像數學這樣的學問,不是一種用來謀取衣食的稻粱之謀,而是一種崇高的智慧,有一種本體上的價值。這位老師實際上是在向學生們灌輸一種信仰一一經過一個蒙昧時代,這種信仰已經將近失傳一一那就是人應該超脫實利,從理性角度完善自身。
記得我們有一次借到了一本書,書名叫《人類改造自然》,是從外文原版翻譯過來的科學讀物,部頭很大,好像是海外印的,裝幀精美。把書打開,扉頁上是一段赫胥黎的名言。大意是說如果一個人能讓玉米多結一個穗,或者讓三葉草上多長一個葉子,他就對人世做出了重大貢獻。無論是皇室貴胄,還是廟堂上的袞袞諸公,都難以望其項背。這段話雖然不長,卻給我們內心造成了巨大撼動,有醍醐灌頂之功,所以以后一直把它奉為圭臬。這好像是一種源于西方的智慧,和中國的傳統思想方法全然不同。
中國人骨子里有一種無法克制的對權力的崇拜,皇帝和權臣永遠受到至高的敬仰,被視為歷史的核心。至于讓老玉米多結個穗一類的事則顯得毫不足道,是田舍翁或者販夫走卒的微末勾當,充其量算是個雕蟲小技,賞幾兩銀子就可以打發,絕不會寫在史書上。殊不知那些皇帝和權臣的你上我下,常常只是人們驢推磨一般原地打轉,和大槐安國螞蟻窩里的出將入相有得一比,無非是南柯一夢而已。試想那些山林中的土著蠻族,甚至各式各樣結群共生的動物,譬如說狼群、猩猩、甚至蜜蜂螞蟻之類,通常也會有一個白上而下的統治結構,也會有與皇帝、權臣、升斗小民相應的層次。他(它)們也會有自己的權力傾軋游戲,也會有自己的宮廷政變、狡獪和陰謀,甚至燭影斧聲、千古之謎。他(它)們也會有自己的朝代更替,也會有自己的戰爭和血腥屠戮,征服和被征服,也會有各式各樣的利益爭奪,包括對食物和異性進行爭奪的好戲。只可惜無數世代過去了,這些草莽英雄你方下臺我登場,競相折腰,努力表演,而他(它)們的族群始終在重復著原始循環,無法向前踏出半步。這樣的故事究竟有什么意思,這能算真正的歷史嗎?恐怕即使是人類學家或者是動物學家也不屑于記錄這些單調無味的重復。如果只是對這類伎倆津津樂道,我們和原始人和猩猩又有什么區別?
(摘自江蘇文藝出版社《我的兄弟王小波》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