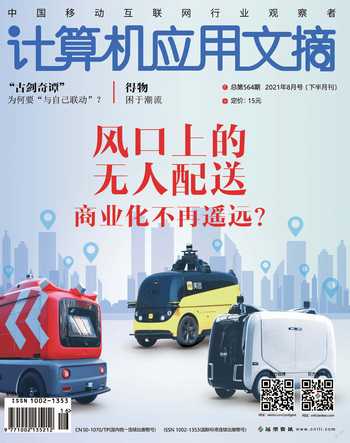巨頭們釋放的信號

巨頭們的行動
外賣和物流大軍的出現,曾經深度改寫中國互聯網的商業格局。面對無人配送這樣的新興物種,利益相關的互聯網巨頭們可謂相當謹慎,紛紛在資本和技術層面展開角逐,生怕錯過潛在的機會窗口。
一向“善戰”的美團,在無人配送賽道表現出了勢在必得的攻勢,僅在過去半年中就向外界釋放了兩個標志性信號:一是在4月20日的時候發起了近100億美元的募資計劃,并宣稱資金主要用于科技創新,無人車和無人機配送被重點提及,也就有了文初的一幕;二是在4月底推出了新一代無人車魔袋20,這款由毫末智行提供量產服務的車規級無人配送車,已經具備L4級別的自動駕駛能力。
嗅覺敏銳的阿里巴巴,同樣將目光盯向了無人配送賽道,在力道和速度上可以說絲毫不遜于老對手美團:去年9月的云棲大會上,阿里巴巴首次向外界演示了可量產的物流機器人小蠻驢,主要向園區、學校、小區等場景提供外賣、快遞等最后三公里配送服務;一個多月前的全球智慧物流峰會上,菜鳥首席技術官程立正式向外界宣布將在一年內投入1 000輛“小蠻驢”進入校園和社區的菜鳥驛站。
京東和蘇寧也躍躍欲試。前者宣布和行深智能、鑼卜科技、智行者、高深智圖等企業合作的無人配送車已經進行實驗性部署,其中京東物流的無人配送車“大白”在武漢跑了超過6 800公里的街道,運送了約1.3萬件包裹;后者進行了“臥龍”無人車的路測,包括自動識別路標并通過紅綠燈路口,在100米開外就能夠發現障礙,行進過程中自主規劃路線、避開障礙物、返回充電等。
巨頭們親身下場的同一時間,無人配送領域的創業派也動作頻頻。比如前面提到的毫末智行,除了為美團提供量產服務,自身也推出了小魔駝、小魔盤等產品,以及一系列場景化的定制方案,包括幫助人類解決繁重的物品運送工作的“自動跟隨載物平板機器人”,為主人運送物品、衣物等功能的“自動跟隨載物出行機器人”。
可以看到,盡管不同玩家的技術成熟度還有些差距,但“落地”已經是一種行業共識。相較于外冷內熱的無人駕駛汽車,技術難度相對較低的無人配送車似乎有了規模化量產的可能,哪怕短時間內在成本上仍高于人工。
乃至于可以根據巨頭們整齊劃一的動作,給出一個大膽的預測:2021年下半年開始,無人配送車將陸續出現在校園、園區、社區等特定場景中,既是為了廣泛地教育市場和用戶,也隱藏了巨頭們的野心,在無人配送產業中搏一個有利的站位。
商業化的最后一步
巨頭們的戰略布局和市場卡位,為無人配送的前景注入了一針強心劑,可這股熱度能夠維持多久,最核心的變量還是商業化進程。倘若只有幾十款的演示性產品,規模化落地的門檻不被掃除,市場進程終究會再次放慢。

疫情防控期間物流配送的“壓力測試”,無疑是無人配送行業跨周期崛起的主要誘因,并逐漸衍生出了三個利好因素。
一是無人配送車身份的“合法”。5月舉行的第八屆國際智能網聯汽車技術年會上,北京市高級別自動駕駛示范區頒發了國內首批無人配送車車輛編碼,首次給予了無人配送車相應的路權。“合法身份”的價值在于無人配送車的制度性規范,比如借道、超車、倒車等上路通行規則,尺寸、載重、速度等上路車輛標準,以及安全監管和車輛保險。監管和標準層面的市場空白被填補,等于為無人經濟業態的出現培育了“土壤”。
二是無人配送車的加速量產。和產業分工高度成熟的汽車工業不同,無人配送車的量產可以說是整個產業最大的短板。不僅要在車輛穩定性、非實時操作系統、決策規劃和運動控制技術等方面持續優化,還要逐步打通產業鏈的上下游環節,向一些上游供應商定制零部件。利好的消息是,國內無人配送車的產業鏈初步成形。

三是無人配送車的成本下降。辰韜資本曾在《末端無人配送賽道研究報告》中認為,當下制約無人配送車大量投入使用的主要原因是成本因素,包含軟硬件成本、運營成本、運營效率等。目前單輛無人配送車的成本在20萬~25萬元人民幣,相較于“外賣小哥”普遍6 000元人民幣上下的月收入,一輛無人配送車的造價約等于4位“外賣小哥”的年收入。但外界普遍認為,單車成本將隨著規模化量產下降,預計在三年內降至10萬元人民幣以內。
商業化被證實是最切實的驅動引擎,商業化落地的最后一步有了破局的可能后,市場做出反應不可謂不激烈。
京東、阿里巴巴、美團等巨頭均表示在年內投放千輛級的無人配送車隊,并在三年內投放上萬輛無人配送車。同時冷靜了一段時間的資本市場,也在2021年重押無人配送賽道,白犀牛、毫末智行、行深智能、PIX等均在上半年完成了新一輪融資,其中毫末智行在Pre-A輪融資的規模就達到3億元人民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