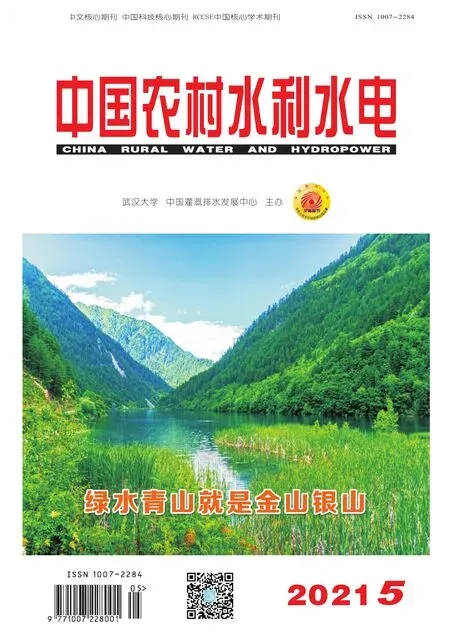氣候變化對巖溶區(qū)流域極端徑流頻率分析的影響研究
王大洋,王大剛
(中山大學地理科學與規(guī)劃學院,廣州510275)
當今環(huán)境下,氣候變化正時刻擾動著地表流域的水文循環(huán)過程,使許多流域的水文系統(tǒng)發(fā)生了明顯的改變。極端氣候的頻繁發(fā)生導致極端水文事件頻發(fā),量級也明顯增大,這其中最為突出的當屬降水和洪水[1,2]。傳統(tǒng)的洪水頻率分析多是基于徑流序列滿足一致性的前提,而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的影響,很可能會使原始洪水序列的一致性遭到破壞。因此,研究氣候變化條件下的洪水頻率分析是非常重要且有現(xiàn)實意義的[3-5]。此外,巖溶區(qū)作為中國西南地區(qū)常見的地貌類型,其水文循環(huán)過程本身就較普通流域復雜,因此,有必要針對巖溶區(qū)流域開展氣候變化對其極端徑流頻率分析的影響研究。
1 研究方法
1.1 趨勢分析和突變檢驗
研究分別采用線性趨勢分析和Mann-Kendall 檢驗方法對研究流域的徑流序列進行趨勢分析和突變點確定,從而將徑流序列劃分為兩個時段。突變前時段被認為是未受到氣候變化影響的時段,稱為天然時段;突變之后時段被認為是受到氣候變化影響的時段,稱為氣候變化影響時段。由于線性趨勢分析和Mann-Kendall 檢驗方法較為常用,故本文不再贅述相關理論,具體可參考相關文獻[6-7]。
1.2 徑流頻率分析模型優(yōu)選
針對極端徑流情況,研究采用廣義極值分布(GEV)和廣義帕累托(GPD)分布。選擇兩者的原因有兩點:①與皮爾遜III(P-III)型曲線在中國的廣泛應用相比,GEV分布和GPD分布在中國的研究起步相對較晚,但近些年的關注度在持續(xù)上升;②多數(shù)分布都是以兩者的統(tǒng)一形式為基礎進行衍生,如Gumbel分布、Fréchet 分布和Weibull 分布是GEV 分布的形狀參數(shù)選取不同符號(正、零、負)的具體表現(xiàn)。Pareto 分布、指數(shù)分布和Beta分布分別是GPD 形狀參數(shù)為(正、零、負)的具體表現(xiàn)[5]。GEV分布和GPD分布模型的表達式如下。
GEV的概率分布表達式為:
GPD的概率分布表達式為:
式中:μ、σ、ξ分別為模型的位置參數(shù),尺度參數(shù)和形狀參數(shù),滿足μ∈R,σ>0,ξ∈R和1+ξ(x-μ)/σ>0的條件。
1.3 樣本抽取
樣本抽選是頻率分析的基礎,針對GEV和GPD兩種不同的分布模型,其抽樣方法也是有所差異的。對于GEV,通常選擇序列中的“年最大值(AM)”作為抽樣依據(jù);而對于GPD,通常選擇超過某個定量值(POT)的所有數(shù)據(jù)來建模,適用于超門限值等系列的頻率分析。本研究中,參考我國學者進行POT 模型分析的經(jīng)驗,以樣本年限為基數(shù),以年均超過定量值發(fā)生次數(shù)2倍為原則進行樣本抽取,此外,對于POT 抽樣方法,還應當注意抽取樣本的獨立性,從而避免因樣本依賴導致的抽樣誤差[5]。
1.4 參數(shù)估計
由于極大似然估計法(MLE)結果能夠在總體上較好地反映樣本的統(tǒng)計信息,具有良好的統(tǒng)計性質[8,9]。因此本研究采用極大似然估計法進行分布模型的參數(shù)估計。用MLE 對GEV 和GPD進行參數(shù)估計的似然函數(shù)如下。
對于GEV,計算極大似然估計參數(shù)需要求解方程組:
對于GPD,其極大似然方程為:
式中:xi表示樣本值;ε表示門限閾值。
為了便于求解,通常將其轉化為對數(shù)形式的方程:
根據(jù)牛頓迭代法,可以計算得到相關參數(shù)。
1.5 模型優(yōu)選檢驗
模型建立后,通過對觀測樣本進行擬合和參數(shù)估計,可得到各模型的擬合結果。結合模型檢驗方法可以優(yōu)選出最合適的線型。本研究采用Kolmogorov-Smirnov 檢驗[10](簡稱K-S 檢驗),PP概率圖檢驗,QQ 圖檢驗3種檢驗方法,根據(jù)GEV 和GPD模型的擬合結果進行檢驗,從而確定最優(yōu)分布模型。
(1)Kolmogorov-Smirnov 檢驗。該方法以經(jīng)驗分布函數(shù)和理論分布函數(shù)之差為基礎,進行模型擬合效果的檢驗,其檢驗統(tǒng)計量為:
式中:yi是經(jīng)驗頻率去線上的點;F(yi)是累積分布函數(shù),N為樣本大小。
(2)PP 圖和QQ 圖。PP 累積分布概率(CDF)圖是根據(jù)變量的累積概率對應所指定的理論分布概率來繪制散點圖,它可以較為直觀地反映樣本數(shù)據(jù)與擬合模型分布的一致性。當樣本數(shù)據(jù)符合某一分布時,樣本點會較為接近45°對角線。QQ 圖則和PP圖比較相似,只是采用變量數(shù)據(jù)分布的分位數(shù)與所指定分布的分位數(shù)的關系進行比較。兩種方法的基本原理如下。
若樣本為{x1,x2,…,xN},若經(jīng)驗分布函數(shù)為(x) ={x1,x2,…,xN},模型估計的擬合分布函數(shù)為(x),則可以通過(x)和(x)的差異反映模型擬合效果。若用概率進行表示(PP圖),則為:
若用樣本點的分位數(shù)對比,即QQ圖:
2 研究區(qū)域概況
澄碧河發(fā)源于廣西壯族自治區(qū)西部的百色市,屬于珠江流域的西江水系,河流長度為127 km,流域集雨面積2 087 km2。高程由西北向東南逐漸走低,流域內(nèi)分布著較多的典型石灰?guī)r巖溶峰林,伏流河,落水洞較為常見,是世界上最大的連續(xù)巖溶地區(qū)之一。流域多年平均降水量為1 560 mm,因地形原因和巖溶發(fā)育較廣,汛期降水多集中且易引發(fā)洪澇災害,造成較為嚴重的社會經(jīng)濟損失和負擔。
流域內(nèi)部設有4個水文站,其中部分站點由于遷移、改測和撤銷等原因使水文序列時間較短,且不能滿足一致性要求。研究選取平塘站的1963-2017年的實測徑流數(shù)據(jù),該站點以上集雨面積占據(jù)整個流域的70%左右,且觀測資料較為完整,因此可以作為研究數(shù)據(jù)。
3 研究結果及分析
3.1 趨勢分析及突變檢測
氣候變化影響流域水文循環(huán),水文循環(huán)中水分經(jīng)過降水產(chǎn)流匯流過程,最終在河道的徑流環(huán)節(jié)得以體現(xiàn)。研究選取澄碧河水庫流域的年最大1日徑流量、年最大3日徑流量、年最大5日徑流量和年最大洪峰流量作為極端徑流的研究對象。首先采用線性趨勢分析,對4個極端徑流指標進行趨勢分析,然后采用Mann-Kendall 方法對其進行突變檢驗,從而確定極端徑流指標的突變時間點。
采用線性趨勢分析時,研究發(fā)現(xiàn)年最大1日徑流量、年最大3日徑流量、年最大5日徑流量和年最大洪峰流量均表現(xiàn)為下降的趨勢,將其趨勢線方程匯總在表1。從結果可知,最大5日徑流的下降率最為明顯,年最大3日次之,年最大洪峰流量相比之下降率最小。但4 個極端徑流指標總體均表現(xiàn)為下降趨勢,較為一致。

表1 各個水文特征值趨勢線方程
采用Mann-Kendall 檢驗方法對澄碧河水庫流域的上述4個極端徑流指標進行趨勢分析和突變檢驗,結果見圖1。從結果來看,年最大1日、年最大3日、年最大5日徑流的趨勢上具有較強的一致性。UF曲線的正負顯示了特征值的變化趨勢,圖1表明,年最大1日、年最大3日、年最大5日徑流在1990年之后,UF一直小于0,說明三者均表現(xiàn)出明顯的下降趨勢,且這一下降趨勢在1998年左右超出了α= 0.05 的顯著水平,表明下降趨勢顯著。相比之下,年最大洪峰流量,雖然在1983年之后呈現(xiàn)下降趨勢(UF<0),但未超出置信區(qū)間,因此其表現(xiàn)為不顯著下降。此外,由圖可知UF和UB的曲線出現(xiàn)交點,且該交點位于置信區(qū)間范圍內(nèi)部。從交點位置來看,年最大1日徑流量、年最大3日徑流量、年最大5日徑流量的交點位置均出現(xiàn)在1991年,而年最大洪峰流量的交點較多,為1973、1976、2002 和2013年。綜合各檢測結果,確定澄碧河流域的氣候突變發(fā)生在1991年。
3.2 序列分段與樣本抽取
根據(jù)檢測出的突變點,將整個樣本分為兩個時段:天然時段和氣候變化影響時段。研究中天然時段為1963-1991年,氣候變化影響時段為1992-2017年。因此,分別以兩段時間為基礎進行樣本抽選。
樣本抽選是頻率分析的基礎,針對GEV和GPD兩種不同的分布模型,研究采用不同的適應性抽樣方法。對于GEV,結合“最大值”原則,本研究中選取最大1日徑流量、年最大3日徑流量、年最大5日徑流量和年最大洪峰流量為GEV 分布擬合的基礎數(shù)據(jù);對于GPD,本研究,以年均超過定量發(fā)生次數(shù)2 倍為原則,針對突變前和突變后分別以58 和52 為樣本容量進行樣本抽取,針對澄碧河水庫的匯流時間,以3 d 作為抽樣間隔,以保證每個樣本的獨立性。
3.3 分布模型擬合及優(yōu)選
研究選取了GEV和GPD分布模型進行擬合與對比分析,其突變前、突變后時段擬合的PP 圖和QQ 圖為圖2和圖3,同時將擬合模型的各個參數(shù)值和K-S 模型檢驗結果匯總在表2。圖表中am 和pot 分別表示年最大取樣法和超定量取樣法,pre 和pos分別表示氣候突變前、后時段,1 d、3 d、5 d 和peak 分別對應最大1日徑流量(萬m3)、年最大3日徑流量(萬m3)、年最大5日徑流量(萬m3)和年最大洪峰流量(m3/s)。
從GEV分布和GPD分布模型的PP圖和QQ圖可知,兩個分布均能較好地反映經(jīng)驗觀測值與模擬值之間的關系,從散點圖與45°對角線的關系可以看出,兩者也都緊密地環(huán)繞在對角線周圍。通過K-S 檢驗量化的統(tǒng)計結果(表2)發(fā)現(xiàn):①所有情況下的統(tǒng)計量值均小于對應的顯著性標準值。由此表明,GEV 分布和GPD 分布均能通過α=0.05 的顯著性檢驗標準。②除了天然時段的年最大5日徑流量(pre-5d)和氣候變化影響時段的年最大1日徑流量(pos-1d)之外,其他所有情況下的K-S 檢驗結果中GPD 分布對應的統(tǒng)計量均小于(或等于)GEV 分布對應的統(tǒng)計量。因此綜合上述比較分析可知,雖然GEV分布和GPD分布均能很好地反映澄碧河流域的極端徑流序列,但相比之下,GPD分布在擬合澄碧河流域的極端徑流方面更具優(yōu)勢。

表2 GEV和GPD分布模型參數(shù)及K-S檢驗結果
從GPD 分布的參數(shù)變化來看,突變后時段相比突變前時段,年最大1日徑流量和年最大洪峰的形狀參數(shù)均有所減小,而年最大3日徑流和年最大5日徑流則表現(xiàn)為形狀參數(shù)增大。尺度參數(shù)方面,除最大1日徑流增大外,其余3 個指標均有所減小。而位置參數(shù)方面,只有年最大洪峰流量表現(xiàn)為增加,其余則都是減小的趨勢。由此表明,分布參數(shù)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
3.3 氣候變化對各重現(xiàn)期下極端徑流的影響
通過分布模型的對比分析,確定澄碧河流域的極端徑流頻率分析模型為GPD 模型。因此,以POT 抽取的樣本觀測數(shù)據(jù)為基礎,采用GPD 分布進行數(shù)據(jù)擬合,采用極大似然估計進行參數(shù)估計得到的線型可以作為重現(xiàn)期計算的依據(jù)。根據(jù)重現(xiàn)期與累積概率分布函數(shù)的關系可以計算天然時段和氣候變化影響時段的各重現(xiàn)期及其對應的極端徑流,進而研究在氣候變化條件下各重現(xiàn)期對應的極端徑流變化情況。
對計算的兩個時段的重現(xiàn)期進行分析,結果見圖4。
從圖4和表3變化可知,突變后時段的各個極端徑流指標在不同重現(xiàn)期水平下,較突變前均有不同程度的減小。其中,年最大洪峰變化最為明顯,10年一遇重現(xiàn)期水平下,其值由550.54 m3/s 減小至448.09 m3/s,減小比例為18.61%;100年一遇重現(xiàn)期水平下,其值由1 141.02 m3/s 減少至602.63 m3/s,減小比例為47.18%;1 000年一遇重現(xiàn)期水平下,其值由2 130.04 m3/s減少至718.52 m3/s,減小比例為66.27%。其次是最大1日徑流量,其減小比例為23.03%~65.51%。相比之下,年最大5日徑流量變化最小,其減小比例為12.95%~21.94%;由此可見,氣候變化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影響了極端徑流的頻率,使其發(fā)生了變化。

表3 澄碧河流域氣候變化前后極端徑流重現(xiàn)期
4 討論與結論
4.1 討 論
受氣候變化的影響,處于巖溶區(qū)的澄碧河流域的極端徑流序列平穩(wěn)性發(fā)生了變化,作為極端徑流指標的洪峰和洪量序列的平穩(wěn)性遭到了破壞,都由原本的“平穩(wěn)序列”轉變?yōu)榱恕胺瞧椒€(wěn)序列”。綜合分析,序列的突變年發(fā)生在20 世紀90年代初。研究表明亞洲區(qū)域,尤其是中國范圍內(nèi),氣候變化在90年代表現(xiàn)最為劇烈,這在一定程度上佐證了本研究的正確性。此外,據(jù)廣西百色市《凌云縣縣志》考證,澄碧河流域自20 世紀70年代之后就沒有再有過大規(guī)模的人類活動,因此造成極端徑流頻率變化的原因應該還是來自于氣候變化。氣候變化影響著流域的氣溫、降水、蒸發(fā)等水文循環(huán)過程,最終表現(xiàn)在極端徑流上[11]。
從結果來看,氣候變化影響最大的是年最大洪峰流量和年最大1日徑流,這可能與澄碧河流域的山區(qū)地形和巖溶區(qū)地貌有關。澄碧河流域弄塘以上流域多為巖溶區(qū),巖石裂隙、洼地、溶溝、溶槽和地下暗河等地質形態(tài)發(fā)育而成了交錯縱橫的地下河網(wǎng)體系。加上該地區(qū)土壤相對疏松,水流垂向運動頻繁,暴雨轉化為徑流的效率較高,一旦發(fā)生極端降水形成大洪水,也能很快被削峰坦化。從流域的匯流面積及匯流時間分析,即便是大洪水,基本也能在3 d 左右完成匯流過程。所以該流域對于短時降水引發(fā)的極端徑流,表現(xiàn)是較為明顯的。這與研究得到的年最大洪峰流量和年最大1日徑流變化率較大,而年最大5日徑流量變化率最小的結論相符。通過巖溶區(qū)釋水過程及徑流組分的相關研究[12,13]可知,由于巖溶洼地、溶溝、溶槽和地下暗河等地質構造的存在,使得巖溶區(qū)流域釋水過程要明顯快于非巖溶區(qū)流域,其衰減系數(shù)也相對較大。此外,巖溶區(qū)徑流組分隨洪峰的變化也較非巖溶區(qū)劇烈,這也是在氣候變化影響下,極端徑流頻率變化明顯的重要原因。
4.2 結 論
本文以澄碧河流域為實例,研究了氣候變化對巖溶區(qū)流域極端徑流頻率分析的影響,發(fā)現(xiàn)如下結論。
(1)澄碧河流域的氣候突變時間發(fā)生在1991年,可將其極端徑流序列分成突變前(天然時段)和突變后(氣候變化影響時段)兩個部分進行研究。
(2)GEV 分布和GPD 分布均能較好地擬合澄碧河流域的4個極端徑流序列,但相比之下,GPD分布表現(xiàn)更為突出。
(3)氣候變化導致該流域4 個極端徑流指標在不同重現(xiàn)期時都出現(xiàn)了不同程度的減小。其中,年最大洪峰流量減小比例最大,為18.61%~66.27%,年最大1日徑流量次之,年最大5日徑流量減小比例最小。
(4)巖溶區(qū)流域獨特的地質構造可能加劇了氣候變化對極端徑流頻率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