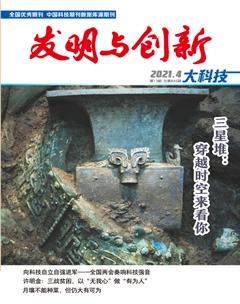爭當“首席科普官”,讓“科普之翼”強起來
“白內障對于老年朋友來說不是一個陌生的毛病了,但真的要選擇治療,卻又有很多觀念上的誤解……”“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感嘆頭發‘余額不足,信偏方不如信科學,首先還是要正確判斷脫發原因,再去選擇干預的手段……”3月5日下午,上海市第十人民醫院(下稱“上海十院”)的會議室里特別熱鬧,22名醫務人員輪番上陣帶來具有各自學科特色的演講,爭當醫院“首席科普官”的職務。
該事件經多家媒體報道后,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為推進科普工作鼓與呼多年的全國政協委員、中科院院士周忠和對此感到欣慰。“這表明越來越多單位和科研人員意識到科普的重要性,并轉變為行動。”他希望這樣的轉變更多些。
首席科普官,說是個官,其實這是個憑熱愛來發電的虛職,在競爭這個崗位前,上海十院的不少醫務人員其實早已擁有了豐富的科普經歷,下社區、上媒體,勤寫稿件、自制視頻,還有不少人斬獲過各級各類科普比賽的獎項。因此面對來自社區、媒體、衛生健康委、科協、兄弟醫院組成的評審專家團隊提問時,大家對于科普工作的意義有著充分的理解。
心內科副主任醫師劉偉靜表示:“都說上醫治未病,我也是在工作中漸漸理解了這個理念,我們往前走一步,離老百姓再近一步,希望能讓老百姓離健康近一步。”
眼科副主任醫師高鵬在微博上有著8000多粉絲,他說:“寫科普稿意味著得花業余時間去把熱點和專業相結合,這不是簡單的工作,但一想到通過這個渠道能有更多人了解到正確的眼病防治知識,就覺得有無窮動力。雖然我離‘大V還很遠,但有一分光發一分熱。”
重癥醫學科主治醫師姜維認為,科普工作除了接地氣外,團隊作戰也是不可或缺的。“科普官的主要職責除了自己做好科普,還要把周邊更多的人吸引到隊伍里來,讓健康科普成為每個醫務人員都具備的素養,這是我們今后要努力的方向。”
我國科普工作的進步有目共睹。
此前中國科協發布的第十一次中國公民科學素質抽樣調查結果顯示,2020年公民具備科學素質的比例達到10.56%,較2015年的6.20%提高了4.36個百分點,完成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提出的目標任務。
如果說數字太宏觀,公眾的感受則更真切。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健康科普與醫療救治、疾病預防一起成為“三駕馬車”。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以鐘南山、張伯禮、李蘭娟、張文宏為代表的一批醫務工作者將科研和科普有機結合,在穩定民心、科學戰“疫”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但周忠和認為,從戰略角度看,“科技創新與科學普及是創新發展的一體兩翼”這一格局尚未真正實現。“一些部門、科研單位、科技型企業對科普的重視和支持程度遠不如科技創新。”
周忠和分析,相關科研企事業單位普遍存在科普支撐能力、科普生產能力和科普服務能力不足等問題,如科普活動專項經費不足,引導與激勵措施吸引力不夠,科研成果科普化的機制尚未真正建立,科技資源向科普資源轉化的專業人才短缺,部分單位為科研人員提供的科普渠道和方式相對落后。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氣象局公共氣象服務中心氣象服務首席朱定真也認為,相比“科技創新”這一翼,科研人員參與度不高,管理層對科普工作認識不到位的現象依然存在。
“要做好頂層設計,建立科研與科普一體兩翼、協同發展的良好生態。”周忠和強調,要抓緊制訂科普與科研同步規劃、實施、評價、激勵的專項政策及實施細則,鼓勵科技工作者科研與科普并舉。
周忠和給出的數據是,截至2018年底,我國科技人力資源總量達10 154.5萬人,居世界首位,但2019年全國科普專、兼職人員只有187.06萬人。
在中科院國家天文臺研究員鄭永春看來,我國科普體系建設需進一步加強。“科研領域有各種人才計劃、獎勵制度、重大項目等,科普領域基本沒有,或者很少。”他說,系統的科普能力建設必須從學科、人才、資助等方面成體系抓,“要不然可能只是某個地區、某個單位做得好,但總體仍是低水平建設,長期下去,不同地區、不同領域之間的科普不平衡會持續加大。”
鄭永春介紹道,國外很多大學都設有專門的科普教職,比如《自私的基因》一書的作者道金斯就是牛津大學第一任公眾傳播科學教授。
“目前僅上海、廣東等少數省市設立了科普人物、作品獎項,僅北京、天津等地設有科普系列職稱評定。”朱定真說。
正因此,周忠和呼吁,在科研項目尤其是國家和地方重大科研項目中納入科普指標,促進科研與科普緊密結合;設立完善的科研科普工作考評體系,合理體現科普權重;借鑒上海市設立科普教育創新獎的經驗,完善國家科技獎勵體系,設立科學技術普及獎,鼓勵行業與社會設立相應科普獎勵,充分發揮科普獎勵的引導作用。
周忠和認為,還應設立前沿重點科技領域科普專項。“科普專項由重點科技領域的權威科技專家牽頭,聯合科研機構、高校、媒體、科技場館、出版機構、中小學等共同參與實施。”他說,對于科學素質較低的西部地區予以重點關注,開展針對性科普項目。
不可否認的是,當前我國仍然缺乏優質的科普內容。
“雖然我們的科普圖書有了比較大的進步,但占據主流的依然是國外引進的圖書,科普主題的紀錄片更是被壟斷,我國這些年科技創新取得的巨大成果,目前還沒有轉化成優秀的科普作品。”鄭永春坦言。
另一重要瓶頸是,我國缺少相關資源支撐。“我們還沒有建立專門的科普圖片庫,出的科普書里的圖片基本都是國外的,而國外一些機構,比如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就有高質量的科技圖片和科普影視素材庫,并免費提供。”
朱定真說,科教電影也得不到像故事片那樣的關注和投資,生產數量逐年下滑。“政府設立的‘中國電影華表獎2016年就撤銷了最佳科教片獎,每年對科教片的資助在2020年也暫停了,金雞獎2020年將原本獨立的最佳科教片獎與紀錄片獎合并為一個獎。”
朱定真建議,設立中國促進科學傳播產業投資基金,文化產業的投資保持一定比例以支持科普事業發展,通過稅收減免等政策鼓勵企業加大科普投入。
鄭永春則強調,目前受眾面較廣的大平臺也要擔起社會責任。“一些短視頻平臺完全根據算法推薦內容,在這種算法下,優質科普內容大概率拼不過娛樂內容。”他說,這些平臺應采取一些措施,給予這些內容傾斜支持,弘揚科學精神。(據《科技日報》《新民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