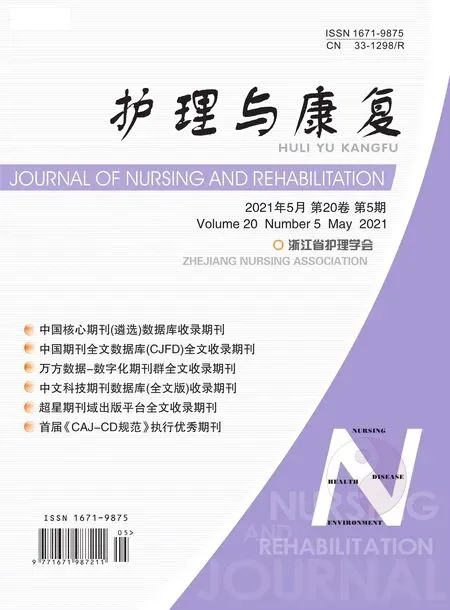基于循證的泌尿外科術后患兒導尿管留置及早期拔管的方案制訂與實踐
蔣偉紅,單曉敏,徐紅貞,余真香,諸紀華
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兒童醫院,浙江杭州 310003
留置導尿管在泌尿外科手術患兒中的應用非常廣泛,尤其是腎臟、膀胱輸尿管等部位的手術,因治療及病情觀察的需要,術后通常留置導尿管以及時引流尿液、膿液等,防止其反流而影響切口愈合。但長期放置導尿管會增加患兒感染等相關并發癥的發生率,限制其術后早期活動,延長住院時間,加重醫療費用負擔等[1-2]。研究發現,導尿管留置4~6 d術后感染率為18.60%、留置>7 d術后感染率則高達75.00%[3]。目前國內外雖有相關導尿管管理的指南文獻,但臨床上仍經常出現導尿管使用不恰當及拔除不及時的情況[4-6]。本研究基于導尿管的臨床使用與管理現狀,借鑒高質量的指南,制訂適合臨床應用的導尿管留置及早期拔管循證實踐方案,并應用于臨床,以期為泌尿外科術后患兒導尿管的規范化使用及護理提供參考依據。
1 方法
1.1 導尿管留置及早期拔管方案的制訂與實施
1.1.1成立循證小組
組建導尿管留置及早期拔管循證小組,共9名成員,1名護理部主任,主要負責循證項目培訓和指導;1名泌尿外科護士長,主要負責項目的總體規劃、推進和質量控制;2名護理研究生,主要負責檢索證據、質量評價及數據匯總分析;2名責任組長及3名骨干護士,主要協助循證方案的臨床應用及進行數據收集。小組成員均接受臨床實證應用項目系統培訓并全部通過考核。
1.1.2確立循證問題
根據PIPOST構建模式確定循證問題。P(population)為泌尿外科手術的患兒;I(intervention)為減少導尿管使用及促進早期拔管的干預措施;P(professional)為泌尿外科病區的護士和醫生;O(outcome)為預期結局;S(setting)為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兒童醫院泌尿外科病房;T(type of evidence)為檢索證據類型。
1.1.3證據檢索
遵循金字塔原則進行系統化的證據檢索,中文檢索詞:“兒童/兒科/小兒”“短期/早期”“留置”“導管/導尿管”“感染”“移除/拔除/拔管”。英文檢索詞:“children/pediatrics”“short-term/early”“indwelling”“urethral catheter/urinary catheter/catheterization”“infection/urethral tract infection”“removal”。檢索Nature、PubMed、Cochrane Library、BMJ、JBI、萬方數據知識服務平臺、維普資訊中文期刊服務平臺等文獻數據庫2008年至2018年的所有關于導尿管的證據,包括臨床實踐指南、證據總結、系統評價和基于原始研究數據的證據總結。共檢索到278篇:Nature 35篇,PubMed 190篇,Cochrane Library 2篇,BMJ 1篇,萬方數據知識服務平臺48篇,維普資訊中文期刊服務平臺2篇。其中主題不符剔除271篇,去除重復剔除4篇,最后納入指南3篇[7-9]。采用指南研究與評價(AGREE Ⅱ量表)[10]對納入的指南進行文獻質量評價,指南1、指南2、指南3的標準化得分分別為96.62%、89.86%、92.75%,均為強烈推薦,故均納入研究。根據FAME評價法[10],對證據應用的可行性、適宜性、臨床意義和有效性進行評價,最終納入5條證據,但由于檢索到的證據來源于不同的機構,其證據分級系統不同,本研究統一采用JBI循證衛生保健中心和美國感染病學會(Infectious Diseases Society of America,IDSA)所發布的分級和推薦標準(2009版)[11-12]進行證據的匯總評價,并確定了5條質量審查指標,見表1。

表1 證據轉化質量審查指標
1.1.4制訂早期拔管方案
本研究以Iowa循證實踐模式[13]為指導,參考循證臨床實踐指南改編的步驟[14],借鑒由安大略省注冊護士協會(RNAO)發布的指南實施工具書[15]中相應的實施策略,初步制訂導尿管留置及早期拔管方案,并實施專家函詢。最終形成泌尿外科術后患兒導尿管留置及早期拔管方案,包含一級條目4項,二級條目10項,各條目及方案內容見表2。

表2 泌尿外科術后患兒導尿管留置及早期拔管方案
1.1.5導尿管留置及早期拔管方案的實施
將實踐方案在浙江省某三級甲等兒童醫院泌尿外科病房開展3個階段的臨床研究,包括方案應用前的基線審查、兩輪實踐變革及效果評價。2018年6月至10月開展了證據應用前的基線審查;2018年12月至2019年4月開展第一輪實踐變革及效果評價,根據在實施過程中新出現的障礙因素,采用整合式健康服務領域研究成果應用的行動促進框架(i-PARIHS)[16]分析并在原有基礎上制訂相應的行動策略,以確保循證實踐方案的實施;2019年6月至10月開展第二輪實踐變革及效果評價。
1.2 質量控制
在實踐方案第一輪應用期間(2018年12月至2019年4月),方案中“手術留置導尿管的患兒,若無繼續留置的適應證,在手術24 h內盡早拔除”行動策略的執行率較低,再次使用i-PARIHS分析原因,確定存在的障礙因素如下:部分護士對導尿管留置的適應證掌握不到位;臨床工作繁忙,對導尿管及時拔除的監督存在遺漏;缺乏完善的培訓、考核機制。基于以上障礙因素分析,更新方案的實踐變革措施:將小兒泌尿外科導尿管留置的適應證及早期拔管標準制作成隨身攜帶的小卡片,以便為護士進行導尿管相關操作前提供標準參照;導管管理護士加大監察力度,對于依從性低的護士進行訪談,及時反饋、更正,提高執行率;增加培訓頻率并將培訓內容納入晨間提問,及時進行考核,并對規范操作行為給予激勵和表揚,納入個人績效考核。在此基礎上,2019年6月至10月開展實踐方案第二輪臨床應用。

表2(續)
2 效果評價
2.1 研究對象資料
基線調查、第一輪和第二輪實踐變革3組研究對象均為行小兒泌尿外科手術患兒。基線調查100例,男48例、女52例,年齡(28.97±19.72)月;腎積水45例,重復腎12例,發育不良腎13例,腎囊腫9例,膀胱輸尿管反流21例。第一輪100例,男44例、女56例,年齡(27.21±19.24)月;腎積水41例,重復腎12例,發育不良腎8例,腎囊腫15例,膀胱輸尿管反流24例。第二輪100例,男46例、女54例,年齡(29.86±19.83)月;腎積水42例,重復腎13例,發育不良腎13例,腎囊腫12例,膀胱輸尿管反流20例。3組患兒的性別、年齡、疾病等基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基線調查、第一輪和第二輪實踐變革3組研究對象均為同一批泌尿外科護士,共15人,均為女性,平均年齡(30.57±3.20)歲,平均工作年限(8.80±4.39)年,研究生2人、本科13人,主管護師6人、護師9人。
2.2 評價指標
由循證小組評價泌尿外科術后患兒導尿管留置及早期拔管方案應用前后5條質量審查指標的達標率,患兒導尿管的置管率及住院時長,導尿管留置時長、留置期間相關并發癥(包括導尿管相關的尿路感染、導尿管阻塞、意外拔管)發生率,患兒拔管后不良反應(包括尿潴留、重新置管)。對護士導尿管知識的掌握情況進行測評,自行設計測試卷3套,內容涉及導尿管的置入、維護、拔除等,每套測試難度、題型、內容相似,測試卷總分100分,題型包括30道單選題(2分/題)和2道問答題(20分/題)。對護士導尿管行為規范進行測評,自行制定泌尿外科護士導尿管操作行為查檢表,該表包括導尿管置入、維護、監督、拔除四大維度,細分為20個條目,使用Likert 5級評分法,每個條目分為非常不標準(1分)、不標準(2分)、一般(3分)、標準(4分)、非常標準(5分)5個計分等級,總分100分。
2.3 統計學方法

2.4 結果
2.4.1審查指標的達標情況比較
方案應用前后審查指標達標率比較,見表3。

表3 方案應用前后審查指標達標率比較 %
2.4.2患兒各結局指標比較
方案應用前后患兒導尿管的置管率及住院時長比較見表4,術后留置導尿管患兒的導尿管留置結局指標比較見表5。

表4 方案應用前后患兒導尿管置管率及住院時長比較

表5 方案應用前后患兒導尿管留置結局指標比較
2.4.3護士知識水平及行為規范比較
方案應用后護士知識水平及行為規范均有顯著提高(P均<0.001),見表6。

表6 方案應用前后護士導尿管知識及行為規范得分比較(n=15)
3 討論
3.1 基于循證的導尿管留置及早期拔管方案有利于改進臨床護理質量
留置導尿是臨床上常用的操作技術,但其導致的并發癥亦不容忽視,如尿路感染、尿潴留、尿路損傷等。有研究顯示,尿路感染的發生率高達40%~50%,占醫院感染的第1位,其中70%~90%的尿路感染與留置導尿管相關[17]。本研究基于循證制訂泌尿外科術后患兒導尿管留置及早期拔管的方案,引入“導尿管生命周期”模型,從導尿管的置入、維護、拔除、重置四個環節的有效干預來規范管理醫護人員導尿管操作;統一相關導管護理記錄單的書寫,如記錄中應標明置管適應證、置入時間、拔除時間以及每班記錄拔除或說明繼續留置的標準等;建立導尿管數據分析報告系統,使用大數據監測導尿管留置時長及其相關的不良后果,一旦超過規定的留置時長或發生不良后果,系統將及時提醒醫護人員早期拔除導尿管。經過兩輪的實踐變革,審查指標1、4、5的達標率均為100.0%,審查指標2、3的達標率升至94.0%、96.0%,可見基于循證的早期拔管方案的應用有利于規范導尿管的管理,持續改進臨床護理質量。
3.2 基于循證的導尿管留置及早期拔管方案可改善患兒結局
有研究表明,導尿管相關性感染的發生率和導尿管的留置時間呈正相關,隨著導尿管留置時間的增加,感染發生率平均以每天3%~7%的速度增長[8]。故減少不必要的導尿管留置和最大程度縮短導尿管留置時間相當重要。本研究基線調查發現,該院泌尿外科手術患兒導尿管使用率高達100.0%,留置導尿管時長高達129.0(118.0,140.0)h。然而相關文獻表明,小兒泌尿外科手術患兒無需常規留置導尿管,且留置后一旦不具備繼續留置的適應證,應在24 h內盡早予以拔除[2,7]。
對此,本研究使用i-PARIHS進行原因分析,確定主要障礙因素,針對障礙因素提出策略并實施。經過兩輪實踐變革,導尿管的置管率降至64%,留置時長降至109.5(100.0,114.8)h。由表4、表5可見,基于循證的導尿管留置及早期拔管方案實施降低了導尿管相關尿路感染和尿潴留的發生率,縮短了患兒的住院時間(P均<0.05)。表明基于循證的導尿管留置及早期拔管循證實踐方案能有效減少非必要的導尿管使用和縮短導尿管留置時長,有效改善患兒的結局。本研究中患兒導管阻塞、意外拔管的發生率在實踐變革前后并無明顯差異,可能與其低發生率及本研究的樣本量小有關,后續可加大樣本量做進一步研究。
3.3 基于循證的導尿管留置及早期拔管方案能提高護士的知識及行為規范水平
指南指出確保醫護人員定期接受導尿管在職培訓,培訓內容包括導尿管的插入、維護和拔除,導尿管相關尿路感染,其他并發癥,選擇合適的導尿管[8]。本研究基線調查發現,護士導尿管相關知識得分僅(68.13±8.46)分,護士導尿管行為規范得分僅(74.01±7.78)分,均處于較低水平,主要原因為醫院未對醫護人員進行導尿管相關知識的培訓及考核。本研究將相關的導尿管循證資料納入科室業務培訓中,通過培訓、檢查、再培訓等方式定期開展對護士導尿管相關護理行為的系統學習。在第一輪實踐變革中,護士對導尿管的置入、維護及拔除等行為規范得分為(84.07±4.32)分,對導尿管相關知識得分為(81.93±3.56)分,其方案對護士層面的實踐變革有待進一步加強。因此,研究小組再次使用i-PARIHS分析,重新制訂整改措施,將導管培訓納入護士月學習計劃,每個月學習不少于2次,并及時在培訓后對護士進行考核,評估其導管相關專業知識的掌握情況。并重點開展對未達標護士的強化培訓,定期反饋其導尿管行為規范存在的問題,明確考核機制,將考核質量納入護士績效考核。同時,循證小組成員每天查看護士的執行依從性,對新標準實施過程中出現的偏倚及時進行糾正。第二輪實踐變革中護士導尿管的知識水平及行為規范均得到很大提高,有效規范了護士導尿管護理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