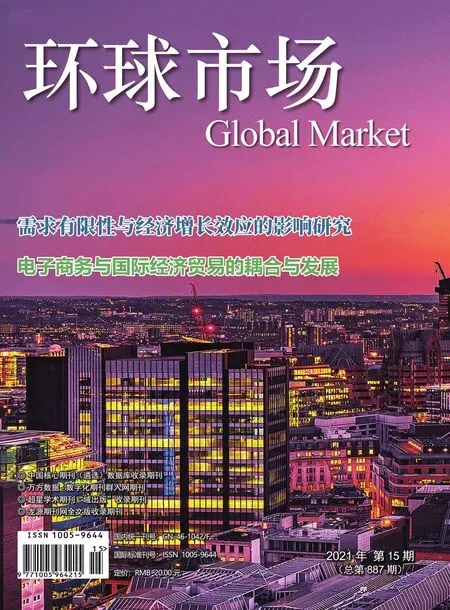地方財政能力的新詮釋
閆婷 中共遼寧省委黨校
一、地方財政能力的內涵
筆者認為地方財政能力體現為兩點:一是促進地方內生發展能力,即以制度創新和政策設計,使得市場、社會各主體能自主進入地區價值和財富創造的進程中,引導地區社會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軌道,可稱為內生發展能力;二是防范化解地方風險能力,即地方政府集中資源以拆解和防范那些容易具有系統性、高關聯性和傳導性的風險點,以實現地區發展的穩定,可稱為控制風險能力。
為提高地方內生發展能力,地方政府需要做到:一是對政府財政活動進行有效規管,規管是規管政府所有部門的外部財政行為(王紹光,2014[1]),使政府部門的財政行為符合黨中央所制定的規則。特別是在經濟建設領域,政府更好發揮作用,保障市場運行的有效性,實現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的結合,建立高標準的現代市場體系,保護產權、促進市場要素自由流動等,這些都需要對政府權力進行更好的規管;二是實現再次分配的均等性和基本保障性。這里的再分配指的是公共物品,像基礎設施、基本養老、醫療、教育等公共物品分配以均等化為基本原則,要保障社會各群體的生存權利,縮小收入、財富在初次分配時的不平等;三是宏觀調控,即對經濟波動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進行間接調控,對社會問題設計制度機制以化解。
為提高控制風險能力,地方政府需要做到:一是對財政資源的強化統籌,嚴格控制政府的預算外行為,包括預算外資金和收費,實現所有政府行為在國家預算約束之內,目的是既對政府財政風險有效把控,又能在對沖社會經濟風險時及時整合財政資源;二是公共資源的汲取與整合。政府的控制風險能力有兩個基本因素,即公共資源汲取力和整合力。這主要指的是政府對公共資源的控制力,包括對社會資源和經濟資源在必要時刻的汲取和整合;三是對風險的評估和預判。風險包括公共風險和政府風險,需要對這兩者建立相應的評估和預判制度及其機制,才能有的放矢的控制風險、化解風險,為社會經濟提供穩定的預期。詳見圖1。

圖1 地方財政能力支柱圖
二、地方財政能力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保障
回顧改革開放歷程可以發現,我國地方經濟改革初期是在中央高度集中財政收支權和資源配置權的計劃經濟體制下開啟,在中央逐漸放松下放權力的過程中面對的是如何充分激發地方市場主體活力,解放和發展地方生產力的問題。正如林毅夫在其《新結構經濟學(2019年版)》一書中所寫到的:中國改革的經驗是強調市場和政府在促進經濟發展過程中均要扮演重要角色,經濟發展既要“有效市場”,也要“有為政府”。“只有同時用好市場和政府兩只手才能實現快速、包容、可持續的增長。”[2]在這里,中國確定改革開放后就開始同時啟動政府內部激勵機制改革和市場化改革,即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下,以經濟增長和發展為核心任務,一邊不斷放松政府管制、引入市場機制,另一邊激勵地方政府主動發展經濟,最終形成市場主體與地方政府并重的經濟發展格局。在體制及其配套政策改革實施上,財政系統改革一直發揮著破冰者作用,從改革初期的探索階段的央地財政分權改革,通過“行政性分權”到“經濟性分權”等創新體制舉措,到現代財政制度目標的設立,逐步完善調整市場與地方政府間關系,并最終確立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有效結合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最佳發展模式。從中我們不難發現,市場與地方政府的共同作用是中國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功的寶貴經驗。如果我們承認這一點,那么在不斷推進國家改革的進程中,地方財政能力的主導與保障作用也就不可否認。在改革開放初始階段,中央以財政分權改革打破“統收統支”的集權型計劃經濟體制,在央地間財政關系上嘗試以“分灶”“包干”等形式調動地方積極性,同時在政企間實行“利改稅”“承包”等措施下放經營權,有效激勵了地方政府發展轄區經濟的積極性和動力。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行講話后,財政系統為了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國家間接宏觀調控體系,推進分稅制改革,在明確事權和支出責任基礎上進行財政收入的劃分,通過“稅費”相關改革規范央地、政企間關系,建立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運行機制。進入改革新時代后,不斷推進政府預算、部門預算、國庫支付以及政府采購等改革,完善相關制度建設,不斷調整地方政府與市場主體間的關系,平衡、彌補地方政府所存在的一系列“越位”與“缺位”問題。在整個過程中,既確保了黨的領導核心基本政治制度不動搖,中央政府宏觀調控能力不斷增強,同時也對地方政府推進改革、引導本地經濟的能力進行加持,從而實現了經濟改革始終以國家規劃戰略、人民切身利益為核心不斷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雖然,在近些年,地方財政在可持續性問題上存在一些挑戰,但整體而言,地方財政相關改革仍按照計劃進行。現代財政制度改革部署按部就班,在地方財政可持續、央地財政關系、事權與支出責任劃分、收入與財力劃分等重大問題上,已經有了明確的改革目標并取得了有效進展,地方財政改革與建設始終為我國改革提供重要支撐和保障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