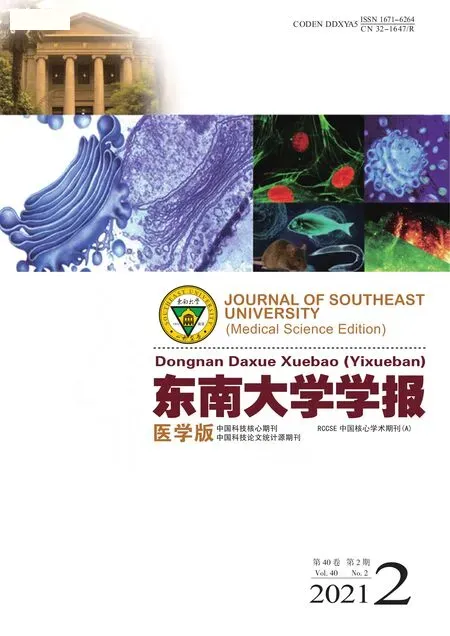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癥冠狀病毒-2與橫紋肌溶解癥
韋湛海,呂海芹
(東南大學 醫學院,江蘇 南京 210009)
2019新型冠狀病毒(2019 novel coronavirus,2019-nCoV),又被稱為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癥冠狀病毒-2(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SARS-CoV-2),是一種具有高傳染性的新型冠狀病毒,由SARS-CoV-2感染引發的新型冠狀病毒病(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全球大流行給人類健康造成巨大威脅。根據霍普金斯大學的統計數據,截至北京時間2020年11月19日12點,全球已經有56 187 563人被確診感染SARS-CoV-2,1 348 600人死于COVID-19[1]。SARS-CoV-2感染患者出現病理損傷的部位主要是肺部,胸部電子計算機X射線斷層掃描(computed tomography,CT)檢查顯示散在分布于全肺的磨玻璃樣密度影、網格狀影和(或)纖維化影等,病情發展后期逐漸進展為實心白色樣的“肺實變”,最常見的臨床癥狀包括發熱、咳嗽、呼吸困難、肌痛和全身不適,少數患者出現腹痛腹瀉[2-4]。但是隨著患病人數的增加,越來越多的文獻報道提示COVID-19是一種多器官系統疾病,除了呼吸系統以外,還可以侵犯消化系統、神經系統、泌尿系統及骨骼肌系統等,有的患者甚至以其它系統損害為主要臨床表現,這些非典型表現增加了COVID-19臨床診治的難度和挑戰,影響疾病的預后,需要引起特別重視[ 5-11]。
橫紋肌溶解癥(rhabdomyolysis)是一種急性、潛在的致命性綜合征,是由于物理、化學、生物等因素導致橫紋肌細胞壞死、崩解,細胞內容物大量釋放入血液而引起的一組臨床綜合征。由于引發橫紋肌溶解的因素不同,其臨床表現也不全相同,一般當血清肌酸激酶(creatine kinase,CK)水平為正常值的5倍以上或血/尿肌紅蛋白升高時,即可確診[12]。Guan等[4]統計了1 099例發生在中國大陸的COVID-19患者的臨床資料,發現有13.7%的患者出現CK升高,2例患者出現了橫紋肌溶解。橫紋肌溶解癥是COVID-19的一種罕見并發癥,但是如果不能及時診治,容易引起代謝紊亂、電解質異常及急性腎功損傷(acute kidney injury,AKI),甚至成為患者的直接致死因素[8]。作者綜述了目前已經報道的SARS-CoV-2感染相關的橫紋肌溶解癥案例,并分析了其臨床特點及可能的發病機制,從而為進一步防治COVID-19及其并發癥提供理論依據。
1 SARS-CoV-2感染相關橫紋肌溶解癥的臨床特征
作者以“COVID-19 and Rhabdomyolysis”和“SARS-CoV-2 and Rhabdomyolysis”為關鍵詞,從Pubmed和SciFinder數據庫檢索到24篇SARS-CoV-2感染相關的橫紋肌溶解癥案例報道[7-11,13-31]。這些文獻一共報道了28個臨床案例,從這些案例的臨床資料中可以發現SARS-CoV-2感染相關的橫紋肌溶解癥的發生無地域分布特征,3例發生于中國,15例發生于美國,墨西哥和瑞典各2例,其余6例分別來自西班牙、土耳其、法國、葡萄牙、比利時和秘魯。不同性別患者的疾病發生率和預后有明顯差異,28例患者中男性為24例(占患者總數86%),其中19例伴有AKI,死亡7例,2例治療后病情繼續惡化;4例女性患者中只有1例伴有AKI,經治療后全部好轉。AKI是橫紋肌溶解癥的嚴重并發癥,這類患者除了需要大量補液治療以外,常常需要腎功能替代治療,為了了解不同性別對橫紋肌溶解癥病情的影響,作者對不同性別患者AKI發生率進行了統計學分析,結果發現男、女性患者中發生AKI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提示男性COVID-19患者更易發生AKI且預后較差(表1)。各個年齡段的COVID-19患者均可發生橫紋肌溶解,患者年齡最大者為88歲,最小者為15歲。50歲以上患者共12例(占43%),其中有 9例伴有AKI;50歲以下患者16例(占57%),其中11例伴有AKI,不同年齡AKI發生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表1 ),提示年齡與病情嚴重程度、是否會引起AKI及預后無直接相關性。有20例患者(占71%)在感染SARS-CoV-2前患有其它疾病或曾接受過其它治療,其中16例出現AKI;8例無基礎性疾病或未接受過其它治療的患者中有4例出現AKI,但是兩組之間AKI發生率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表1)。在臨床表現方面,所有患者都出現局部或全身肌肉疼痛和無力,肌肉疼痛以四肢更為顯著,伴有肌肉壓痛,部分患者出現尿的顏色變深甚至呈濃茶水或可樂樣顏色,這些癥狀出現的時間無明顯規律性,有的出現在發病初期[18,21,23],有的出現在病程后期[13,20];23例患者(占82%)同時有呼吸系統感染的臨床癥狀,包括發熱、咳嗽、氣短、呼吸困難及乏力等,多數患者胸部X線或CT顯示雙肺多發磨玻璃影、浸潤影,個別患者僅出現胸膜腔少許積液[7,11],23例患者中有17例出現AKI;5例無呼吸系統感染表現的患者中有3例出現AKI,有無呼吸系統感染表現的患者AKI發生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表1)。部分患者除了呼吸系統和骨骼肌受到侵犯以外,還出現心血管系統病變,2例患者有心肌炎或心肌炎合并心包炎[10-11],1例患者出現嚴重的下肢靜脈血栓形成及閉塞性動脈粥樣硬化樣病變[9],1例患者出現嚴重的體循環毛細血管滲漏綜合征(systemic capillary leak syndrome,SCLS)[24],周圍血管病變加重了病情,增加了診斷和治療的困難,提示預后較差。所有發生橫紋肌溶解癥的COVID-19患者都出現血液CK或肌球蛋白(myoglobin)顯著升高,CK峰值出現的時間不固定,有的是入院時即為峰值,有的是在治療過程中出現峰值,經過治療峰值一般持續2 d左右開始下降;另外,除了反映腎功能的血液肌酐、尿素氮、電解質及淋巴細胞等常規指標變化以外,絕大部分患者的血液中丙氨酸氨基轉移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天門冬氨酸氨基轉移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AST)、乳酸脫氫酶(lactate dehydrogenase,LDH)、C反應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D-二聚體(D-dimer)等炎癥因子明顯升高,提示炎癥反應在橫紋肌溶解的發生發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表1 SARS-CoV-2感染相關橫紋肌溶解癥患者伴發AKI的影響因素 例
2 SARS-CoV-2感染相關橫紋肌溶解癥的發病機制
目前對于COVID-19相關的橫紋肌溶解癥的發病機制還不清楚,根據已有的文獻報道及患者的臨床診治資料推斷,可能的發病機制:(1) 病毒侵犯橫紋肌細胞導致橫紋肌溶解;(2) 病毒引起機體的過強免疫反應導致大量細胞因子釋放和過度炎癥反應,破壞肌肉組織;(3) 肌肉組織缺氧性損傷。
2.1 SARS-CoV-2感染直接引起橫紋肌溶解
既往的研究表明,流感病毒、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癥(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病毒感染均可以引起橫紋肌溶解癥,其中以流感病毒相關性橫紋肌溶解最常見[32-36]。SARS-CoV-2是屬于β屬的冠狀病毒,為單鏈正股RNA病毒,病毒基因組被包裹在由核衣殼蛋白形成的螺旋衣殼內,并進一步被包膜包裹。病毒顆粒呈球形或橢圓形外觀,至少有3種蛋白與病毒的包膜相關,其中膜蛋白(membrane protein,M蛋白)和衣殼蛋白(envelope protein,E蛋白)與病毒的包裝相關,刺突蛋白(spike protein,S蛋白)介導病毒侵入宿主細胞[3,37-39]。S蛋白是一種糖蛋白,位于病毒表面,呈釘狀向外突起,它除了介導病毒入侵以外,也是誘導宿主免疫反應的關鍵因子。S蛋白由S1和S2兩個亞單位組成,S1用于與宿主細胞受體結合,能夠與人血管緊張素轉換酶2受體(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2 receptor,ACE2)高度親和性結合;S2用于膜融合,當病毒顆粒通過S1與受體結合附著在宿主細胞表面后,S2使細胞膜與病毒顆粒的膜融合,然后通過內吞作用進入細胞[38-40]。Wrapp等[39]研究發現,SARS-CoV-2的S蛋白與ACE2的親和力遠高于SARS病毒的S蛋白,提示其傳染性更強。Desdouits等[41]研究發現,分化成熟的骨骼肌細胞是甲型流感病毒H1N1的易感細胞,病毒可以直接感染骨骼肌細胞并在細胞中增殖,增殖的子代病毒具有較強的傳染性,能夠感染周圍的肌細胞,被感染的細胞發生病變、溶解并持續釋放炎癥細胞因子,為病毒直接侵犯骨骼肌細胞引起橫紋肌溶解提供了直接的證據。ACE2是腎素-血管緊張素系統(renin angiotensin system,RAS)中一種重要的金屬鈦酶,廣泛表達于各種器官和組織,在調節血壓、體液平衡和細胞增殖等生命活動中發揮重要作用[42-43]。目前雖然未見到有關ACE2在骨骼肌細胞中表達的研究報道,但是不能就此排除ACE2在骨骼肌細胞上的表達,SARS-CoV-2有可能通過結合ACE2直接進入骨骼肌細胞并在細胞中大量增殖,引起橫紋肌溶解。
2.2 過度炎癥反應導致橫紋肌溶解
SARS-CoV-2的S蛋白具有較強的免疫原性,可以刺激機體的免疫系統產生特異性和非特異性免疫反應[38,40]。據Guan等[4]統計,中國1 099例COVID-19患者中有914例(83.2%)出現低淋巴細胞血癥。COVID-19患者血漿中多種炎癥因子如白細胞介素(interleukin,IL)、粒細胞集落刺激因子(granulocyte colony-stimulating factor,G-CSF)、腫瘤壞死因子α(tumor necrotic factor alpha,TNF-α)和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ascular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等水平明顯升高,而COVID-19危重癥患者體內的炎癥因子水平顯著高于普通COVID-19患者,更容易發生多器官功能損害且預后更差[44-45]。血清IL-18的水平與肌酸酐、轉氨酶、肌鈣蛋白等炎癥指標及患者疾病的嚴重程度呈正相關。COVID-19患者血清IL-18水平越高,病情越嚴重,預后也越差[46]。另外,Takahashi等[47]研究發現,男性和女性患者對SARS-CoV-2感染產生的免疫反應不同,男性血漿炎癥因子IL-18、IL-8、趨化因子5(chemokine ligand 5,CCL5)及血液中非典型單核細胞水平均顯著高于女性患者,女性患者的CD8+T細胞活性高于男性患者。較弱的T細胞反應與男性患者的年齡呈負相關,與較差的預后相關,而在女性患者中則沒有這種相關性。相比之下,在女性患者中非特異性免疫細胞因子水平較高與病情惡化有關,水平越高預后越差,而在男性患者中則沒有這種相關性。男性和女性均容易感染SARS-CoV-2,在中國1 099例COVID-19患者中,女性患者占41.9%[4],但是男性患者的病死率和重癥率明顯高于女性[48-49]。作者統計的28例SARS-CoV-2感染相關橫紋肌溶解癥患者中,男性患者24例,占85.7%,其中19例出現AKI,AKI發生率顯著高于女性,提示男性患者對SARS-CoV-2的免疫應答反應更強烈,炎癥損傷更重。另外,CRP是血漿中一種急性時相反應蛋白,正常人血清中含量極微,但是在各種急性炎癥發作后迅速增加,能夠激活補體和加強吞噬細胞的吞噬而起調理作用,在宿主對感染的防御反應、對炎癥反應的吞噬作用和調節作用中發揮重要作用,常作為急性炎癥反應的重要指標。作者統計的大部分SARS-CoV-2感染相關橫紋肌溶解癥患者血清CRP水平明顯升高,部分患者對糖皮質激素治療很敏感,經甲基潑尼松龍和羥氯喹治療后,肺部炎性浸潤迅速減輕,血CK水平很快回落至正常水平[27]。這些結果表明SARS-CoV-2感染后可以引起機體產生過度免疫反應,大量的炎癥因子持續釋放,免疫失調和細胞因子風暴(cytokine storm)引起的過度炎癥反應可能是導致組織損傷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導致橫紋肌溶解的重要因素。
2.3 肌肉長時間缺氧導致橫紋肌溶解
ACE2在血管內皮細胞和平滑肌細胞中高表達,心血管系統很容易被SARS-CoV-2攻擊。當冠狀病毒的S蛋白與血管內皮細胞的ACE2結合后,病毒進入細胞大量復制,可能導致大量內皮細胞死亡和毛細血管滲漏,觸發大量促炎癥細胞因子和趨化因子的產生[40]。同時SARS-CoV-2引起ACE2脫落和表達下調,導致RAS功能失調,進一步加重炎癥反應及增加血管滲透性,導致血液濃縮、血管內微血栓形成,引起供血部位組織水腫、骨筋膜室綜合征及橫紋肌溶解[9,24]。血漿D-二聚體是在血栓分解過程中由纖溶酶裂解纖維蛋白而產生的片段,D-二聚體水平升高提示有血栓形成傾向,需要進行抗凝治療。作者統計的28例SARS-CoV-2感染相關患者中有17例出現血漿D-二聚體水平升高;重型、危重型COVID-19患者可見D-二聚體升高、外周血淋巴細胞進行性減少、炎癥因子水平升高;全身主要部位小血管可見內皮細胞脫落、內膜或全層炎癥;血管內有混合血栓形成、血栓栓塞及相應部位的梗死及微血管內透明血栓形成[50]。這些結果提示,血液循環中病毒粒子侵犯血管內皮細胞導致的血管壁炎癥反應和血管內血栓形成可能會引起骨骼肌長時間缺血缺氧,進而發生細胞壞死和凋亡,這可能是導致橫紋肌溶解的機制之一。
3 SARS-CoV-2感染相關橫紋肌溶解患者AKI的發生機制
AKI是橫紋肌溶解癥的嚴重并發癥,28例SARS-CoV-2感染相關橫紋肌溶解患者中有20例出現了AKI,發生率高達71.4%。目前對SARS-CoV-2導致AKI的機制還不十分清楚,根據已有的文獻資料可以推測:COVID-19橫紋肌溶解癥患者AKI的發生是多個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Su等[51]對26例死于COVID-19的患者的腎組織進行了病理檢查,結果發現所有患者都出現不同程度的彌漫性急性腎小管損傷(acute tubular injury,ATI),表現為近端小管上皮細胞變性,刷狀邊界消失或空泡變性,管腔內可見到細胞碎片或壞死、脫落的上皮細胞。電鏡下可以觀察到近端腎小管上皮細胞和腎小球足突細胞中有簇狀的球形冠狀病毒樣顆粒和棘突狀的刺蛋白,部分足突細胞呈空泡樣變性,從腎小球毛細血管基底膜脫落。腎小管上皮細胞中的球形顆粒經免疫熒光染色證實為冠狀病毒顆粒。這一發現有力地證明,SARS-CoV-2可以直接侵犯腎小管上皮細胞和腎小球足細胞導致AKI或蛋白尿的發生。另外,腎間質充血、腎小管周圍毛細血管及腎小球毛細血管腔內有紅細胞聚集甚至堵塞管腔及血管內皮損傷的病理現象較常見,部分患者腎小球毛細血管袢中有少量節段性纖維蛋白血栓形成,近端腎小管細胞內ACE2表達上調,免疫熒光染色可以檢測到腎組織內非特異性IgM和補體C3蛋白,部分患者腎小球系膜區和毛細血管壁上檢測到IgA,電鏡下可以觀察到毛細血管壁上散在分布的呈駝峰狀的補體C3蛋白,有1例患者腎組織活檢檢測到毛細管內節段性顆粒狀IgG,這些結果提示免疫炎癥反應引起的腎血管內皮細胞損傷和血栓形成可能導致患者腎血流量減少及腎小球濾過功能下降,從而損傷腎功能[51]。橫紋肌細胞溶解后細胞內大量內容物釋放入血液循環,血液中的鉀離子、肌球蛋白、CK及乳酸等水平顯著升高,導致電解質紊亂、乳酸血癥及高肌球蛋白血癥。當肌球蛋白水平超過血漿結合能力時會通過腎小球濾過經尿液排出,形成濃茶樣尿液。大量的肌球蛋白會沉積在腎小球中,堵塞腎小管,從而產生腎毒性和AKI[12]。Su等[51]發現,4例臨床上出現血尿的COVID-19患者的腎小管上皮細胞中可以檢測到含鐵血黃素顆粒,其中3例腎小管內可以見到含鐵血黃素鑄型同時伴有磷酸肌酸激酶水平的顯著升高,提示患者發生橫紋肌溶解,肌球蛋白沉積堵塞腎小管,導致AKI。
4 SARS-CoV-2感染相關橫紋肌溶解癥的預防和治療
橫紋肌溶解癥是COVID-19的罕見并發癥,但是如果不能及時發現和治療,很容易引起AKI,使病情惡化,增加救治成本和死亡風險。橫紋肌溶解癥的臨床癥狀與疾病的嚴重程度相關,輕者可以只是血清CK和血漿肌球蛋白顯著升高,重者可以有典型的肌痛、尿色深和肌無力表現,但是只有不到10%患者出現上述三聯癥狀[12]。乏力和疲勞是COVID-19的常見癥狀,容易掩蓋橫紋肌溶解癥的癥狀,所以臨床診療過程中建議將血清CK作為住院COVID-19患者常規檢測指標之一進行動態監測。對于無呼吸系統典型癥狀或胸部X線檢查無典型病變、但有與COVID-19患者密切接觸史或疫區旅行史的輕癥患者或普通COVID-19患者,如果出現全身虛弱無力,腹部或上、下肢等部位疼痛時,要高度警惕橫紋肌溶解癥的發生,及時檢測血清CK和肌紅蛋白的水平,以便于早期發現和治療。
COVID-19合并橫紋肌溶解癥的治療措施除了針對呼吸道癥狀和病毒感染等對癥支持治療外,主要是積極的液體復蘇,糾正酸堿失衡,必要時給予利尿劑治療以保持足夠的尿量和腎清除率,阻止肌球蛋白等細胞內容物的持續釋放,防止AKI和嚴重的代謝紊亂及電解質失調的發生[12]。雖然早期給予大量靜脈補液是恢復腎灌注和防止AKI的常規治療方法,但并非所有患者都適合大量靜脈輸液,激進的補液可能會導致患者體內水負荷過多及發生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的風險。Suwanwongse 等[7]建議對患者進行小劑量靜脈輸液(即250 ml),并進行密切的臨床觀察,連續監測血氧飽和度以及血清肌酐和CK水平。如果患者的血清肌酐水平升高,應重復小劑量補充液體。Alrubaye等[15]推薦采用下列方案對有輕度呼吸道癥狀COVID-19合并橫紋肌溶解癥的患者進行治療:(1) 在血壓為100/60至120/80 mmHg的情況下,開始使用大劑量的生理鹽水;(2) 以150 ml·h-1的速率給予乳酸林格液維持治療,同時密切監測血氧飽和度、尿量、血清電解質以及CK、肌酐和轉氨酶的水平;(3) 如果患者的CK、肌酐水平和低血壓狀況繼續惡化但沒有出現急性心力衰竭的癥狀,則除乳酸林格液維持治療外還應補充少量生理鹽水。如果患者出現AKI、高鉀血癥、嚴重酸中毒或利尿劑治療無效的肺水腫或水負荷過多時,則要盡早給予血液凈化和連續性腎替代治療(continuous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CRRT)[50]。
5 結 語
SARS-CoV-2感染所導致的COVID-19是以呼吸道受累為主要表現的呼吸道傳播性疾病,越來越多的臨床資料表明COVID-19是一種多器官系統性疾病,其發病機制尚不清楚。根據已有的研究結果推測病毒通過識別和結合ACE2進入宿主細胞并在細胞內大量復制,引起細胞損傷變性、甚至壞死,釋放出細胞內容物,產生炎癥反應;同時通過刺激機體產生特異性和非特異性免疫反應,導致免疫失調和細胞因子風暴形成,進一步加重炎癥反應和組織損傷。COVID-19呼吸道以外的并發癥有神經系統損傷、心血管系統損傷、消化系統損傷、泌尿系統損傷及骨骼肌系統損傷等等。橫紋肌溶解癥是COVID-19的一種罕見并發癥,由于其臨床表現不典型容易被漏診,但是治療不及時容易導致AKI和病情惡化,給臨床診治帶來極大挑戰,因此在臨床診治過程中需要引起重視,有必要將血液CK作為常規的檢測指標之一進行動態檢測以便于早發現和及時治療。SARS-CoV-2感染相關的橫紋肌溶解機制仍不明確,治療上主要是補液、糾正酸堿失衡和電解質紊亂及對癥支持治療。有效的隔離措施和積極開發疫苗進行主動免疫是預防COVID-19流行和橫紋肌溶解癥并發癥發生的最重要措施。下一步亟待解決的問題是明確COVID-19的發病機制和治療靶點,以便盡早研發出高效價的特異性疫苗和治療藥物,減少并發癥的發生和病死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