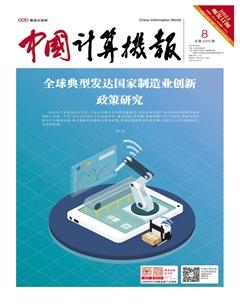全球典型發達國家制造業創新政策研究

科技與產業更加交織互促,產業在創新中的作用顯著提升,從科學發現到產業化落地的周期在持續縮短,“科技—產業”交互迭代效應正在加速形成。集成電路、傳感器、智能網聯汽車、光信息、智能電網等新興產業蓬勃發展,技術更新和成果轉化更加快捷,持續創造新市場和新機遇,給經濟社會帶來根本性、全局性影響。
基本形勢
(一)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演進,創新生態系統建設成為全球競爭的關鍵。近些年來,全球進入了創新密集期,世界范圍內的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快演進,制造業的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導致制造模式理念、技術體系、價值鏈發生重大變化。制造業創新的主體越來越多元,創新鏈條更加靈巧,創新正在不斷突破行業、地域、組織、技術的界限,創新模式越來越多樣,跨產業、多領域創新日益成為發展趨勢。以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第五代通信技術等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加速突破應用,帶動幾乎所有領域發生了以智能、泛在、綠色為特征的群體性產業變革。
科技與產業更加交織互促,產業在創新中的作用顯著提升,從科學發現到產業化落地的周期在持續縮短,“科技—產業”交互迭代效應正在加速形成。集成電路、傳感器、智能網聯汽車、光信息、智能電網等新興產業蓬勃發展,技術更新和成果轉化更加快捷,持續創造新市場和新機遇,給經濟社會帶來根本性、全局性影響。
(二)全球創新實力格局不斷加快重塑,圍繞制造業創新的競爭已成為新焦點。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主要發達國家深刻反思經濟“脫實向虛”發展模式,紛紛調整戰略方向,重新聚焦發展實體經濟,通過實施“再工業化”戰略,集中發力高端制造領域,持續加大創新力度,以創新作為制造業振興的戰略支點。美國、歐盟、日本等發達經濟體在信息技術、人工智能、區塊鏈、網絡安全、高端裝備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車等重點領域不斷加強戰略部署,在研發稅收減免、知識產權保護、政府公共采購、促進技術出口等方面支持企業開展技術創新,利用創新進一步刺激產業增長,提高國家競爭力。例如,美國2018年10月發布《國家先進制造業領導戰略》,提出發展和推廣新的制造技術、教育和培訓制造業勞動力,以及擴大國內制造業供應能力;此外,英國2019年5月發布《國際研究和創新戰略》、德國2019年2月出臺《國家工業戰略2030》以便在未來產業中占據主導地位。
與之對應的是,中國、俄羅斯、印度等發展中國家也在工業技術創新上取得了明顯進步,部分新興經濟體綜合國力的快速提升,正引發一些發達國家警惕,使得新興經濟體與發達國家的關系逐漸由戰略合作向戰略博弈轉變,突出表現為主要發達國家都在限制外資在敏感領域的投資、加強技術出口管制、強化供應鏈安全可控等。例如,美國2018年10月簽署《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2018年11月出臺《出口管制改革法》等,綜合運用國家安全、關稅、國際規則等多種手段和借口,意圖制約新興經濟體創新型企業和高技術產業創新發展。歐盟2018年11月通過了關于審評海外直接投資對于國家安全威脅的法律提案,把芯片、通信、人工智能、醫療服務、生命科學等領域放到投資核查的范圍中,通過限制外國投資來確保本國對關鍵技術產業的自主可控。
(三)中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面臨多重挑戰,對制造業創新提出了更高要求。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也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戰略支撐和根本要求。經過長期努力,我國制造業創新發展成就顯著,一些重大科技成果進入世界先進行列。但是,我國制造業創新能力與經濟實力還不相稱,與發達國家相比,在創新機制、創新實力和創新能力方面都還有一定的差距。當前,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社會發展面臨著鞏固全面小康、應對人口老齡化、維護社會安全、保障人民健康等多方面挑戰,我國制造業的高質量發展關系到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全局,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要求愈加迫切,需要依靠創新為經濟發展注入新動力。我們必須發揮好科學技術對產業升級的催化賦能作用,通過實施制造業創新,加快實現科技與產業的并行演進、融合創新,從而實現產業發展動力的根本性變革,真正依靠創新引領和驅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
發達國家制造業創新政策概述
創新戰略頂層設計
1.美國
(1)美國制造業創新政策管理體制。美國制造業創新政策的科技管理體系由總統科技顧問委員會(PCAST)、總統科技助理(ASTP)、國家科技委員會(NSTC)、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OSTP)構成,是以總統辦公室為核心的制造業創新戰略政策的“四駕馬車”。“四駕馬車”跨領域跨部門整合國家的制造業創新資源,把關總體戰略計劃,確保政府能夠充分發揮領導職能和牽引作用。
總統科技助理(ASTP)在一屆總統任期下兼任OSTP主任。此職位在冷戰末期和后冷戰時代確保了美國在重點技術領域優勢的擴大和保持。
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OSTP)是總統行政辦公室與聯邦和非聯邦科技機構的聯絡樞紐,從美國工業科技領域的全局出發提供國家制造業創新發展的整體構想和措施,并適時發布《美國創新戰略》報告。2015年的報告將建設創新型政府推動私營部門創新與大眾創業創新列為政府的首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OSTP的歷任科技CTO為總統親自提名。
國家科技委員會(NSTC)具體組織協調聯邦機構中的制造業創新政策和具體事務。2018年10月,NSTC的先進制造委員會發布《美國先進制造業領導力戰略》,列出五大重點技術和三大產業發展目標,旨在提升和擴大美國的先進制造的國際競爭力優勢。
總統科技顧問委員會(PCAST)負責對重大的制造業創新問題開展咨詢,主要由學界、工業界和科研機構的一些有代表性的杰出專家組成。2012年起PCAST預算由OSTP轉為美國能源部劃撥,但具體工作仍由OSTP進行領導。
(2)美國制造業創新戰略頂層設計一覽。總結和對比近十多年的美國制造業創新政策設計,美國政府結合國家產業創新發展的重要需求制定宏觀計劃方向,在推動制造業創新頂層設計中發揮重要作用。2009年12月,美國總統行政辦公室發布《重振美國制造業框架》,提出要加大政府資金對于新興技術和產業化的扶持力度。2015年10月,美國總統行政辦公室、國家經濟委員會和科技政策辦公室聯合發布《美國創新戰略》,強調了以下九大戰略領域:先進制造、精密醫療、大腦計劃、先進汽車、智慧城市、清潔能源和節能技術、教育技術、太空探索和計算機新領域。2012年,奧巴馬政府發布了《先進制造業國家戰略計劃》。時隔6年后,2018年美國特朗普政府再次發布《美國先進制造業領導戰略》。該報告展示了新階段美國引領全球先進制造的愿景,提出通過發展和推廣新的制造技術;教育、培訓和匹配制造業勞動力;擴大國內制造業供應鏈能力三大任務,確保美國國家安全和經濟繁榮。
2.英國
(1)英國制造業創新政策管理體制。1915年,英國成立科學和工業研究部,管理政府實驗室。1918年之后,為解決一戰之后經濟停滯不前,英國議會成立了科學技術辦公室,負責評議政府提交的重大科研與改革方案。20世紀80年代,為扭轉輕視技術轉化的現象,撒切爾政府(1979—1990年)進行了一系列改革促進科技轉化為生產力,形成以市場為導向,向私營企業傾斜的科技政策體系。1992年,英國內閣成立科學技術辦公室(OST),此后英國的科技政策的核心是科技辦公室,由政府首席科學顧問負責科技政策與管理事務。為了科技政策與工業政策更加協調統一,1995年OST由內閣又并入貿易與工業部,保持政府首席科學顧問的職能,獨立向內閣提出科學技術發展咨詢建議。工貿大臣兼任國家最高科技委員會主席,作為最高科技決策的咨詢機構。同時為了和產業結構發展相結合,英國的科研預算理事會和商業、創新與技能部(BIS)在政府科技經費預算及管理體系中也處于十分重要的位置,也擁有下設政府科技辦公室,專門負責協調研究理事會總會與七大研究理事會的管理、預算和經費撥款。自1994年以來,英國皇家科學委員會首次發布了白皮書《完成我們的潛能——科學、工程和技術戰略》。此后,1998年、2000年和2001年的三份政府白皮書都以創新為主題。
(2)英國制造業創新戰略頂層設計一覽。英國內閣與地方政府協調推進工業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出臺“創新與研究戰略”,全面推動創新生態系統的發展。為了在全球創新經濟領域取得成功,2011年12月,英國政府出臺了名為《以增長為目標的創新與研究戰略》,提出政府要從鼓勵創新型企業等5大方面采取措施驅動經濟發展。2012年9月,英國政府發布了《英國產業戰略:行業分析報告》,指出政府要與產業界建立長久的戰略伙伴關系,共同培育商業發展機會,刺激經濟增長,創造就業,英國政府陸續發布了11個重點產業的發展戰略規劃,采取長期的、“政府一盤棋”的辦法支持產業發展,為投資和增長增添信心。英國進入“脫歐”進程后,制造業創新面臨諸多新挑戰,政府采取一些改革舉措應對變化。2017年4月頒布《高等教育與研究法案》,成立英格蘭研究署,承接原英格蘭高等教育撥款委員會資助大學科研活動和知識轉移的職能;組建國家級科研資助機構——英國研究與創新署(UKRI),由研究理事會、英國創新署和英格蘭研究署共同組成,匯集60億英鎊科研預算,將政府從基礎研究到商業創新的投資納入清晰統一的戰略框架,該機構已于2018年4月正式運行。2017年底英國政府公布了《現代產業戰略:構建適應未來的英國》白皮書。產業戰略由“五大基礎”、“巨大挑戰”“行業計劃”及具體政策組成,具有共識性、延續性、創新性等特點,政府資源得以保障,得到產業支持。推進地方政府的產業創新戰略和機制建設有序進行。
3.德國
(1)德國制造業創新政策管理體制。德國研究和創新體系的宏觀咨詢決策協調機構主要包括科學和人文理事會(WR)、科學聯席會(GWK)、研究與創新專家委員會、高科技論壇、研究對話等。
1957年成立的科學人文理事會(WR)的職能是負責對德國的萊布尼茨科學聯合會、馬普學會、亥姆霍茲聯合會、弗勞恩霍夫協會進行評估。1970年成立的科學聯席會(GWK)的前身是聯邦和各個州的教育規劃與科研委員會(BLK),將教育與研究促進問題提供給對應的政府機構首腦。2008年成立科學聯系會(GWK),取代BLK。GWK的成員負責增強德國科研部門的國際競爭能力,就跨區重大的科研項目基礎設施和計劃決策進行溝通。聯邦政府在2006年8月23日成立研究和創新專家委員會(EFI),其使命是綜合分析德國創新體系的優劣和不足,就產業創新和德國創新體系上的問題向德意志聯邦政府提供科學建議并提供報告。同時,各州政府在制造業創新服務方面依據《聯邦德國基本法》負責50%的公共研發支出。德國的科研決策體系層級分明,依照公共管理制度設計,強調從頂到底的貫徹執行,最終作用于德國制造業的中小企業和大型跨國公司。
(2)德國制造業創新戰略頂層設計一覽。除了提出工業4.0之外,2019年2月5日,德國聯邦經濟事務與能源部發布《國家工業戰略2030》(Nationale Industrie strategie2030)計劃草案。該戰略旨在提高德國的經濟和科技競爭力和創新能力,提供網格化全維度的工業融合,確保或奪回其在相關工業領域國際市場上的領先地位。
4.日本
(1)日本制造業創新政策管理體制。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經濟騰飛以來,日本著力將政府財政和企業社會資本投入到制造業質量精細化和科技振興計劃中。日本的國家科技管理體制變遷自2001年始,其科技和制造業產業相關的政策從由“科技廳”和“內閣科技會議”負責變換為“綜合科學技術會議”來統籌日本各部委,主要負責提出制造業創新的新政策。同時將文部省和科技廳合并,發展起來了文部科學省。發展新產業、制造業創新領域的相關預算的主體部分由文部科學省負責進行管理。
與此同時,日本政府還設立了具有長遠戰略意義的科研政策。比如日本政府在2007年和2008年分別成立了綜合海洋開發戰略總部和宇宙開發戰略總部。2013年增設了健康醫療戰略總部,2020年設立防衛省宇宙作戰部隊,這些總部設立之后陸續出臺了海洋基本計劃、能源基本計劃和太空國家安全基本計劃等科技戰略方針政策。
2013年日本內閣提出創新創造計劃項目(SIP)和“創新性科研開發推進項目”設立綜合科學技術會議和創新理事會,日本首相作為委員理事會主席,分為內閣部分和執行部分。2019年的委員理事會主席為首相安倍晉三,一般由15個來自各個科研機構和部門的相關人士參加。
(2)日本制造業創新政策制定的思路與機制。日本制造業創新政策制定主要分為四步,先由內閣總理大臣提出向綜合技術創新聯席會議提出研討的議題和需求。之后由綜合制造業創新會議組織專家,就新一期科學技術基本計劃的制定舉辦專家研討會,圍繞議題創新政策的方方面面,聽取其他業界專家學者的意見和問題,最終形成基本計劃文件,并對所形成的文件內容進行答辯。新一期科技基本計劃將由政府內閣決議來通過。最終決議通過之后,各省廳分別按照計劃內容推行新的制造業創新政策。以《2019日本綜合創新戰略》為例,日本制造業創新政策的制定主要分為三個階段:一個是對實時狀況進行調研分析,并總結研究的重點;二是分析確定當年的發展的重點;三是將重點工作分解到具體的領域。
新興產業創新政策
1.人工智能
(1)美國。2019年2月,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聯邦政府要“全面投入資源”重點發展人工智能(AI)。2020年8月26日,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和能源部(DOE)宣布在全國建立12個新的AI和QIS研究與開發(R&D)機構,資助總價值超過10億美元。其中NSF每年在人工智能活動上的投資超過5億美元,并且是美國聯邦非國防AI研發的最大推動者。截至2020年9月,美國政府機構在非國防AI研究方面支出9.735億美元。
(2)英國。為了搶占“人工智能AI”的領先地位,英國將人工智能產業放置于國家高度的制度層面,2019年英國議院成立人工智能委員會,出臺人工智能行業協議。到2027年,計劃將增加研發支出達到GDP的2.4%,從長遠來看,AI研發支出將增加到3%,以資助計劃7.25億英鎊的投資開始在新的產業戰略挑戰中獲取價值創新。
(3)德國。2018年11月,德國聯邦政府出臺《聯邦政府人工智能戰略要點》,將人工智能正式升級為國家戰略,具體做法為努力夯實人工智能功能平臺建設,促進人工智能與“工業4.0”深入對接。
(4)日本。2019年日本發布《AI戰略》強調云工業概念,將開發AI技術與現有的工業體系深度結合,同時注重傳統的機器人技術的升級和迭代。2019年6月,日本政府出臺《人工智能戰略2019》,旨在建成世界上最能培養人工智能人才的國家,并引領人工智能技術研發和產業發展。
2.5G領域
(1)美國。美國國務院表示,5G政策不僅事關通信網絡發展,更事關國家安全和價值觀。白宮發布的《2020財年政府研究與發展預算優先事項》指出,要加快指導聯邦機構支持5G無線網絡的開發和部署,包括“優先考慮研發以管理頻譜,保護網絡并增加對高速互聯網的訪問”。
2018年9月28日,白宮5G峰會上出臺了“促進美國在5G技術方面的優勢”計劃,旨在將更多頻譜推向市場,更新基礎架構政策并鼓勵私營部門對5G網絡進行投資,并對過時的法規進行現代化改造,以充分發揮5G技術的潛力并確保美國持續的競爭力。
(2)德國。2017年7月,德國聯邦交通和數字基礎設施部發布《德國5G戰略》。德國致力于成為5G網絡及應用的領導國家,主要措施包括:全面優化現有實驗場的基礎設施條件;建立起可持續性的競爭市場,設計出更多人性化的5G網絡應用;更多借鑒世界各國的經驗和知識,加強與其他國家合作。
3.新能源汽車領域
(1)德國。2009年德國《國家電動汽車發展規劃》明確了電動汽車的國家戰略性地位,致力于增強德國在電動汽車領域的國際競爭力,推動德國成為電動汽車領先市場,實現能源與環境政策目標。具體做法包括成立國家電動汽車平臺(NPE),“政產學研”合力共同推動電動汽車發展。2010年2月,為更好地促進政府部門間形成合力,由德國交通部和經濟部牽頭,成立“電動汽車聯合機構(GGEMO)”,而后教育部和環境部也加入其中。
(2)日本。日本內閣于2008年7月發布《創建低碳社會的行動計劃》,提出混合動力及清潔燃料汽車概念,力爭到2020年,下一代汽車在新車銷量中的占比達50%。2010年發布的《下一代汽車戰略(2010)》是對該文件的進一步細化和落實。2014年11月,日本經產省發布《汽車產業戰略(2014)》,提出要“加速下一代汽車的普及,努力實現《下一代汽車戰略(2010)》的普及目標。2018年3月,日本經產省組織成立“汽車新時代戰略委員會”,提出了《面向2050年xEV戰略》,不再強調包括清潔柴油汽車等的“下一代汽車”,而是提出“xEV”概念,包括BEV、PHEV、HEV、FCEV等4類電動汽車,強化了對“電動化”的支持。
對策建議
(一)完善政府創新治理頂層設計,進一步提升整體創新效能。目前我國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必須進一步完善政府制造業創新治理的頂層設計,厘清相關政府機構的分工與職責,清理、廢除不適應創新發展需求的各項法律法規與相關制度,調整并完善相關的人、財、物管理制度,使之適應創新體系建設、研發以及科技成果高效轉化的要求。瞄準國際科技前沿加強基礎研究,突出關鍵共性技術的研發與產業化,強化知識產權保護,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從根本上增強我國經濟的創新力和競爭力。
(二)集中資源發揮制度優勢,增強產業自主創新能力。一方面,要鼓勵骨干企業制造業創新,加大制造業創新獎補力度,鼓勵企業加大技術創新投入,創建省級以上企業技術中心、重點實驗室等各類研發平臺。支持有條件的企業創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工作站。另一方面,要深化產學研協同創新,引導企業與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建立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發揮技術人才優勢,開展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培育新興創新產業和戰略高新產業,打造“雙創基地”,推動骨干企業研發一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和重點新產品,形成市場競爭力。
(三)大力創新人才管理制度,加快形成競爭新優勢。創新我國人才引進與管理制度,制度要具有國際競爭力,制度設計要有人才退出機制;嚴格按照制造業創新規律設計、制定高校、院所、企業等不同崗位科研人員的績效分類評價體系,把科研人員的精力和時間聚焦在深入研究原創技術與關鍵核心技術上。人才是制造業創新體系中最活躍的因素,人才管理制度要允許科技人員自由流動,創造出寬松、無障礙、人盡其能的工作環境,使研發人員的創新潛力與積極性得到充分發揮,對做出突出貢獻的科技人員給予重獎。
(四)強化產學研協同創新,打通科技到產業創新通道。探索產學研合作有效機制,引導支持企業、科研機構、高校等建立以利益為紐帶、緊密合作的研發團隊和創新網絡,推動高校、研究機構和企業間的深度協同和跨界融合創新,并探索建立科學合理的利益共享、風險共擔合作機制。進一步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充分發揮國有龍頭企業在技術創新體系中的引領示范作用,鼓勵民企建立研發機構、實驗室和中試基地。
(五)充分整合創新資源,加快制造業創新中心網絡化布局。為應對解決制造業創新體系中存在的基礎研究與產業化之間脫節的問題,圍繞國家部署的重點領域,以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為依托,充分整合企業、科研院所、高校以及金融資本等資源,有序推進國家制造業創新中心建設。同時,鼓勵制造業基礎雄厚、研發創新實力強的省市探索創建一批區域級制造業創新中心。依托兩級制造業創新中心,最終形成以創新中心為核心節點的多層次、網絡化制造業創新體系。
(六)主動發聲,提升我國制造業知識產權國際話語權。為貫徹新發展理念,推進制造強國建設,提升我國制造業知識產權國際話語權,我國要進一步加強國際發聲,支持科研院所、行業協會、產業聯盟、企業等在國際研討會、行業大型會議等場合,積極宣傳我國制造業知識產權保護、運用成效;圍繞制造強國建設重點,開展重點領域知識產權風險分析與預警防范;由被動應對逐步轉向正面防御與主動發聲,支持相關機構研究發布國內外知識產權保護相關情況報告;強化企業產權意識,做好知識產權保護工作,創造良好營商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