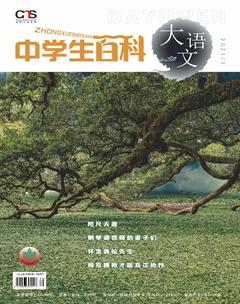協
張世程

“眾人同力”,往往需要把力用在同一方向,這樣才能產生最大的合力,比如曾經的拉纖就是這樣,流傳至今的龍舟賽也是這樣。《淮南子》說:“今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后亦應之……”魯迅先生在《且介亭雜文·門外文談》里也寫道:“我們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連話也不會說的,為了共同勞作,必須發表意見,才漸漸的練出復雜的聲音來。假如那時大家抬木頭,都覺得吃力了,卻想不到發表,其中有一個叫道‘杭育杭育……”這“邪許”就是“舉重勸力之歌”,這“杭育杭育”就是原始人的“創作”。“歌”“創作”是為了凝聚人心,眾人同力。于是,我們仿佛還聽得到河邊的“嗨喲嗨喲”和汨羅江上“咚咚鏘,嗨”的號子,以及“邪許邪許”“杭育杭育”。
當然,到現代社會,我們很多時候就把這個“同力”交給機械了,比如高鐵“動車組列車”,作為現代火車,若干帶動力的車輛(即動車)排成一列,一齊同向用力,跑出了領先世界的速度。而在非常時期,比如面對災害或者疫情,我們同樣需要這種一聲號令之下的同向用力。比如新冠疫情突如其來,我們無須爭論戴口罩的利弊,大家宅家做貢獻,醫護人員則逆行擔當;某個地方突發疫情,幾天內千萬人接受核酸檢測,有效防控;暫時犧牲經濟,接下來是經濟大復蘇,我國成為唯一的經濟正增長的大國。而在平時,我們更多需要的是“同心協力”,心同了,然后就分工使力,通力協作,在于平衡,在于和諧,在于融洽,正好比“聲律相協而八音生”的壯麗篇章。
觀電影《奪冠》,看中國女排走過的道路,20世紀80年代全國人民把“奪冠”看得多么重要,中國女排所奉行的就是“祖國至上,團結協作”。正如老教練說的:“心里頭有這個東西,就是女排精神,就是我們的國家。”想想那時,剛剛改革開放,中國還比較落后,中國人多么希望某一方面某一領域能有突破,能“奪冠”。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協作需要一種“精神”、一種“信念”、一種“信仰”來凝聚,老女排正是靠著“祖國至上”的信念而團結協作、奮力拼搏的。
作為個人,不管是什么身份,處于什么地位,應該懂得“每一個人都不是一座孤島”,應當懂得基于共同目標或共同命運的同心協力和通力協作,成為“大陸的一部分”(約翰·多恩)。唯有如此,這樣的“個人”才具備人格的完整性。
一個群體要成為“大陸”,一個人要成為“大陸的一部分”,無論是“眾人同力”,還是“同心協力”,都需要一個共同的目標或者理想,或者說一種共同的“信念”。一個團隊的共識是如此,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認同更是這樣。
大而化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其實也正是先圣所追求的“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的人格理想和社會理想。《書·堯典》有“協和萬邦”之語,它昭告世人,各國各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應是當今社會的常態,天下“協和”應是我們人類的共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