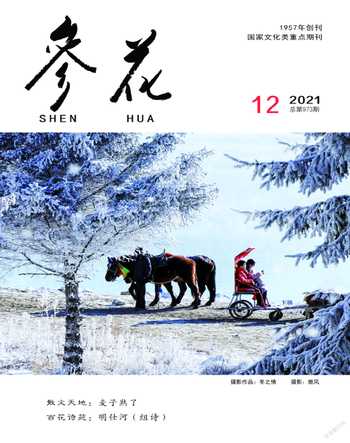《終條山的傳說》的形式與環境描寫分析
摘要:《終條山的傳說》是著名文學評論家李健吾的一部短篇小說。小說以神話為故事外殼,在敘事結構上呈現出內部遞進的線性發展與整體的環形結構的特點。在故事情節的敘述之外,小說也具有自然環境的人化與神化特性。這也體現出李健吾在創作上對語言與形式及個人風格的強調,本文就其形式與環境描寫加以分析。
關鍵詞:《終條山的傳說》 文學思想 環境描寫
一、引言
李健吾,筆名劉西渭,著名作家、戲劇家、文學評論家、翻譯家。但相較于評論、劇作和翻譯,李健吾的小說創作獲得的關注顯得較少,“他的小說雖然也有一些出色之作,卻被他的劇本盛名所掩蓋了,并沒有引起文藝界的足夠注意。”[1]而實際上,李健吾最開始即是以小說創作而嶄露頭角的。李健吾的小說創作始于20世紀20年代中期,先后出版過小說集《西山之云》《無名的犧牲》《一個兵和他的老婆》《壇子》《心病》和《使命》。1935年由魯迅編選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中選入了李健吾的《終條山的傳說》,并在導言中寫道:“……《終條山的傳說》是絢爛了,雖在十年以后的今日,還可以看見那藏在用口碑組織的華服里面的身體和靈魂。”[2]
二、神話傳說下的創作追求
神話是一種古老的文學體裁,也是文學的發源,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曾指出:“《漢志》乃云出于稗官,然稗官者,職惟采集而非創作,‘街談巷語’自生于民間。固非一誰某之獨造也,探其本根,則亦猶他民族然,在于神話與傳說。”“故神話不特為宗教之萌芽,美術所由起,且實為文章之淵源。”[3]19世紀末,歐洲為拯救過度工業化造成的人性扭曲,出現了神話與神話文學的復興。在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為拯救日趨腐朽的民族文化,也發現了神話在文學上的活力,這也引發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和創作成果。
實際上從中國神話的起源開始,中國的神話傳說一直就與時代、與現世連接緊密。“大羿、女媧、盤古、精衛、夸父、大禹,等等,他們并不是要做宇宙的主宰,而是或作為為民除害的象征,或作為征服某種勢力的精神代表。”神話是民族精神的最初記錄,是中華民族精神的原始表象,浸染著中華民族注重道德與崇尚實用的色彩,包含濃重的道德意識與教化意味,表現了人們在嚴峻的自然環境與復雜的社會條件下不屈不撓的抗爭精神。李健吾的《終條山的傳說》也具有這樣的彰顯作者構思與文學思想和體現作家創作觀的特點。
從李健吾發表的有關自身小說創作的后記中,可以看出他十分強調作品中的個人風格對創作的重要性,“我用藝術和人生的參差,苦自揉搓我渺微的心靈。作品應該建在一個深廣的人性上面,富有地方色彩,然而傳達人類普遍的情緒。我夢想去抓住屬于中國的一切,完美無間地放進一個舶來的造型的形體。”“從我曉得什么叫作文學創作以來,我把風格看作一種人生的質素,可以因人而異, 因書而異,不必篇篇雷同。不是人生之外另有什么風格。風格區別作者的個性,然而也區別作者自己的觀察和方法。合起來看,全是我。一篇一篇去看,是不同的我的經驗。這種風格明晰的觀念,實際扎根在一個深刻的心理的社會的分析。”從以上敘述中,能夠發現李健吾對創作中個人風格的注重。而對李健吾來說,在創作中拋開個人風格之外,還有一點非常重要的就是作品的形式。李健吾不止一次地在他發表的評論文章中指出:“但是我們最可惜的一件事,就是一般作家在作品形式上——如果這里有真實的內容——的不注意。”“我相信真的內容絕摘不掉好的形式:形式即內容。”在論林徽因的小說時,李健吾也講道:“形式和內容不可析離,猶如皮與肉之不可揭開。”綜上,李健吾的創作觀可以總結為對語言形式的重視和對個人風格的追求。而選取神話傳說這一文學題材,李健吾的創作思想則更能體現得淋漓盡致。下文就將在形式和語言上對《終條山的傳說》進行進一步分析。
三、內部遞進的線性發展與整體的環形結構
按有具體時間標志與有明顯故事情節為劃分標準,《終條山的傳說》中主要包含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以“有次”做起始,講述的是一個冒險的青年樵夫在失群之后獨自在終條山中過夜,等他的同伴們再次見到他的時候,他留下了“金頭,銀身,鐵尾巴!”的一個啞謎似的遺囑之后,就僵挺在地上死去了;第二部分的時間是接續第一部分“隔了許多年月”,主要敘述的是游歷者發現了終條山壁下的一個洞門,并描繪了這一洞門仙窟的怪異;第三部分是小說的主要部分,時間點明是“當光緒皇帝從京城避難到陜西,經過潞村的這一天”,其中的人物也有了名字——“張世芳”。這一部分講述的是農夫張世芳由城里歸家,夜晚不知為何到了仙窟洞口,在聽到洞中傳來“張世芳——挑去這里的燈花”之后大著膽子照著指示去做了,并且得到了五十兩贈銀并一直保守秘密到臨終前一刻。
第一部分的樵夫留下啞謎之后死去,給“終條山的傳說”留下了一條文字線索,引發的后果是所有樵夫都離開了這個“隱秘的怪所”;第二部分對仙窟洞門的描寫,是對“終條山的傳說”留下了關于奇異場所外部的直觀描繪,引發的后果是所有想搬走洞口石門的人都會遇到災禍;第三部分,通過描述張世芳的經歷,終于對“終條山的傳說”的隱秘做了一個敞開式書寫,將終條山的古怪之處展現在了讀者面前,而張世芳探秘之后導致的最后的結果則是“從此以后,永久,永久,那隱秘的石門還再未敞開。”
如以小說主要情節的第二部分為中點,則會明顯發現《終條山的傳說》在結構上的環形與對稱。在第一部分開始之前,作者點明了故事的發生地,潞村、運城、終條山。而在第二部分開頭,也再次點明了地點“潞村”,這是這一地點名稱出現的兩處。在第一個主要情節的末尾,青年樵夫在提到“金頭、銀身、鐵尾巴!”后即死亡。而在第三部分結束時,農夫張世芳在彌留之際,對妻子說出五十兩贈銀的來歷時,也提到“金頭,銀身,鐵尾巴”,分處于兩個部分末尾的“金頭,銀身,鐵尾巴”是文中兩次出現這句啞謎的地方,它們在出現之后都接續著主人公的死去。同時,啞謎也都未在敘述它們的部分得到解答。而如果要得到謎底則需要將小說與情節發展并無多大關系的收尾段落結合起來。
小說的起始部分為小說的第一到第三段,而小說結尾部分則是最后一段。在這兩個部分中,沒有具體人物與具體行動,沒有時間的流動感,可以單獨分作兩個部分。這兩個部分都以“如今”作為時間標志,書寫地是對“當下”情況(自然與社會狀況)的概括。開始部分從描寫順序來看,寫到的是:王屋龍門兩山、怒哮的黃河、河伯傳說與慘淡的環境;在這樣的環境中居住著的誠實不欺的百姓和他們的生活;當地食鹽歸官府與外國人協辦,靜穆的終條山。結尾部分如以描寫順序來看,則是:變成荒涼土堆的終條山;來到此地的外國人斷定有豐富的礦苗;城市的百姓和忙碌的官府;黃河激怒的喧號和自然物的無語平靜。
四、人化自然的反諷性
在情節發展之外,李健吾在《終條山的傳說》中著墨最多的是有關自然環境的描寫。在眾多文學理論家的論述中,環境對敘事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它也構成了故事的一部分。托馬舍夫斯基在《主題》一文中曾將作品的母題分為兩大類:靜態母題與動態母題,他將“對大自然、地點、情景、人物及其性格等的描寫”稱為靜態母題。巴爾特也將敘事文的最小切分單位——功能分為兩大類:功能和標志,其中表示地點、氛圍的單位屬于標志之列。在李健吾筆下,《終條山的傳說》中具有十分明顯的人化特點,如“貪睡的猛獅”般的高山,怒哮、疲倦、發出“緩長的嘆息”的黃河等,這些景物與小說中提到的“河伯”一起構成了“傳說”人化自然的特點,十分符合神話傳說題材自然人化神化的寫法。
下面選取幾個在小說中富有特色的描寫段落——
起始部分:覓食的虎狼聳起耳朵,倒曳垂尾,逃入巖穴,屏息以觀厄運降臨;沉濁的浪漩像狂笑似的跳舞,一陣陣鬼旋風卷起蘊慍的黃沙,打在兩岸;于是懸崖的石礫戰栗起來,有些軟軟的斜墜叢林,驚自己的奇游,有些卻砰砰地暈墜河心。一切景象都顯慘淡。
主要情節第二部分,關于石洞門前的描述:一座平巖突伸在洞上,如檐椽似的屏遮著落雨;離此不遠,一條小溪潺潺低唱,經過門前,水底淺鋪的沙礫像貓兒眼石的發光,一棵無年代的古松挺立溪旁,枝葉橫布空際,像浮云停在山腰;半熟松子滴在綠茵中,如由母懷轉就情人肩下的微笑,有些蛛網遠遠織在石罅,槍端,仿佛了然于洞門的怪秘。
第三部分中張世芳在夜晚行走時路過洞門:從谷縫吹出和平的微風,同他的新竹大褂相嘲戲。一排排的棗樹在道旁自傲地站著,垂下生青的小果;半山腰的白楊葉像鬼似的尖嘯,使四圍的酸棗樹只是顫擺。巖端斜懸著幾只松鼠,很疲乏地徹夜嘆息。
在這幾段主要的自然描寫之中我們可以發現小說自然環境的對稱式描寫:陰森——優美——可怖。除了這之外,我們也可以看出李健吾在描寫人化自然環境時是為了具體情節服務,起始部分的陰森是為了營造全文的氣氛;第二部分的仙窟描寫與古代仙窟有異曲同工的互文作用;第三部分則是將張世芳的心理通過可怖的環境烘托出來。但小說中自然環境描寫的功能也不止于此,這些環境描寫不止為具體情節服務,還為整篇小說的主題服務。
無論小說中的自然環境是陰森可怖還是美麗寧靜,都具有動態感,也都具有對小說中人物的反諷意味。在自然環境中,人物渺小而孤獨,無法對環境做出絲毫改變;同時,人物雖然懼怕自然,但自然環境在其中也是被人物漠視的,幾代樵夫村民都漠視著終條山的自然資源,農夫張世芳在窺見秘密之后也只是選擇了保持沉默不作為。在這樣的人與自然關系的反諷中,也更加突出了李健吾在創作中對語言的控制力和對現實以啟發的創作追求。
參考文獻:
[1]蹇先艾.我的老友和畏友:悼念李健吾同志[J].新文學史料,1983(2):148-149.
[2]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35.
[3]魯迅,撰.郭豫適,導讀.中國小說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作者簡介:白旭,女,碩士研究生在讀,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
(責任編輯 葛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