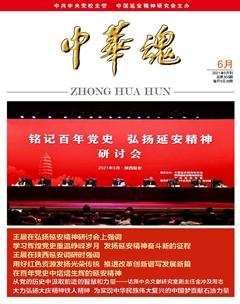甘獻年華逐紫煙
王磊

幽幽燕山腳下,翠翠官廳之畔,一座布滿彈洞的水泥碉堡隱藏在青青綠草之間。40年了,這里已經人跡罕見。平日里,只有遠處那不知建于何年的烽火臺與它共訴歷史的滄桑。但是,門口那斑駁銹蝕的大鎖,遠處那站如蒼松、目如鷹隼的警衛戰士,草叢里那隱約可見的條條小路都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它曾經的重要與輝煌。
2000年9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51周年慶典前夕,一位老人又來到這座老房子,充滿深情地望著嵌在墻壁上的一方紀念碑。碑文因久歷風雨,字跡已經顯得稍有模糊,但略加注意還是能看清楚:“第一顆原子彈的第一個爆轟實驗場,始建于1960年2月,同年4月21日打響第一炮。該場地一直使用到1964年初,為我國第一個原子彈的研制提供了寶貴的數據。我國從事核武器研制、實驗的科學技術人員、工人、干部、人民解放軍指戰員為我國掌握核武器立下了豐功偉績。”默念著這塊“爆轟實驗場紀念碑”上的碑文,老人的思緒又回到了幾十年前那炮聲隆隆的實驗場。這位老人,就是中國著名金屬物理學家、共和國“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陳能寬。
一
1955年1月15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作出了中國要發展核工業的戰略部署,中國核工業(包括核武器)的研制從此正式列入國家計劃,開始大規模運轉起來。
1956年第三機械工業部(后改名為第二機械工業部,簡稱二機部)成立,主管核工業的建設和發展。1958年1月,二機部九局成立,主要負責核武器研制和基地建設工作。1959年6月20日,蘇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提出暫緩向中國的核計劃提供任何形式的援助。隨之,蘇聯政府通知中國政府,蘇聯將撤走全部在華專家。截止到8月23日,在二機部工作的233名蘇聯專家全部撤走。毛澤東以他特有的氣魄說道:“我們要下決心搞尖端技術。赫魯曉夫不給我們尖端技術,極好!如果給了,這個賬是很難還的。”正是在這種大背景下,10月7日,二機部九局向部和中央請求選調高、中級科技干部106名,充實核武器研究工作,陳能寬在選調名單之列。
原子彈的研制,是一項浩大的工程物理系統工程。在豐厚扎實的理論研究基礎上,絕對不能缺少應用環節中的經驗積累。但當原子彈計劃進行到1960年時,理論準備已有了一定突破,而驗證理論所必需的試驗進行得并不順利。當得知陳能寬參與了核研究計劃后,時任九所一室主任、主要從事理論物理研究的鄧稼先興奮地對陳能寬說:“我現有的認識、參數和計算工具都無法單靠理論來解決至為關鍵的爆轟設計。你來了就好了,請你從實驗途徑來解決吧。”這也是當時王淦昌、彭桓武和郭永懷的共同看法。依據中國當時掌握的核武器爆炸原理,所有核武器都離不開炸藥。從雷管動作開始直到主裝藥爆轟作功,驅動并壓縮核材料,使核材料在極短時間內達到臨界值或超臨界值,最終發生核聚變或裂變,產生核爆炸,這一系列過程,都有十分嚴格的時空關系和物理狀態的匹配要求。正是核武器研制的需要,才促進了現代爆轟物理學和現代動態高壓物理學的迅速發展。然而在1960年,我國在爆轟物理方面的實踐經驗和學術沉積還近似于空白。很快,37歲的陳能寬被任命為九所第二研究室(即爆轟物理研究室)主任。
在筆者采訪陳能寬先生時,他反復強調“當時我們誰也不懂原子彈,大家都是摸著石頭過河”,當時手頭所掌握的,只有支離破碎的蘇聯專家留下的一點材料,然后便是零零星星的一些國外論文所透露的信息。這些東西可信度很低,有些國外論文提到的方程式、數據,根據中國科學家的論證基本是假的,陳能寬所做的就是從這些真假難辨的東西中找出一些靈感來。
1960年的夏天,陳能寬奔跑于河北懷來與北京之間。他在北京最主要的任務之一,是消化蘇聯專家在華設計的221廠2分廠各子項工藝平面圖以及設備材料清單,其中有注裝工房、組合件工房、組合件裝配工房、炸藥切割工房以及炸藥物理化學分析工房。這項任務,陳能寬交給了負責二室炸藥工藝組和物理化學分析組的室副主任孫維昌。
通過翻閱大量的圖紙材料,孫維昌等人了解了各子項工程的任務、性質以及聯系,但這只是一般炸藥工廠公開的信息,對涉及保密內容的具體資料,蘇聯專家在給中國方面提供的清單中并沒有列出來。了解這一情況后,陳能寬決定面對面地與蘇聯專家談一次,盡最大可能從他們的口中獲得更多的材料。在談話中,孫維昌一口氣向專家提出了20多個問題,如裝注工房里米哈伊洛夫融化爐里的是什么炸藥?壓裝工房200噸壓機壓制的是何種炸藥?炸藥組合件幾何結構是什么?切割炸藥是機械切割還是手工切割等問題。但蘇聯專家凡涉及炸藥名稱、炸藥性能以及工藝性等保密內容都不做正面回答,只是不斷地搪塞說“不用著急么,到時候會告訴你們的,到時候蘇聯政府一定會向中國政府提供有關資料的”。
陳能寬從這件事情上更加認識到蘇聯專家是徹底不能依賴了,一切都必須依靠中國人自己去努力。他把各個小組的科研人員召集起來,向他們介紹了情況,鼓勵大家不要氣餒,要立足自力更生,以創新的精神完成好自己的工作。
二
除了北京的圖上作業、理論研究,陳能寬的主要心思花在了17號工地的建設上,因為那里是一切理論研究工作的實驗場。1960年2月29日,河北懷來縣花園鎮附近的工程兵炸藥實驗場一角的炸藥實驗室及爆轟試驗場破土動工,為保密起見,這個爆轟實驗場被定名為“17號工地”。
陳能寬初到工地,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看上去十分嚴肅”,“經常一個人呆在屋子里計算”。其實,他的“嚴肅”是因為心中實在是沒底,又怎么笑得出來。從金屬物理轉向爆轟物理,雖然同屬于物理學范疇,但學科相互之間已經獨立了,像絕大多數中國第一代核科學家一樣,陳能寬可以說是“白手起家”。需要解決的第一個問題是“人”的問題。當時二室是一個剛組建的單位,人員來自國內各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員、大專院校的教師、工礦企業的技術人員,還有相當多的應屆畢業生。由于科研工作面寬,涉及學科比較多,各項工作都要從零開始做起,在最短的時間內把眾多門外漢領入核科學的殿堂。陳能寬親自給青年人上課講解基本的爆轟物理學研究方法,他推薦青年們讀兩本書:一是俄文版的《爆轟物理》,二是趙忠堯編寫的《核物理基礎知識》。陳能寬特別叮囑青年們要充分利用圖書館的作用,多去查閱一些美、英等國的相關文章和書籍。陳能寬帶領一批青年人將美、蘇等國的資料做成卡片然后進行分析,這既可以避免研制工作中走彎路又通過言傳身教使青年人迅速成長起來。
17號工地面臨的眾多困難之一就是如何克服惡劣的自然環境。試驗場地處風口,每年春天大風夾雜著來自塞外高原的黃沙撲天蓋地而來。夏天則是晴雨不定,雞蛋大的冰雹能把山羊砸死。而冬天西伯利亞的寒流從風口咆哮而來寒風刺骨。直到今天,曾經在這里工作過的解放軍某部參謀長感慨地說那是不堪回首的艱難歲月。
試驗場的基礎設施十分簡陋:一座水泥碉堡,里面裝滿了貴重的實驗儀器;一座兩層小樓,用來裝配各種炸藥;一個十分簡易的變電站,曾因老鼠在里面偷油吃而短路起火;剩下的就是一排平房,這是所有場地人員的宿舍。大多數科技人員同工人、警衛戰士一起睡30多人一排的大通炕,誰要晚上起來一趟,回去時的位置便沒有了。陳能寬因工作需要,居住條件稍好一點,自己一間屋。但這間屋同時也是辦公室,堆滿了圖書與計算尺、草稿紙,而他睡的是一張簡簡單單的行軍床。
最讓17號工地建設者們痛心的是,在各項準備工作已經基本就緒馬上投入到研究工作中去的時候突降暴雨,洪水從山口中噴涌而出,把簡易的實驗場沖得七零八落,研究人員搭建的帳篷被沖走了10多米。陳能寬鎮定地指揮大家把帳篷重新搭起來,把四散的實驗儀器重新調整就位。鎮定自如的陳能寬感染了大家,二室的科研人員不分晝夜地工作,終于把失去的時間搶了回來。
陳能寬在17號工地所進行的最初研究工作,是用實驗來驗證當時核爆的一些基本理論和方法。要使原子彈發生核爆炸,必須首先想辦法使其中的核裂變材料受到猛烈的壓縮,由次臨界狀態進入臨界狀態,從而發生鏈式核裂變反應,在瞬間釋放出威力強大的裂變能。那怎樣才能壓縮核裂變材料從而產生這一系列的反應呢?
在原子彈研制初期,中國核科學家已經知道原子彈產生核爆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槍法”,一種是“內爆法”,中國科學家一般稱之為“壓擾式”。“槍法”結構較為簡單,威力小,美國在廣島投擲的第一顆原子彈“小男孩”就采用這種方法。“內爆法”結構比較復雜,但威力更大,而且更適合原子彈武器化的需要。在長崎上空爆炸的第二顆原子彈“胖子”采用的是“內爆法”。
為保證原子彈研制成功,決定兩條腿走路:“把比較高級的‘內爆法作為主攻方向,同時進行‘槍法的理論計算。”但無論是張愛萍、李覺等行政組織者,還是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懷等科學研究人員,他們最大的希望還是寄托在更高級的“內爆法”上面。要攻克“內爆法”,除理論上需解決一系列難題外,在試驗方面也有兩個“攔路虎”。一是炸藥的組裝形式,二是點火裝置。“內爆法”要求原子彈組裝的常規炸藥產生均勻的內向爆炸力,在以微秒(百萬分之一秒)計的計時精度內精確聚集到裂變物質的表面,使裂變物質瞬時達到或超過臨界值。同時,爆轟所產生的高溫高壓使金屬變成第四態的等離子體,釋放出大量的中子進入裂變芯。
陳能寬帶領的爆轟實驗室的任務,就是通過實驗來設計炸藥的裝配方式。在王淦昌、郭永懷的幫助下,陳能寬帶領一批科技人員開始了漫長而又危險的實驗。當時面臨的第一個困難,是如何配制實驗所需的炸藥。出于實驗的需要,17號工地上的炸藥完全要由試驗人員自己配制。這項工作不需要太高的技術,卻需要極大的勇氣、充沛的體力。陳能寬親自出馬,與其他科研人員、工人一道冒著風險從事著這項被稱為“逗龍尾巴的游戲”。剛剛接觸爆轟物理的陳能寬等人對炸藥的了解十分膚淺。當時分在搞炸藥的大學生劉敏回憶,大家誰也不知道高能炸藥的品性,所以搬炸藥時一個個都膽戰心驚,實驗場上充滿了緊張氣氛。所以陳能寬提出:“青年中有人在常規武器和地質礦山中玩過炸藥和雷管,我要拜能者為師!”在他的帶動下,全體參試人員互相學習,對炸藥的性能有了深刻的了解,一些不必要的恐懼消失了。
融化炸藥混合劑需要高溫條件,陳能寬帶領大家架起了一口普通的鍋和幾只舊軍用桶,一次次的融化、配料、實驗,再融化、配料、實驗。在高溫狀態下,各種化學物質散發著難聞的有毒氣味。但氣味越難聞,陳能寬他們就越需要使出全身力氣進行攪拌,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使炸藥配料更加均勻。為了保障身體健康,實驗人員不得不經常換班。到后來為了保障進度,甚至并不常來17號工地的王淦昌等人也加入到攪拌炸藥的行列之中。
隨著爆轟物理研究的深入開展,對炸藥部件不斷提出新的要求,由圓柱形發展到多邊形、圓錐形,由單質炸藥發展到混合炸藥,即幾種不同爆速的炸藥混合澆注成型,這就給裝注工藝帶來了相當的難度。TNT炸藥加入鈍感材料后降低了工藝流動性,很可能影響炸藥部件的成型質量。在這種情況下,王淦昌、陳能寬親自參與到炸藥的研制工作中,與其他科技人員研究改善炸藥工藝、降低混合炸藥液態黏度,并親自查找“綜合顆粒法”資料,由外文翻譯成中文。經過多次工藝實驗,終于用“綜合顆粒法”解決了混合炸藥注裝工藝性能差的問題。
實驗面臨的第二個困難,就是實驗本身的危險性。為了取得各項數據,需要將各種實驗部件引爆,人們形象地稱之為“打炮”。試驗場上天天炮聲隆隆。每次“打炮”時,試驗部件就放在實驗場碉堡的附近,各種導線從3個碗大的洞口伸進碉堡內部,聯在控制設備、示波器和高速轉鏡照相機上。為了抓緊進度,試驗人員經常是第一個試驗部件剛剛炸過,硝煙還沒散盡,便帶著另一個部件沖上去,接好電纜、聯好導線,然后便開始打第二炮。對他們來說,一天打10多炮是十分正常的。在陳能寬等人的大膽實驗和精心組織下,17號基地雖然進行了無數次爆轟實驗,但從來沒有出過大事故。

陳能寬不僅面臨實驗的艱辛和危險,還有各種研究工具的匱乏。由于國力有限,陳能寬的實驗小組沒有太多先進設備,實驗開始時全是憑借自己堅實的理論基礎和零星國外資料選定了一些特殊的化學炸藥,并指定了幾個較為可行的模型來澆濤實驗部件。蘇聯提供的熔化炸藥沒有到貨,就用自制的熔藥桶來代替米哈伊洛夫熔化爐;新建鍋爐房沒有建好,就用開水爐送氣;沒有專業設備,就用鋁盆、鋁鍋做裝注藥輔助工具;裝注工房沒有建好,就用帳篷房代替。
幾十炮打過之后,陳能寬得到了一些實驗數據。但他能夠用來分析這些數據的,只有幾部簡單、甚至簡陋的手搖計算機。有時甚至不得不用計算尺和對數表。后來實驗種類越來越多、取得數據越來越復雜時,所有工具無用武之地了,就不得不在王淦昌、鄧稼軒等人協助下,依靠自己所掌握的一般力學原理來改進炸藥模型。當時張愛萍正帶領一批水利專家在官廳水庫進行考察,聽說陳能寬急需實驗器材,就立即從炮兵部隊調撥來一批進口器材,這才解了燃眉之急。
物質是貧乏的,但精神是富足的。在17號工地的歲月里,陳能寬并沒有被惡劣的環境、艱巨的任務所嚇倒。他經常告誡自己,也鼓勵同事們,一定要學會苦中作樂。每當陳能寬從北京趕往實驗場時,他總是親自駕駛著吉普車,沿著蜿蜒曲折的長城穿行。一座座敵樓、烽火臺,一段段城墻從他的眼前掠過,仿佛他真的聽到了長城內外延續了幾千年的廝殺,看到了濃煙滾滾的狼煙。在那顆充滿各種數據、方程的大腦中,閃現出的是撫今追昔的感慨,也更加明白核武器對中國的重要性。
三
爆轟波聚焦元件是17號工地產品中最關鍵的部件之一。實現聚合爆轟波有兩條路可循:一是復合裝藥燃轟聚焦,二是爆轟元件。前者在1961年初已經在理論設計上完全解決了,在實驗上也取得了初步成果。但應用在產品上對整體結構不利,部件笨重且不利于儲存,不利于武器化。后者在設計和實驗上雖都存在不少困難,但對產品結構有利,便于武器化。
面對兩個可選擇的設計方案,陳能寬細致陳述爆轟元件的優點,力主以后者為突破重點。在他的倡議下,上級領導經權衡利弊批準了以爆轟元件為主攻方向。以后一系列產品都使用此類原理,正是在這一點上,陳能寬為中國的核武器事業立了大功。
大約在1961年底,爆轟元件研究實驗正式開始,陳能寬親自動手設計第一個元件。聚合爆轟裝置的動作是一個二維流體動力學問題,它包含了一個復雜的爆轟理論問題,沒有嚴格的解。為了尋求答案,陳能寬采用“有效藥量法”,嘗試用一維模型來近似估算。當時17號工地上的計算工具就是一臺手搖計算機。陳能寬報數據,由當時剛剛畢業參加工作的劉文翰搖計算機,邊算、邊記、邊修正。經過反復推敲,第一個元件的設計誕生了,陳能寬把它命名為“坐標1號”。
接著,陳能寬集思廣益,又從不同觀點考慮設計了“坐標2號”“坐標3號”。1號到3號的爆轟實驗結果雖然沒有達到目的,但已接近了設計目標,完全肯定了爆轟元件的技術可行性。設計過程中,陳能寬和劉文翰共同提出由實驗數據、用一維模型反算“有效裝藥”的公式,設計下一輪的元件。實驗證明此法是成功的,很快就在“坐標4號”元件上初步達到聚焦要求,以后又經“細調”設計數據使之定型。陳能寬與劉文翰總結的計算方法一直沿用到1965年才由新方法代替。
經過一年中上千次的實驗,1962年9月,爆轟試驗場傳出喜訊:原子彈的起爆元件獲得重大突破,研究人員研制出了直徑為100毫米與200毫米的炸藥平面透鏡,在爆轟波傳播規律和高壓狀態方程的實驗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原子彈“內爆法”的可行性獲得驗證。面對中央領導的詢問,陳能寬滿懷信心地預言:在最后期限前,他們能夠做出原子彈所需的起爆元件。
隨著各項科研相繼取得突破,1962年中國核武器計劃進入攻堅階段。為了加強首次原子彈國家試驗的準備工作,九局成立了四個委員會,陳能寬被任命為冷實驗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協助王淦昌工作。
所謂“冷實驗”,通俗地說就是不使用鈾235等裂變材料的實驗。這是出于中國國情,經過科研人員無數次摸索總結出來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實驗方法,在中國原子彈、氫彈的研制及以后兩彈改進的過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套實驗方法的發軔,就是從17號工地開始的。
由于實驗工具相對簡陋、鈾等核材料比較奇缺,而且實驗所需經費遠遠不夠。“窮則思變”,中國的核科學家無法像美國同行那樣一個個地爆炸實驗品,從中得到C1、C2、C3……這樣的數據。但他們卻發揮了比美國同行更高的聰明才智,即充分利用“方法論”,先從概念入手進行理性分析,用相對簡單、安全的實驗代替復雜的、危險的實驗。陳能寬充分發揮了他金屬物理學的知識,根據材料科學的相似性原理、流體力學的相似性原理及幾何相似性原理,從最初的鋼材料、單個元件開始,一炮炮地打,一個個地分析。冷實驗逐漸開始復雜起來,過渡到不同材料構成的合金,然后是一個部件、兩個部件、三個部件……最終開始使用某些性能接近裂變物質的材料,實驗部件也做到了半球。
為了在簡陋條件下取得真實的數據,陳能寬對參試各小組的實驗要求非常嚴格,每次實驗都要有詳細記錄,所有照相片必須保留。每次做完一個實驗,參試人員必須當場用草本做出記錄,然后再寫出正本。經過認真核查后,每份記錄上都要簽上所有實驗、記錄、檢查人員的名字以示負責。正是充分利用這種實驗方法,使得核實驗節省了大量時間,更主要的是通過“冷實驗”方法,為國家節約了大量資金和戰略物資。
到1962年底,隨著實驗規模的不斷擴大,實驗危險性的增加,河北懷來的17號工地已經不再符合繼續進行實驗的條件了,整個實驗場不得不考慮搬家。
(本文作者 中國外文局海豚出版社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