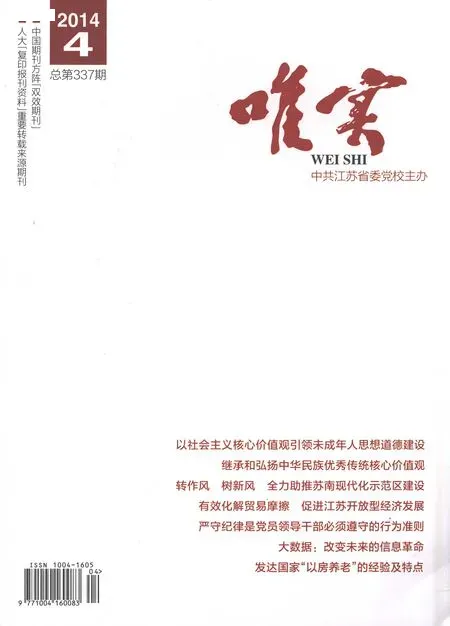中東歐國家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利益訴求
付爭 赫赤
中東歐國家位處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是中國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樞紐和支點地區。無論是在貿易還是融資方面,中東歐國家都對中國有著較強的市場需求,也是中國與歐洲展開合作的重要試水區。自歐債危機以來,歐盟對中東歐國家支持乏力,而中東歐國家恰恰對外部市場和國際貿易具有很強的依賴性。近幾年來國際貿易保護主義與單邊主義抬頭,中東歐國家也在積極尋求更廣闊的新市場與投資來源地。“一帶一路”建設的基礎和核心是互聯互通,即打通原本處于全球化進程之外的斷層與邊緣地帶,并將其納入新的一體化進程。中東歐國家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為國內的轉型發展以及自身地緣關系的重構提供了新契機,也因此可以借力實現國家的加速發展,提高國家和地區在全球范圍內的相對實力,并引發地緣格局與結構發生相應改變。
目前,中東歐16國① 已整體加入“一帶一路”的互通互聯建設,并在基礎設施建設、貿易運輸、資金融通、互通互聯以及人文交流等方面取得了豐碩的合作成果。當然,我們也注意到,中東歐16國彼此在歷史文化、宗教信仰、政治環境和社會經濟方面存在諸多差異,這些差異必然會導致中東歐國家在加入“一帶一路”建設后的利益訴求呈現多樣化特點,也對中國在相關合作中協調各國甚至各區域聯盟的利益訴求帶來挑戰。
冷戰結束后,中東歐國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說明中東歐國家已加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成為“中心—外圍”結構中的外圍國家。中國的“一帶一路”項目大多建在“邊緣—半邊緣”國家,尤其是那些地處大陸腹地的國家,其目的也是通過互聯互通建設,將其由內鎖國變為陸聯國,從而成為全球化網絡中不可或缺的節點,實現外圍國家之間、外圍國家與中心國家之間的“共商、共建、共享”。然而,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的合作無疑觸動了歐盟、俄羅斯和美國的敏感神經,以這三方為代表的外界普遍認為,中國借歐美俄三方關系緊張之際謀求在歐亞大陸“心臟地帶”的地緣政治影響力。然而,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的合作是基于后者真實的參與意愿而達成的“外圍國家”之間的合作,是中東歐地區對外政策多元化的表現之一。為使這些誤解不攻自破,我們可以通過分析中東歐地區所面臨的新態勢來理解為什么中東歐與中國建立這樣的伙伴關系,進而探究中東歐國家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后的利益訴求。
一、地緣政治層面
由于位處西歐與俄羅斯之間,地緣政治特征顯著,因此,中東歐地區歷來是大國地緣博弈的競技場和利益爭奪的交鋒地帶。近些年來,中東歐國家的地區自主性意識逐漸增強,但面對地緣政治博弈體系中的大國,小國平衡策略無法幫助其成為主動的地緣政治玩家。在美國戰略重心東移、歐盟經濟復蘇乏力、俄羅斯地緣攻勢增加以及中東歐自主性增強的國際環境下,目前中東歐地區的四方博弈呈現出新的時代特點。首先,面對美國在歐亞大陸中的戰略重心轉移,中東歐國家對外戰略也從對中心國家的“一邊倒”轉向“中心—外圍”國家兼顧的多元務實平衡戰略。其次,歐盟東擴和歐元區東擴的錯位,顯示了中東歐國家對歐盟穩定性與歐洲經濟前景的復雜預期。最后,面對大國博弈下的“分而治之”,中東歐國家地區聯盟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由于在歷史文化、民族分布、宗教信仰、政治環境和社會經濟方面存在諸多差異,中東歐16國各國的利益訴求也不盡相同,這為大國在該地區的地緣博弈提供了“分而治之”的契機。目前,維謝格拉德集團、波羅的海三國和西巴爾干地區的自主性意識日益增強,并著意推進彼此間的融合與協作。雖然維謝格拉德集團內部依然在對俄政策上存在分歧,但在能源安全、地區互聯互通、難民、與新興國家關系等重要領域卻能達成基本共識,并有意發展與波羅的海三國、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等國在地區重大問題上的協調與合作。面對歐美在能源多元化問題上給予的大力支持,波羅的海三國卻更加重視與北歐國家在能源安全與經濟方面加強合作。面對四方博弈的地緣政治新形態,中東歐國家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后也會產生新的政治利益訴求。
一方面,與新興市場大國中國合作,可以為在四方博弈中積攢議價籌碼,進一步謀求地區自主權,使對內政策不因歐美壓力而輕易改變。為改變以往“東靠”“西傾”皆悲劇的小國命運,中東歐國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一直在尋找合作的伙伴和方向,增加對歐洲—大西洋以外地區和國家的關注,中國便是這些國家中的新興市場大國。與巴西、南非、印度等新興市場大國相比,中國不僅在“中心—外圍”結構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且與中東歐國家同屬轉型國家,都踏足了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艱難歷程,因此更能理解中東歐國家在地緣政治上的困境與增強自主性的強烈訴求。雖然中國無意卷入中東歐地區的地緣政治斗爭,但與中國“一帶一路”倡議開展深化合作符合中東歐的切實需求。例如,面對歐盟與俄羅斯的競相爭取,巴爾干地區卻選擇積極加入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以獲取基礎設施建設融資。2016年與2017年,中國在西巴爾干五國的投資約49億美元,占中國對中東歐16國投資交易額的一半以上。為助力歐盟的多瑙河戰略發展項目,捷克和斯洛伐克也積極與中國開展合作。此外,在政治安全領域,中東歐國家與中國積極搭建政策溝通平臺,從近些年來的平臺發展情況來看,政策溝通平臺形式會日趨多樣化。①
另一方面,出于中東歐地區內部聯盟(比如維謝格拉德集團、波羅的海三國、西巴爾干地區)的需要,中東歐國家需要與信息技術相關的科技創新與基礎設施建設,而中國在這方面具有豐富的建設經驗,值得中東歐國家學習借鑒,并與中國在相關方面展開進一步合作。如前文理論部分所提到的,信息技術的發展會提高資本克服空間障礙的能力,改變曾經禁錮于既定空間內的資本循環與勞動力交易的連貫性,增強國家間相互依賴,促進地區聯盟重組,弱化半邊緣與邊緣國家邊界。因此,在中東歐地區內部聯盟發展進入新階段之際,中東歐國家亟須與信息技術相關的科技創新服務與基礎設施建設資金支持,而不僅限于鐵路交通方面的基礎設施建設。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下的互聯互通,既包括與設施聯通相關的“硬聯通”,也有金融資金、科技人文交流的“軟聯通”。因此,基于強化地區內聯盟的訴求,中東歐國家未來會在“一帶一路”倡議框架下與中國展開更深入的合作。
二、經濟利益層面
經過20多年來的轉型與發展,中東歐地區的經濟面貌大為改善,這得益于歐盟發達國家的資本輸出與所提供的市場需求。目前,中東歐國家成為全球范圍內僅次于中國的成長最快的汽車生產地,[1]部分中東歐國家已成為泛歐供應鏈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是加入歐元區的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愛沙尼亞和立陶宛。然而,正是因為對以德國為代表的歐盟市場過度依賴,中東歐國家的經濟脆弱性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中也暴露得較為徹底。金融危機以及歐債危機后,歐盟經濟增長疲態日益顯現,中東歐地區的經濟也遭遇增長瓶頸。
自中東歐地區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以來,中國與中東歐的經貿關系持續升溫,并取得了豐碩的階段性成果。據統計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與中東歐地區貿易額達822億美元,較2011年增長了55.4%。中國企業在中東歐國家投資超過百億美元,新增就業崗位兩萬余個,投資領域包括機械制造、物流配送、電力、酒店、金融、研發中心等。
從接收中國資本的投資領域和地域來看,中東歐國家已然在嘗試通過重組外資結構和來源以實施平衡增長戰略。黃賾琳和姚婷婷(2018)研究了中國與“一帶一路”國家經濟周期協同性及其傳導機制,發現雙邊貿易和金融一體化會強化協同性,專業化分工和雙邊直接投資則會弱化協同性,而在經濟波動上升期和下降期時,中國與轉型國家的協同性最高。[2]因此,借助“16+1”合作機制和“一帶一路”倡議,中東歐地區可以通過提高與中國經濟周期的協同性來平衡歐盟經濟增長乏力帶來的外部市場低迷。2013年至2018年期間,中東歐和中國已通過投資合作,初步完成了交通基礎設施聯通以及物流信息通信網絡的建設,為暢通兩地貿易往來、發展雙邊貿易打下了良好的物質基礎。同時,面對加入歐元區可能帶給國家經濟主權的負面影響,尚未加入歐元區的中東歐國家更愿保有貨幣主權,因此,中東歐國家很可能與中國在貨幣結算和供應鏈金融方面展開進一步合作,以分散“幣緣政治”對國內經濟自主性帶來的風險。
此外,目前中東歐地區是泛歐供應鏈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泛歐供應鏈的受益者,這種由全球價值鏈主導的專業化分工在短期內很難轉變。因此,專業化分工會進一步促進經濟關系的空間分化,使中東歐地區的專業化分工更傾向于歐美,而非中國。由此,中國對中東歐地區直接投資中的綠地投資發展空間可能較為有限,選擇差異化而非競爭性的產業進行投資可能會改善這一現狀,形成中國—中東歐投資雙贏局面。
三、地緣文化層面
后冷戰時期,文化因素在解決政治沖突、處理國際事務中的戰略地位大幅提升,在現實利益之外,精神信仰和文化傳統影響著國家行為和國際斗爭,文化這一長期分離并隱藏于政治、經濟等因素背后的因素,構成了地緣政治和經濟板塊的深層次動力。[3]受地域的交錯分布和不同文明傳承的影響,中東歐地區的地緣文化結構十分復雜,宗教問題和民族問題交織在一起,并不定期地引爆國內矛盾和國際沖突。
近幾年來,中東歐地區采取多元化外交戰略,且內外政策自主性不斷增強,但這并沒有改變中東歐地區在文明歸宿上的困惑和政治定位上的搖擺。根據前文理論部分的分析,多元文明在短期內無法融合成單一文明,但由于地緣文明是借助國家權力而發展的,而利益又是壯大權力的工具,因此,借助利益的融合去推動地緣文明的發展,降低“文明沖突”演化為“暴力沖突”便成為可能。
相對于西歐、俄羅斯與北非,中國幾乎未曾參與到中東歐地區地緣文明交織變化的歷史,也與中東歐國家在地緣文化上鮮有交集。因此,中東歐國家在與中國進行合作時,民族問題和宗教問題引發地區沖突和國家間對抗的概率較低。中東歐各國在不同程度上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可以說是以開放的態度為未來的文化融合實踐活動預留了可能。中東歐各國完全可以通過經貿往來所帶來的經濟增長契機,增加與中國和其他中東歐國家在人文交流上的互動,在獲得地緣文明按雙贏發展的物質基礎的同時,以提升文化軟實力作為國家安全戰略導向。而面對中東歐地區復雜的地緣文化結構,中國一貫秉持尊重中東歐地區人民的立場選擇,希望能按照和諧雙贏的方向增進彼此的了解,從“民心相通”的角度推進地區間人文交流,為深化合作打下良好的人文基礎。
參考文獻:
[1]朱曉中.歐美大國與中東歐利益關系的結構和深度[J].世界態勢,2018(6).
[2]黃賾琳,姚婷婷.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周期協同性及其傳導機制[J].統計研究,2018(9).
[3]孔寒冰.東歐民族分布的“馬賽克現象”[J].世界知識,2012(1).
〔本文系遼寧省教育廳2020年高等學校青年科技人才“育苗”項目“空間政治經濟學視域下全球金融空間演化脈絡動力機制研究”(LQN202023)、遼寧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一般項目“全球金融空間重塑下的東亞貨幣合作研究”(Y201912)、2020年度遼寧大學本科教學改革研究一般項目“基于交叉學科優勢特色的教學改革與實踐探索——以《比較政治經濟學》為例”(JG2020YBXM027)和“基于研討式教學法將國際經濟學前沿科研成果融入《國際經濟學》課程的研究”(JG2020YBXM125)成果〕
(付爭:遼寧大學國際經濟政治學院副教授;赫赤:遼寧大學國際經濟政治學院研究實習員)
責任編輯:彭安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