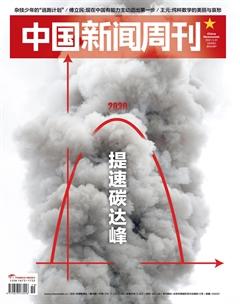“祝融號”著陸:中國正式入局火星探測
彭丹妮

5月19日,中國國家航天局發布天問一號任務探測器著陸過程兩器分離和著陸后“祝融號”火星車拍攝的影像,圖像由火星車前避障相機拍攝,正對火星車前進方向。圖中可見坡道機構展開正常;圖像上部的兩個伸桿為已經展開到位的次表層雷達;前進方向地形清晰。圖/中國國家航天局
5月22日,國家航天局發布“祝融號”火星車攜帶的前避障相機和后避障相機拍攝的駛離著陸平臺過程,這些最新的火星表面影像,讓全世界共同見證:“祝融號”終于踏上“熒惑”,開啟巡視探測之旅。至此,中國已成為美國、俄羅斯以外,世界上第三個實現登陸紅色星球的國家。
1962年9月,肯尼迪發表了一段被后來人稱之為“月球演說”的演講。在這次演講中,他放出豪言壯語——美國要在20世紀60年代結束前把人送上月球,這被看作美蘇月球競賽的挑戰書。
2010年,在肯尼迪航天中心的一次演講中,奧巴馬宣布,美國要在2030年代將宇航員送往火星。他說,“我們已經為美國太空事業的下一篇章設定了一個明確的關鍵目標。”
奧巴馬的“火星演說”標志著人類對火星的探索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亦即載人登火。但彼時,中國尚未真正意義上地參與過火星探測。這一年,孫家棟、戚發軔、龍樂豪、徐匡迪等八位院士聚在一起討論,希望盡早開展火星探測工作,國防科工局隨即開始組織相關的論證。
國家航天局原局長欒恩杰曾在2016年撰文寫道,中國原本有能力在2013年實現火星探測,但由于多種原因,當時沒能實現。“但人類探索火星的第三個時期我們趕上了,我們不應失去這個機會。”
在2020年7~8月的火星探測窗口,中國首個火星探測任務“天問一號”發射,就在前后幾天,阿聯酋“希望號”與美國“毅力號”也分別出發了。“希望號”僅僅是環繞火星以研究火星大氣,但“毅力號”卻絕對是“天問一號”的競爭對手。中美火星任務將會在科學探索上較量,也都會為將來在火星取樣、載人登火等更長遠的賽道上競爭打個頭陣。
火星探測競賽史
火星上第一個來自人類的物體,是1971年12月蘇聯發射的“火星3號”,但它在著陸僅20秒后就迅速失聯,連拍攝的第一張火星照片都沒能傳全。直到4年后的1975年,美國發射的“海盜1號”和“海盜2號”著陸器,才真正成功地著陸并開展了工作。
1960年代,在人造地球衛星和月球探測器發射不久后,人類就開始了遙遠的火星探測之旅,它最初是作為一種體現政治優越性的象征而存在的。在美蘇太空爭霸的大背景下,1960~70年代,兩個勁敵互不放松,步步制衡,然而,就像“火星3號”的命運一樣,蘇聯勢頭強勁,但其發射的20多個火星探測器基本以失敗告終。
“火星對俄羅斯人來說算是一個墳墓”,業內專家這樣形容說,而美國不僅成為那場競賽中的絕對贏家,一直到今天,美國無疑都是全球火星探測領域最富有經驗和成果的國家。
1964年11月28日,美國“水手4號”探測器在火星外面掠過,拍攝了火星表面的第一張特寫照片。1969年初,美國又發射了“水手6號”和“水手7號”,發回了一些數據,且向地面傳送了200張火星照片。
在1971年的發射窗口,美國和蘇聯迎來了激烈的“火星爭奪賽”。在短短21天里,美蘇相繼發射了5顆火星環繞器。最終,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后出發的“水手9號”卻率先到達,于1971年11月14日進入環火星軌道,成為人類第一個火星環繞器。自此,人類終于可以駐留在火星附近長期觀測了。
“水手9號”“火星2號”與“火星3號”抵達火星時,恰好趕上火星沙塵暴。只有“水手9號”迅速調整了狀態,堅持到了沙塵暴平息,最終獲得了遠優于其他兩個探測器的探測成果。僅就拍照這一項,“水手9號”就拍攝了并傳回了7000多張火星表面照片,利用它發回的數據,科學家繪制了火星85%的地圖。
早在19世紀晚期,人們通過望遠鏡就可以直接看到火星表面的特征。當時的科學家們發現火星上有很多溝渠一樣的形狀,人們興奮地認為,這是當時火星文明挖出來的一些類似運河的東西。然而,“水手”系列探測器傳回來的關于火星大氣和表面的更為詳細的數據,打破了這一廣泛持有的觀點。這些數據揭示了火星真正引人注目的特征:它擁有太陽系中最大的火山,沙塵暴經常橫掃過它的平原,以及這里有迄今為止發現的最大峽谷之一——與美國大陸一樣長的峽谷。
1975年8~9月,美國兩個先進的“海盜號”火星探測器發射,實現了早期火星探測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火星軟著陸。“海盜1號”著陸器發回的全彩圖片讓人們意識到,這是個空曠、貧瘠、亂石遍布的星球,富含鐵元素的土壤因為氧化而顯得一片橙紅。
“海盜計劃”是人類火星探測史上最昂貴的計劃之一,共耗資10億美元,但獲得的成果也舉世矚目。進入1980年代后,隨著蘇聯解體、太空競賽意識的極大削弱,使兩國月球、火星乃至行星探測的熱情急劇下降,美國這一時期將重點放在空間站的建設。與月球探測類似,火星探測一度進入了約20年的沉寂時期。
欒恩杰將早期這段歷史看作是技術能力實現期,主要驗證了飛掠、環繞、踏足火星的工程先進性。但在1992年之后,科學目標開始決定火星探測的設計、儀器搭載等等。“從1992年開始,我覺得才是真正以科學驅動的新一波火星探測熱潮。”中國國家天文臺行星科學家鄭永春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也表示。繼美國和蘇聯后,上世紀90年代,日本、歐洲和印度也相繼加入火星探測行動。
從1992年開始,以美國“奧德賽”號與歐盟“火星勘探軌道器”為標志的一系列環繞、落火、就位探測、火星車巡視探測,包括“火星快車”“機遇號”“勇氣號”“鳳凰號”和“好奇號”任務等,都在普查的基礎上,聚焦某些有限的重點科學研究項目進行探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