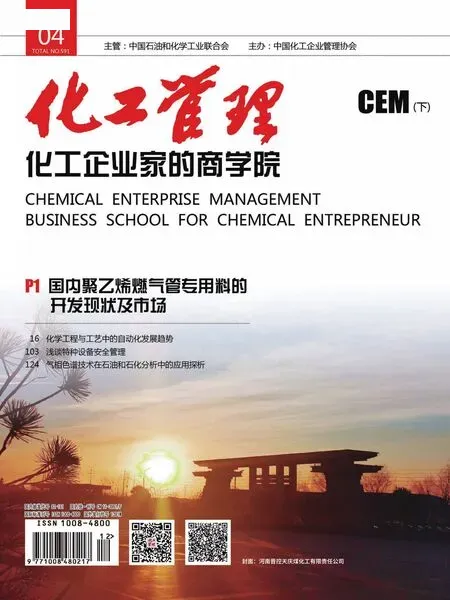九段沙水域不同形態(tài)氮磷(N/P)的時空分布格局及其賦存特征
高連應(yīng),錢利煒,董浩宇,吳鵬飛,王磊(同濟大學環(huán)境科學與工程學院,上海 200092)
0 引言
濕地是位于水陸交界處的復合生態(tài)系統(tǒng),具有獨特的水文、土壤、植被與生物特征,具有重要的生態(tài)服務(wù)價值。由于植物、土壤的吸附、吸收和根部微生物的降解、轉(zhuǎn)化作用,濕地被認為是一個污染凈化器,有“地球之腎”的美譽[1]。作為陸地生態(tài)系統(tǒng)碳循環(huán)的重要組成部分,濕地在全球碳固存中起著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被認為是重要的碳匯。濕地具有多種類型,按照地貌類型和濕地形成過程可以將濕地劃分為濱海濕地、河流濕地、湖泊濕地、沼澤濕地和各種人工濕地[2]。
河口濕地因為其處在獨特的海陸交錯區(qū),處在江河入海的交界處,受潮汐河流、航運等多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了其豐富的物質(zhì)多樣性和生態(tài)系統(tǒng)特殊性[3-4]。河口濕地往往處于人口密集、經(jīng)濟發(fā)達地區(qū),污染壓力較大。有機污染物和N/P營養(yǎng)鹽等通過不同途徑輸入河口濕地水域,導致水環(huán)境富營養(yǎng)化,引發(fā)濕地生境變化[5]。研究發(fā)現(xiàn)水體富營養(yǎng)化很可能削弱潮間帶濕地的碳匯功能,從而減少濕地對二氧化碳的吸收[6]。對長江口及其鄰近海域的碳源匯變化進行分析,發(fā)現(xiàn)受水體富營養(yǎng)化影響,長江口近岸海域的碳匯能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由于氮磷的不斷輸入,使得濕地水域逐漸富營養(yǎng)化;水體的富營養(yǎng)化反過來又會對濕地的生態(tài)功能造成負面影響[7]。所以,水體富營養(yǎng)化對濕地生態(tài)服務(wù)功能的影響及其機制需要得到特別的關(guān)注。
九段沙國家自然保護區(qū)是長江口最年輕的河口沙洲,是上海重要的生態(tài)屏障,對長三角地域的微氣候調(diào)節(jié)有非常重要的作用[8]。近年來有關(guān)九段沙濕地的生物多樣性和生態(tài)服務(wù)功能的研究已經(jīng)有了較多報道[9-11],九段沙水域的污染情況及其對生態(tài)功能的影響也有一些研究,如吳鵬飛等人初步研究了九段沙濕地水域典型污染物COD、無機氮、總氮(TN)、活性磷(AP)、石油烴和重金屬的分布格局與動態(tài)。結(jié)果發(fā)現(xiàn),九段沙水域水質(zhì)整體污染比較嚴重,特別是營養(yǎng)鹽含量已超過了地表水環(huán)境質(zhì)量Ⅳ類水標準。但是,針對導致九段沙水域富營養(yǎng)化的N/P營養(yǎng)物的主要形態(tài)和賦存特征尚缺乏詳細的研究,對其主要的來源也未有較清晰的認識。闡明九段沙濕地水域N/P污染物的主要形態(tài)及其時空分布格局,解析其主要的賦存形式,對于進一步認識導致九段沙水域水體富營養(yǎng)化的主要原因,探究N/P等營養(yǎng)鹽的主要來源具有重要意義。鑒于此,本研究在九段沙水域上游到下游共設(shè)置了4個采樣水域,通過定時采樣,分析了水域中不用形態(tài)N/P的時空分布格局和賦存形式,并在此基礎(chǔ)上初步探究了導致九段沙水域水體富營養(yǎng)化的主要N/P形態(tài)及其可能的來源。
1 實驗方法
1.1 研究區(qū)域介紹
上海九段沙濕地自然保護區(qū)位于北緯31°06′20″~31°14′00″,東經(jīng)121°53′06″~122°04′33″,東臨東海、西接長江,西南、西北分別與浦東新區(qū)和橫沙島隔水相望,主要由江亞南沙、上沙、下沙和附近淺水水域組成(如圖1所示)。東西長約46.3 km,南北寬約25.9 km,總面積約420 km2,吳淞0 m 以上面積達145 km2。既是目前長江口最靠外海的一個河口沙洲,也是長江口最年輕的河口沙洲。九段沙濕地屬于亞熱帶大陸性季風氣候,年均氣溫15.7 ℃;年均降水量約1 143 mm,夏季降水量最大,占全年的42.0%。土壤發(fā)育時間僅50年左右,成土過程原始,主要發(fā)育土壤類型為濱海鹽土類和潮土類。植被以蘆葦(Phragmites australis)、海三棱藨草(Scirpusma riqueter)和互花米草(Spartinaalterniflora)為主,屬典型鹽沼生態(tài)系統(tǒng)。

圖1 采樣點設(shè)置示意圖
1.2 采樣點設(shè)置與樣品采集
在九段沙濕地水域南槽航道,從上游到下游共設(shè)置4個采樣水域,每個水域包括3個采樣點(如圖1所示):分別位于九段沙上游水域(SY1 121.75,31.28;SY2 121.76,31.27;SY3 121.76,31.26),江 亞 南 沙(NS1 121.81,31.24;NS2 121.81,31.23;NS3 121.83,31.22),上沙水域(SS1 121.86,31.23;SS2 121.88,31.21;SS3 121.91,31.19),下沙水域(XS1 121.93,31.18;XS2 121.96,31.16;XS3 122.00,31.15)。
采樣時間,分別于2015年7月—2018年4月進行為期三年的12次樣品采集,每年分為春夏秋冬四次采樣。樣品采集及保存方法按照GB 17378.3—2007《海洋監(jiān)測規(guī)范-樣品采集、貯存與運輸》進行。
1.3 分析方法
水樣pH、電導率、濁度使用多參數(shù)水質(zhì)測量儀現(xiàn)場測定。
水樣總氮(TN)、硝氮(NO3-N)、總磷(TP)、活性磷(AP)等化學指標,按照GB 17378.4-2007《海洋監(jiān)測規(guī)范-海水分析》測定;其中為了測定可溶態(tài)和顆粒態(tài)的氮磷,需要將水樣進行過濾處理,比較處理前后的結(jié)果。
1.4 數(shù)據(jù)處理
同年度水樣分為春夏秋冬四個批次,對各批次每個水域三年的數(shù)據(jù)進行求均值處理。使用Excel 2016進行數(shù)據(jù)處理,使用Origin 2018對數(shù)據(jù)進行繪圖。使用SPSS 24.0 對所測數(shù)據(jù)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ANOVA)和相關(guān)性分析。
2 結(jié)果與討論
2.1 九段沙水域水質(zhì)的基本性質(zhì)
九段沙各水域的基本理化指標(見表1)。從中可以看出,上游、江亞南沙、上沙、下沙各水域的pH變化不大;電導率自上游向下游呈現(xiàn)出上升的趨勢,下沙升高明顯;從上游到上沙,濁度無明顯差異,但下沙水域濁度顯著較高。

表1 九段沙水域基本理化指標
2.2 九段沙水域TN和NO3-N的時空分布格局及其賦存形式
對九段沙水域4個區(qū)域12個樣品采集點的水樣進行分析。九段沙上游、江亞南沙、上沙及下沙水域三年TN均值分別為3.00 mg/L、2.54 mg/L、2.30 mg/L、2.34 mg/L(如圖2所示)。四個水域的TN濃度均未達到地表水環(huán)境質(zhì)量標準V類水,這表明九段沙水域N污染嚴重。上游、江亞南沙、上沙及下沙水域三年NO3-N均值分別為2.13 mg/L、1.83 mg/L、1.80 mg/L、1.69 mg/L。可知,水體中的TN主要以NO3-N形式存在,占比較高,約70%,其他形態(tài)N污染物較少。導致TN超標的主要因素是NO3-N含量較高。

圖2 九段沙水域TN、NO3-N濃度的空間分布格局
從空間角度來看(如圖2所示),九段沙上游、江亞南沙、上沙及下沙水域的TN、NO3-N呈現(xiàn)出從上游到下游逐漸降低的趨勢,四個季度樣品均符合該趨勢,且上游水域濃度顯著高于其他水域。從季節(jié)變化來看(如圖3所示),冬春季TN、NO3-N濃度相對較高,夏秋季略低。從漲落潮對比來看(如圖4所示),同一水域,漲潮水TN濃度低于落潮水。從賦存形式來看(如圖5所示),TN與TDN(溶解態(tài)TN)相差不大,表明TN賦存形式主要為溶解態(tài)。
結(jié)果表明九段沙水域上游的TN、NO3-N值均顯著高于下游水體, NO3-N是TN的主要成分,TDN是TN的主要賦存形式。一般而言,濕地水域的N素主要來源包括濕地枯落物的腐爛釋放、上游泥沙的攜帶、點源或面源污染的排放、大氣沉降等[12-14]。由于上游存在2家污水廠排放口,而污水廠達標排水的水質(zhì)指標遠低于地表水環(huán)境質(zhì)量標準V類水的標準,我們推測這可能是上游水域TN和NO3-N較高的主要原因。從同一水域漲潮的TN、NO3-N濃度低于落潮的規(guī)律也可以初步說明,上游輸入可能是九段沙濕地水域TN、NO3-N的主要來源。來自濕地枯落物分解釋放的TN主要以有機氮為主[15-16],而污水廠排放的TN主要是以NO3-N形式存在。九段沙水域水體中NO3-N約占TN的70%,這也說明了水域中的TN主要不是來自于濕地枯落物的腐爛分解。另外,水域中顆粒TN的占比極低(特別是上游水體),這表明TN主要來自可溶性N,而非泥沙攜帶的不溶性N。下游顆粒物N占一定的比例可能和藻類等浮游生物的貢獻有關(guān)。
從TN、NO3-N的季節(jié)變化規(guī)律可知,冬春季的TN、NO3-N普遍高于夏秋季,特別是上游水體。其原因可能是冬春季節(jié)植物腐爛,會導致有機氮等輸入到水中,同時冬春季濕地的污染凈化能力也較低。另外,冬春季由于溫度較低,污水處理廠的處理效果較差,也會導致出水TN和NO3-N偏高,從而上游水域中TN、NO3-N濃度顯著高于夏季。

圖3 九段沙水域不同區(qū)域各季節(jié)的TN、NO3-N(A)春季;(B)夏季;(C)秋季;(D)冬季。(SY)上游;(NS)江亞南沙;(SS)上沙;(XS)下沙

圖4 九段沙2020.10月TN漲落潮對比

圖5 九段沙各水域TN、TDN
2.3 九段沙水域TP和AP的時空分布格局及其賦存特征
九段沙上游、江亞南沙、上沙及下沙水域三年TP均值分別為0.24 mg/L、0.23 mg/L、0.22 mg/L、0.23 mg/L(如圖6所示)。四個水域的TP濃度未達到地表水環(huán)境質(zhì)量標準Ⅲ類水,這表明九段沙水域P污染的形勢也不容樂觀。上游、江亞南沙、上沙及下沙水域三年AP均值分別為0.082 mg/L、0.070 mg/L、0.070 mg/L、0.063 mg/L。由此可知,九段沙水域的TP中AP占比較低,大部分情況AP占比低于30%。
從空間角度來看(如圖6所示),上游、江亞南沙、上沙及下沙水域的TP從上游到下游無明顯變化規(guī)律,AP在上游水域最高,經(jīng)過江亞南沙后,有明顯降低,但整體而言在下游水域變化不明顯[17]。下沙水域的TP顯著較高。AP在上游水域略高,經(jīng)過江亞南沙后,有所降低,但整體而言在下游水域變化不明顯。就同水域而言,漲潮水TP濃度低于落潮水,且在下沙水域TP濃度都出現(xiàn)了明顯升高的情況(如圖8所示);從賦存形式來看(如圖9所示),TP中TDP(溶解態(tài)TP)的占比較低,在上游和江亞南沙水域TDP約占30%,上沙和下沙水域約占25%。從季節(jié)變化來看(如圖7所示),TP隨季節(jié)無明顯變化規(guī)律,但AP在冬季略高于春夏季。

圖6 九段沙水域TP、AP濃度的空間分布格局

圖7 九段沙水域不同區(qū)域各季節(jié)的TP、AP(A)春季;(B)夏季;(C)秋季;(D)冬季

圖8 九段沙2020.10月TP漲落潮對比

圖9 九段沙各水域TP、TDP
上游與下游水體TP的變化無顯著規(guī)律,但下沙水域的TP濃度在多批次的采樣中都出現(xiàn)了高于上游的情況。TP出現(xiàn)明顯升高的情況,可能與雨水天泥沙沖刷有關(guān)系[18]。當采樣日出現(xiàn)雨水天氣時,沙洲泥沙流失,水域含沙量提高,下游水域TP濃度的增高情況更加明顯(如圖6所示TP(rain))。雨天TP含量增高現(xiàn)象與顆粒態(tài)TP占TP的比例高達70%的結(jié)果是相符的[19]。對AP而言,上游略高于下游水體,落潮水高于漲潮水,這可能和污水處理廠的排放有關(guān)。但整體而言,AP濃度隨空間變化的差異并不大,這說明除了上游的AP排放源,九段沙濕地本身的釋放可能也是AP的來源之一。TP無明顯的季節(jié)變化規(guī)律,可能是由于泥沙含量隨季節(jié)變化的規(guī)律不顯著。AP在冬季較高可能和冬季濕地植物凋落倒伏腐爛造成AP的釋放以及冬季污水處理廠處理效率較低,導致較高的AP排放有關(guān)[20]。
3 結(jié)語
(1)九段沙濕地水域的TN、NO3-N自上游到下游均呈現(xiàn)出逐漸降低的趨勢,落潮水濃度高于漲潮水,秋冬季略高于夏秋季;NO3-N是TN中的主要形態(tài),占比達70%;TN的主要賦存形式為溶解態(tài),約占90%甚至更高。
(2)九段沙濕地水域的TP自上游到下游沒有明顯的空間變化規(guī)律,但下沙水域TP較高,AP自上游到下游呈現(xiàn)出逐漸降低的趨勢,但差異不顯著。TP隨季節(jié)無顯著變化規(guī)律,AP濃度冬季略高。AP對TP濃度貢獻較低約為25%甚至更低。TP的主要賦存形式為不溶態(tài),約占75%。
(3)九段沙濕地水域的TN主要來自于上游點源排放,排放形式主要為NO3-N。TP大部分來自水體中的泥沙攜帶,上游點源排放貢獻較小。上游點源排放和濕地植物的腐爛釋放可能都是濕地水域AP的主要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