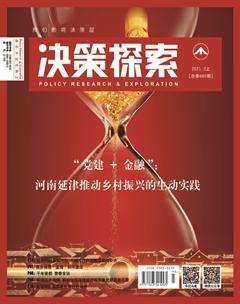孫郁:文學讓我們從俗諦中驚醒
夏斌
孫郁最為人所知的身份是近現代文學批評家、作家,但他也當過報社編輯、博物館館長。無論在哪個崗位上,始終不變的是對他生活保持熱愛和清醒,守望赤誠與責任。
52歲那年,孫郁辭去公職,走進了大學校園,力倡“復興母語的創造性書寫”。他邀請一批當代知名作家加入教師團隊,并率先開設“創造性寫作”二級學科,培養出了幾屆優秀學員。
孫郁認為,文學教育說到底是對想象力與智性的培養。只有更好地接續“文章氣脈”,在與社會、歷史、時代的互動中找到個人志趣與時代命題相連接的橋梁,才能創作出無愧于偉大時代的作品。
一些青年人習慣用程式化的詞語來表達思想,缺乏靈動性、生猛氣
問:有過這么多“跨界”,您最喜歡哪個職業?
孫郁:經歷的每一種職業,其實都是自己喜歡過的。這和年齡有關,年輕時喜歡熱鬧,老了則待在書齋的時候居多。
雖然有過不同的工作崗位,但基本上都在做同一件事情,即魯迅與新文學研究。我個人覺得,記者和博物館館員的經歷,對于現在的教學很有幫助,只是年輕時期浪費了許多時間。
當老師有個好處,就是需要不斷學習,而且在與青年的對話中,可以不斷矯正自己。所以我常常提醒自己,要時時關注新的知識,了解與自己不同的一代人在想些什么。
問:現在的“90后”“00后”是不是不那么排斥文學了?
孫郁:從選課情況來看,一開始喜歡文學的學生不是那么多,他們容易受到流行思維的干擾。文學院有不少學生的第一志愿也不是文學,但調劑過來后,都漸漸學會了安靜地面對文本。畢竟,文學是有巨大吸引力的。
作為老師,我們的任務是與青年人一起面對經典,并在閱讀、討論對象世界的時候發現我們自己。
應該說,現在大學生的知識結構比我們這一代人要豐富,也有很好的人文基礎,但在母語的運用上還存在許多問題。一定程度上,應試教育把人感知語言的能力弱化了,一些青年人習慣用程式化的詞語來表達思想,缺乏靈動性、生猛氣。
文學教育要刺激人保持感知世界的鮮活度,不能沉浸在教條的范式里。目前的教育理應著重解決這方面的問題。
問:中國傳統的語文教育更多的是一種浸潤式學習。從蒙學開始,《大學》《中庸》等一路讀下來,文化的感覺有了,語言的感覺也有了。但現在我們要學的東西比古人多,這種浸潤式學習是不是有點奢侈?
孫郁:這個話題確實值得探討。我是主張雙軌制或多軌制的。坦率地講,現在的教育模式過于單一,應當允許一批人在學科之外的層面接受不同的教育。教育生態變化了,多種可能才會出現。
實際上,每一種模式都有盲區,不同的模式有互補性。聰明的學生可以取長補短。中國有些人文學者沒有大學經歷,但依然有不凡的思想。
能夠放逐思想的人,才會寫出好的文字
問:一直有人說,中文系和文學院培養不出作家。問題出在哪里?
孫郁:大致來看,中文系的授課者整天在講授知識,審美訓練很少。加上學分與考試的因素,學生自然被引到學問的路上來。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中文系出來的作家在校時未必是好學生。典型的例子是汪曾祺,他逃課、散漫,不太喜歡正襟危坐。于是,他的思想會溢出學院的圍墻,精神可以四處飄蕩。
能夠放逐思想的人,才會寫出好的文字。但可惜的是,中文系培養的匠人多,靈氣多被知識掩埋,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問:作家進校園是不是帶來了不同的風氣?
孫郁:作家進入大學,可以營造一種寫作的氛圍。創意寫作也是一門專業,一般的教授未必能夠教好寫作,作家卻可以熏陶、帶動學生去訓練文字。
目前來看,作家駐校帶來了一定的好處,使呆板的學科間有了一種審美的潤滑劑。同時,它清晰地告訴學生一個道理:對母語敏感與否,會影響自己的表達與思考。
應當承認,關于文學創作,沒有天資肯定是不行的,但文學教育可以啟發人走進這個世界。國外創意寫作課已經有了這方面的積累和經驗。國內剛剛興起這門二級學科,還需要慢慢摸索。
問:普希金的詩,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小說,曾為許多中國青年打開了一扇不同于傳統和現實的窗戶。但現在俄羅斯文學似乎逐漸遠離我們,這是不是一種遺憾?
孫郁:近代以來,很多中國人都關注并喜歡俄羅斯文學。中國當代一些優秀的作家也是繞不過俄國文學傳統的,雖然人們對它的態度比較復雜。
普希金的詩句有著燦爛的美質,童真里散著愛意與智性。他的句子被穆旦譯介過來后,刺激了幾代中國詩人的寫作。托爾斯泰的人文關懷直到今天仍得到很多中國作家推崇,他的內省精神對巴金以來的中國作家是有親昵感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殘酷性和復調的審美表達,我們可以從林斤瀾、莫言、殘雪等作家那里看到回應。
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為了改造社會,更是直接從俄國文學那里得到諸多精神鼓舞。我這個年齡的人,因為歷史原因,讀俄國文學也多。現在的作家不同了,擁有更廣泛的參照系,可以根據自己的愛好選擇閱讀對象。
不過,現在也有一個現象值得注意,即許多受過歐美文學啟發的人,后來深入思考中國問題時,不自覺地與俄羅斯文學某些精神有交叉的地方。像格非、王家新等人,最早受歐美文學影響,后來的寫作也頗為注意俄國文學傳統,能夠從其意象里發現自己需要的元素。尤其是王家新,他對俄國詩作的翻譯,有著很深的思想寄托。
魯迅是一個有大愛的人,他的世界沒有一點奴態
問:長期以來,魯迅被塑造為一位“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斗士形象。但在您的筆端,可以看到他在金石學、考古學、科學史、哲學、美學、民俗學、心理學等方面的廣泛興趣與知識譜系。
孫郁:魯迅的豐富性,以流行的思維不易看清。他打撈出了幾近消失的古代文化余緒,又把現代性精神引入自己的文字中。他的現代性不是凝固的,而是帶有不斷自省和突圍的能量,打開了確立自我又超越自我的開放空間。
魯迅的話語方式與詞語方式有時是反本質主義的,辭章背后有我們看不見的東西,但又有一種恒定的追求。所以,走進他的世界,除了以往的方式之外,還要了解其知識結構。
他的修養很深,對各種文化都有心得,一些研究顯得很深。不了解這些,就不會完整發現其整體性。了解這一點,就會發現我們以往對他的描述遺漏了許多元素。知識的豐富與精神的廣遠,才使其有了創作的資本。由此,對比魯迅的文字,當代的作家應當感到慚愧。
問:在魯迅博物館工作的那段時光,是不是讓您更加親近魯迅?
孫郁:魯迅博物館有較為豐富的資料,可以發現許多有趣的文物,這對我來說是一次補課。
博物館的研究室還有一個好的傳統,就是從史料出發討論問題。我過去沒有這方面的專業訓練。在博物館十余年,才發現自己的基礎不行,從而慢慢糾正自己的思路。
國內的魯迅研究有種越來越脫離史料的跡象,缺乏對于20世紀上半葉那個時代具體語境的了解,玄虛的地方有點多。當時,我身邊的幾位前輩都有扎實的根底,不尚虛言,很少空話。這種治學精神一直在啟示我、滋養我。
同時,那段時光的研究讓我真切意識到,魯迅是一個有大愛的人,他的世界沒有一點奴態;他也是一個充滿好奇心的人,能夠在新舊文化中調試出一種屬于現代人的智慧;他不斷地挑戰我們的慣性思維,以智性與詩意的方式,跨越非人道的遺存,引人到開闊光明的地方去。為此,他犧牲了自己,其慈悲的精神甚至可以與一些宗教人物相比。
問:現在不少年輕人在讀魯迅作品的時候,依然會感覺“被電擊中一般”。魯迅的思想何以影響一代又一代人?
孫郁:青年人在尋找自我的時候不斷與魯迅相逢,說明我們還在魯迅那代人巨大的話語場里。他思考的許多難題,也是今天許多青年要面臨的存在。由此我們會發現,他的精神表達方式還是那么富有啟示性。
比如,魯迅認為,人很容易成為奴隸,一方面是別人的奴隸,另一方面是自己的奴隸。為此,他鼓勵大家要靠一種精神的突圍,來尋覓新的、有智性和趣味的生活。
問:還有哪些名言警句值得推薦?
孫郁:我常常不忘的一句話是:“是故將生存兩間,角逐列國是務,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還有一段話也很感人:“人固然應該生存,但為的是進化;也不妨受苦,但為的是解除將來的一切苦;更應該戰斗,但為的是改革。”這里有先生的愛意,也有他的哲學。
問:在呈現豐富性、鮮活性的同時,是否也要警惕對魯迅的碎片化理解或誤解?
孫郁:了解魯迅,既要看文本的細節,也要有整體性觀念。對于他的一些話語,確實要放在特定語境里來理解。
比如,他曾說青年要少讀中國書、多讀外國書,主要是針對讀經復古的思潮來說的。事實上,他給朋友的孩子開列的書單,就有很多中國古書。
再如,魯迅并不否定傳統戲劇的價值,他對于紹劇、秦腔就很喜歡;京劇被士大夫化后,魯迅是有看法的,認為消失了一些原生態的東西。
此外,梁實秋、李敖都曾指責魯迅翻譯語言不通。他們不知道,魯迅的硬譯是為了增加漢語表達的功能,改變國人思想的方式,是對母語表達不周密之瑕疵的挑戰。
他輯校古籍,也不是單一的趣味問題,而是與西學的眼光有關;整理《會稽郡故書雜集》,是民俗學意識在起作用。如果只注意對于國故的態度,不觀察他整理國故時候的世界主義眼光,我們就會遺漏其思想鮮活的部分。沒有微觀體味與系統觀察的結合,對他的誤讀也就不可避免了。
筆墨的興衰,有時隱在無詞的言語里,浮在外面的表達不過是冰山一角
問:2020年是巴金逝世15周年,您特意撰寫《詩人巴金》一文。“詩人巴金”與“小說家巴金”有什么不同?
孫郁:我實際是想從詩學的層面體察他的文本力量。巴金的作品是帶有詩意的書寫,所有的文字都裹在詩意的境界里。他以詩的方式寫小說,也以小說的方式寫詩,但他的詩人氣質中沒有盲從,一直帶有自審的意味。因此,討論巴金的文學作品,應當顧及審美的脫俗意蘊和精神的超越性。這兩方面是不能分開來談的。
就寫作方式而言,他與艾青、穆旦等詩人有很多相似性,即從翻譯語言和口語中建立現代人表達的可能性,毫無傳統文人的迂腐氣。
本雅明在討論克爾凱郭爾的寫作時說,作者具有克服表象的內力,意象里存在著“通過想象而獲得安慰的美學”。百年的文學一直存在這樣的流脈,除了魯迅的傳統,巴金的傳統也值得我們進一步總結。
問:您曾提出,20世紀80年代,真正顛覆人們思想的,哲學上是李澤厚,文學上的代表先是巴金,后來轉為汪曾祺。
孫郁:李澤厚綜合了康德、榮格、魯迅的資源,使思想回歸到主體世界的路徑,這就避免了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理解。一般人接近馬克思主義是從黑格爾、費爾巴哈那里開始,李澤厚卻從康德、席勒走向馬克思主義,把思考的路徑改變了。巴金則歸到托爾斯泰主義的路徑,將人道精神呼喚出來。
汪曾祺在精神上與新康德主義接近,審美思想也屬于新康德主義延伸線上的遺存。他回歸傳統、轉向日常,由儒家的樂天與道家的逍遙,進入京派的散淡、博雅之趣,從而帶來審美路徑的轉移。他的精神底色與李澤厚有交叉之地,和巴金距離較遠。
這三位是我最尊敬的當代知識人。我的成長也得到了他們的許多啟示,所以至今心存感激。
問:在報社副刊工作期間,應該有機會接觸更多的文化人吧?
孫郁:我做編輯時,新京派開始出現,張中行、汪曾祺非常走紅,能夠約到他們的稿子算是幸事。記得有一次與同事去造訪張中行,事先沒有聯系,在沙灘旁的一棟老樓里見到先生,依然受到了很好的禮遇。張先生穿著一件中山裝、戴著一副袖套,樣子像極了胡同里的大爺,講起話來沒有一點架子。他們那一代人平民意識很濃,沒有象牙塔文人的毛病。
汪曾祺也很隨和,雖然學問深,但并不書齋氣,對百姓日常生活非常關注。有一次他打電話給我,說看到報紙上有一篇女工的文章,描寫親人病中的故事,很是不錯。為此,他特意約請林斤瀾、邵燕祥撰稿,自己也寫了篇《花濺淚》的文章。三位老人為工人作者寫的評論占據了整整一個版,一時傳為佳話。這件事給我的觸動很大,編輯工作其實也是自我教育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