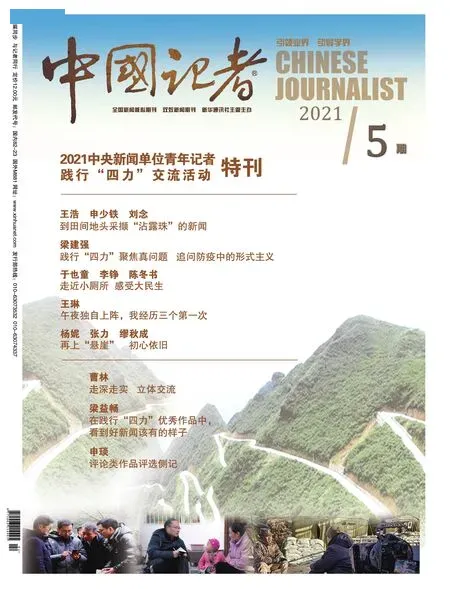在另一個(gè)與新冠病毒較量的戰(zhàn)場(chǎng)
采訪手記

掃碼閱讀《猴子得不得新冠,這很重要嗎?》

掃碼閱讀《從確定病原到疫苗藥物研發(fā),抗擊新冠為什么離不開(kāi)動(dòng)物模型》
2020年1月22日,是我們二人組因?yàn)閼?zhàn)“疫”報(bào)道開(kāi)始正式并肩而行的日子。一年間,我們以新聞圖表、海報(bào)、長(zhǎng)漫畫(huà)與文字稿件相結(jié)合的方式,試圖突破傳統(tǒng)文字稿件的限制,記錄戰(zhàn)“疫”中的真實(shí)故事,展現(xiàn)另一種全國(guó)人民齊戰(zhàn)“疫”的群像和不屈不撓的風(fēng)貌。
這片“戰(zhàn)場(chǎng)”同樣需要被讀懂
我們寫(xiě)過(guò)、畫(huà)過(guò)、展現(xiàn)過(guò)很多醫(yī)護(hù)人員、公安干警、媒體同行、社區(qū)工作者、志愿者乃至倒在戰(zhàn)“疫”一線的犧牲者的故事和形象,也產(chǎn)出過(guò)疫情期間的合租生活、學(xué)生宅家學(xué)習(xí)生活等真實(shí)有趣的條漫作品,但是還有一條更硬核的故事線,我們一直在醞釀,始終沒(méi)放棄。那就是戰(zhàn)“疫”中的科研條線。
這是另一個(gè)與新冠病毒較量的戰(zhàn)場(chǎng)。這里也是一線,重要性不言而喻。我們一直希望能有一種方式,將他們的故事好好地呈現(xiàn)一次。單就文字報(bào)道,此前我們已經(jīng)做過(guò)很多,比如關(guān)于石正麗與武漢病毒所是怎樣與病毒搏斗的,比如北京新發(fā)地、順義、大興疫情中疾控部門(mén)、離新發(fā)地最近的醫(yī)院等重要主體是怎么“破案”、為北京戰(zhàn)“疫”爭(zhēng)取寶貴時(shí)間的。但是這還不夠。
我們想成為更有效的橋梁,將生澀難懂但是卻非常重要的科學(xué)問(wèn)題轉(zhuǎn)換成生動(dòng)準(zhǔn)確的新聞?wù)Z言和視覺(jué)語(yǔ)言。如果不關(guān)注,抑或是只是粗略地帶過(guò)科學(xué)問(wèn)題,這對(duì)長(zhǎng)期奮戰(zhàn)在科研戰(zhàn)線的科學(xué)家們而言,也是一種辜負(fù),對(duì)讀者而言,也是一種損失。
中國(guó)醫(yī)學(xué)科學(xué)院醫(yī)學(xué)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研究所是我們很早就開(kāi)始關(guān)注的一個(gè)機(jī)構(gòu)。不到重大傳染病出現(xiàn)的時(shí)候,他們?cè)诠娒媲安粫?huì)有太強(qiáng)的存在感。科學(xué)家們默默做著人類(lèi)疾病的動(dòng)物模型攻關(guān)工作,十年如一日。人類(lèi)疾病的動(dòng)物模型在中國(guó)從無(wú)到有,從落后到實(shí)現(xiàn)某些研究問(wèn)題的“世界第一”,背后正是他們始終如一的堅(jiān)持。
這一次,他們的堅(jiān)持帶來(lái)了巨大的成績(jī)。通過(guò)讓動(dòng)物得上新冠,研究所完成了諸多“全球第一”:全球第一個(gè)科學(xué)證實(shí)了新冠病毒受體和致病病原體,揭示了病理特征,在國(guó)際上率先構(gòu)建了動(dòng)物模型;中國(guó)成為全球第一個(gè)可以按照科學(xué)程序研發(fā)新冠疫苗的國(guó)家;研究評(píng)價(jià)了國(guó)家部署的80%的疫苗,第一時(shí)間將該技術(shù)和標(biāo)準(zhǔn)提供給世界衛(wèi)生組織,被各國(guó)科學(xué)家和歐美疫苗研發(fā)機(jī)構(gòu)采用;國(guó)內(nèi)外第一個(gè)上市的疫苗都在這里完成評(píng)價(jià)工作。
這份成績(jī)單還在續(xù)寫(xiě)著。我們的記錄也不該缺位。
春節(jié)逢“突變”,我們與科學(xué)家一同“加班”
我們是在除夕前一日走進(jìn)中國(guó)醫(yī)學(xué)科學(xué)院醫(yī)學(xué)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研究所的。它位于潘家園的一條小街里,研究所的大紅門(mén)古色古香,門(mén)框上掛著“國(guó)家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質(zhì)量病理檢測(cè)中心”“國(guó)家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質(zhì)量環(huán)境檢測(cè)中心”“國(guó)家衛(wèi)生健康委員會(huì)人類(lèi)疾病比較醫(yī)學(xué)重點(diǎn)實(shí)驗(yàn)室”的牌子。
我們的采訪地點(diǎn)最終選在了“新冠科技攻關(guān)臨時(shí)指揮部”里。事實(shí)上這只是一個(gè)會(huì)議室,門(mén)上貼著的那張粉色的紙,賦予了這間普通會(huì)議室不一樣的意義。
在那里,我們和研究所副所長(zhǎng)劉江寧老師聊了很久,而后也跟著他了解研究所的環(huán)境,包括我們不能進(jìn)入的P3實(shí)驗(yàn)室,和那塊每年用以祭奠為人類(lèi)作出貢獻(xiàn)的小動(dòng)物的慰靈石。
盡管事前以為自己做足了功課,但是還是有一大堆錯(cuò)誤知識(shí)需要專(zhuān)業(yè)人士的點(diǎn)撥。比如,非典時(shí)期的猴子模型發(fā)燒了,新冠的沒(méi)有。中國(guó)能第一個(gè)完成新冠動(dòng)物模型是因?yàn)檠芯克恢庇米约旱目蒲薪?jīng)費(fèi)保存著當(dāng)時(shí)的非典小鼠模型,全世界獨(dú)一份。他們的工作也遠(yuǎn)比我們想象的壓力更大,任務(wù)更艱巨,作為國(guó)家部署的有關(guān)新冠肺炎五大科研主攻方向之一,動(dòng)物模型研究堪稱(chēng)是“卡脖子”的攻關(guān)環(huán)節(jié)。
當(dāng)時(shí)還有一個(gè)特殊背景,英國(guó)和南非、巴西的變異毒株是那時(shí)熱度很高的重要話題。國(guó)內(nèi)多地也發(fā)生了疫情的局部反彈,響應(yīng)號(hào)召,很多人選擇就地過(guò)年,而研究所的工作也隨著病毒的變異再次緊張起來(lái)。
為了能更生動(dòng)地講述科學(xué)家們?cè)趧?dòng)物模型領(lǐng)域的攻關(guān)歷程,此次采訪,美術(shù)編輯也和記者一同介入,直達(dá)現(xiàn)場(chǎng),和采訪對(duì)象面對(duì)面交流。圖畫(huà)不再是文字記者的衍生作品,而是凝聚了記者和美編共同創(chuàng)作的合力:我們利用視覺(jué)呈現(xiàn)讓科普變得有趣,利用文字將故事講得更深。
春節(jié)期間,我們也跟隨科學(xué)家的節(jié)奏工作著:緊張地敲定條漫文案和畫(huà)面,然后分頭行動(dòng),美編畫(huà)圖,記者寫(xiě)稿。每一步都要求嚴(yán)謹(jǐn),也比想象中更復(fù)雜。比如條漫中鼠的形象,我們一開(kāi)始找的參照?qǐng)D片便是大鼠,這不符合實(shí)際實(shí)驗(yàn)的情況,劉江寧研究員便又講解了他們實(shí)驗(yàn)室具體使用的小鼠。這種對(duì)話經(jīng)常在凌晨發(fā)生,因?yàn)樗麄兘?jīng)常是到那個(gè)時(shí)間才剛剛得空。
這篇稿子、這幅條漫也讓我們感受到這些夜以繼日的研究者的責(zé)任。成稿前后,僅條漫中的文字就大修了五次,兼顧生動(dòng)有趣和科學(xué)嚴(yán)謹(jǐn)。條漫的每一個(gè)畫(huà)面,包括轉(zhuǎn)場(chǎng),更是融匯了諸多巧思。成品發(fā)出后,有同行評(píng)價(jià)漫畫(huà)很有“電影感”,文案的最后“留白適當(dāng),余韻悠長(zhǎng)”,都讓我們兩個(gè)主創(chuàng)者感到非常激動(dòng)。
用腳采訪,用心感受,用力平衡
說(shuō)我們是這條戰(zhàn)線上的“戰(zhàn)地記者”還是標(biāo)題黨了一些。“沉迷”一線,是記者的天性。用腳采訪,用心感受,是記者的天職。
但是,具體到業(yè)務(wù)層面,我們也在反思傳統(tǒng)報(bào)道中的煽情傾向。比如采訪中我們了解到,去年全年,很多研究人員只休息了幾天,有的甚至沒(méi)有休息;有人扶著墻進(jìn)會(huì)議室吃了顆救心丸又回到崗位上;研究所的“訂單”在2020年初便排到了年底;更不必說(shuō)他們還要面對(duì)比一般實(shí)驗(yàn)室濃度高得多的新冠病毒,因?yàn)閯?dòng)物較人類(lèi)而言不易感……怎么去平衡科學(xué)和報(bào)道中的故事性,怎么既體現(xiàn)科學(xué)家的辛苦、奉獻(xiàn),又不陷入盲目煽情的俗套,是我們此次報(bào)道中著力需要解決的問(wèn)題。克制,是報(bào)道的美德。
寫(xiě)下的每一筆,都是帶著思考的。我們也將研究人員介紹的當(dāng)下的困境,概括地融入稿件。在條漫上,我們把重點(diǎn)放在有情感的科普上。在長(zhǎng)報(bào)道上,我們把重點(diǎn)放在有故事、有細(xì)節(jié)的人身上。細(xì)微的變化,是我們對(duì)兩種不同表現(xiàn)方式的判斷,是希望這個(gè)“組合拳”能拳拳到肉,而不是博眼球的“形式主義”。
在確立選題到最終產(chǎn)出中,我們得到了研究所的細(xì)心幫助,也得到了編輯劉世昕老師的悉心指導(dǎo)。我們沒(méi)有將眼光局限于報(bào)紙版面,而是真正從精品內(nèi)容、精品創(chuàng)作出發(fā),不計(jì)較得失;對(duì)自己、對(duì)采訪對(duì)象、對(duì)題材,乃至對(duì)那個(gè)特殊階段我們國(guó)家數(shù)不清的科研戰(zhàn)線上的工作者負(fù)責(zé),做好記錄者的角色。
我們的嘗試才剛剛開(kāi)始。未來(lái),我們將用更豐富的創(chuàng)意,更精致的表達(dá),更負(fù)責(zé)的態(tài)度,一步一個(gè)腳印,將青年的視角轉(zhuǎn)化成生產(chǎn)力,心無(wú)旁騖地踐行中國(guó)記者的使命與擔(dān)當(dā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