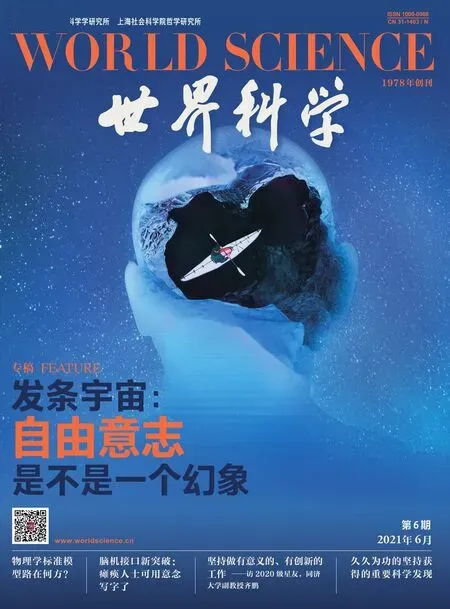射電天文學是怎么揭開宇宙奧秘的?
編譯 喬琦
如果請天文學家挑選出天文學史上最令人激動的一張照片,那么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會選擇你常常能見到的那個橙色環。乍看之下,這張照片似乎也沒什么了不起——無非就是一個底部微微隆起的模糊發光的甜甜圈,2021年3月的時候還加上了一些曲線細節——但實際上,這個不起眼的圓圈是人類第一次窺見黑洞,它的顏色并不是黑洞的真實顏色,而是反映了黑洞本身及其周圍的射電輻射強度。
這張照片的清晰度非常高,就相當于身處華盛頓特區卻看清了遠在洛杉磯的一枚硬幣上的日期。照片中的橙色環其實是一個5 500萬光年之外、質量相當于65億個太陽的黑洞。照片中的微小細節則表明,這個黑洞正在順時針轉動,并且每年都要消耗相當于上千個地球質量的物質。而那些最近剛添上去的曲線則是強磁場的特征。
黑洞無疑是整個物理學領域最為神秘的物體之一,而這張史無前例的黑洞照片則是射電天文學為我們帶來的諸多發現中的最新作品。這張著名照片背后的科學內涵足以令人震驚,但讓其成為可能的這門科學本身也同樣令人印象深刻。正是因為有了射電天文學,全世界的天文學研究者才能以一種全新的方式協同工作,一道研究宇宙的奧秘。

卡爾·央斯基利用一架昵稱叫作“央斯基的旋轉木馬”的巨大天線在偶然間發現了宇宙射電信號
射電波段位于電磁譜的一端,那兒的電磁波攜帶的能量都比較低。人類探測到的第一批射電波是在19世紀末通過人工手段由帶電加速粒子產生的。射電波(無線電波)調制簡單,且波長較長,可以不受干擾地傳播很遠的距離,因此,人類發現射電波后,就立刻意識到它是極好的通信工具。20世紀初,物理學家知曉了像閃電這樣的自然現象也會產生射電波。不過,這類射電波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我們想要剔除的“噪聲”,因為只有把自然產生的射電波除去,我們才能提升無線電通信技術的分辨力、功率和覆蓋范圍。
1931年,卡爾·央斯基(Karl Jansky)正是在朝著這個目標努力的過程中偶然發現了“天體射電噪聲”。物理學家央斯基當時也是貝爾實驗室的工程師,他設計了一個寬100英尺(約合30米)、高20英尺(約合6米)的巨大天線陣列,并將其安放在幾輛福特T型車底座上,這樣就能讓天線自由轉動并指向空中的所有方向。同事給這個裝置起了個昵稱,叫作“央斯基的旋轉木馬”。
央斯基使用這架天線開展工作后,發現收集到的數據中始終有一個微弱的噪聲。央斯基憑借旋轉木馬的機動性追蹤了這個噪聲的源頭,并且最終確定了它的位置:天線收集到的射電噪聲并不是附近的雷暴,也不是地表附近的零星噪聲源——它探測到的是來自銀河系中心的能量。
央斯基的發現勾起了主流天文學界的好奇心,但反響并不算熱烈。由于正值大蕭條時期,各大天文臺都不愿意把本就有限的資金投入未來不明的新技術領域。不過,一位名叫格羅特·雷伯(Grote Reber)的科學家兼工程師認為央斯基的這項發現很有意思,并且立志要把自己的整個職業生涯都拿來研究這個來自宇宙空間的射電信號。在申請貝爾實驗室的工作被拒后,雷伯決定在伊利諾伊的自家后院建一個屬于自己的射電望遠鏡:主體是一個直徑31英尺(約合9.45米)的拋物面,上方直接裝有射電波接收器。

1988年,站在西弗吉尼亞格林班克雷伯天線前的格羅特·雷伯
雷伯的努力取得了巨大成功,他不僅重復了央斯基的發現,還繪制了人類第一幅全天射電圖。此外,他還發現了一些明亮的射電發射源。我們后來才證實,它們是遙遠的星系和近期爆發的超新星留下的遺跡。1940年,雷伯在《天體物理學期刊》(TheAstrophysical Journal)上發表了文章,他的工作也勾起了天文學界對射電觀測更廣泛的興趣。
射電這種波長較長的電磁波為天文學家打開了一扇觀測宇宙的全新窗戶。通過射電望遠鏡,天文學家就能探測到遙遠的昏暗熱源發出的射電輻射,還能以之前從未想到過的極端方法觀測有關加速帶電粒子的奇異物理學。射電望遠鏡率先發現了“脈沖星”——那是一種快速轉動著的致密天體,它們是大質量恒星死亡后的遺跡,率先發現了宇宙微波背景輻射(攜帶著大爆炸信息的宇宙“光”),率先發現了星系(包括我們所在的銀河系)中心都存在超大質量黑洞的蛛絲馬跡。值得一提的是,央斯基當年收到的來自銀河系中心的噪聲很有可能就是那個地方的超大質量黑洞發出的。所有這些現象要是只在可見光波段觀測,顯然都不會有什么成果。
射電天文學取得的科學成果令人驚嘆,但對于習慣了擁有閃亮鏡面的光學望遠鏡的人來說,射電望遠鏡就顯得很是奇怪了。不過,考慮到射電波那么長的波長,那么射電望遠鏡反射面的這個大盤子其實也足夠“閃亮”,足以將從天上收集到的射電波反射到接收器中,這個過程和普通光學望遠鏡的鏡面將可見光反射到目鏡中并沒有什么兩樣。此外,射電望遠鏡遵循的原理也和普通光學望遠鏡一致:一樣都是口徑越大性能越優秀,一樣都是放在昏暗的地方(消除地面光源的干擾)觀測才能更高效地工作。

位于波多黎各的阿雷西博望遠鏡在2020年垮塌之前,始終是全球最大的射電望遠鏡之一
望遠鏡鏡面越大,我們就能收集到越多的光線,也就能觀測本身更加昏暗的天體(想象一下你身處黑暗房間中瞳孔放大時的情景)。此外,望遠鏡的焦距越長,我們拍出的照片就越加清晰(想象一下身在場館邊線的體育賽事攝影師為捕捉清晰動態畫面而使用的長焦鏡頭)。高清晰度常常是天文學研究中的關鍵目標,因為有了高清晰度,我們才能準確找到遙遠星系中的各個恒星,才能準確繪制星云的形狀,而射電天文學研究的是電磁譜中的長波波段,這就給我們提供了另一種建造大型望遠鏡的方式。射電望遠鏡的有效口徑可以大到令人咋舌的程度,這多虧了一種叫作“干涉”的技術,也即將諸多由小射電望遠鏡組成的觀測陣列收集到的數據匯總到一起,從而達到單架超大望遠鏡的觀測效果,進而為天文學家繪制出超高清晰度的圖像。
干涉測量學是一門令人望而生畏的學科,但它也給人類帶來了極有意義的成果——正是憑借這項技術,事件視界望遠鏡才得以將分布于視界各地的8座射電天文臺統一起來,形成一架觀測效果相當于整個地球的巨型望遠鏡,從而拍攝到這張著名的黑洞照片。
因此,“大”顯然是射電望遠鏡能夠做到的。那么,“暗”呢?解決這個問題的難度就要高多了。諷刺的是,央斯基的最初目標——過濾掉自然界中的射電波源,從而為通信技術的發展掃除障礙——現在已經徹底反轉:射電天文學家如今正在現代電子學時代通過這些自然射電波源研究整個宇宙。如果你的眼睛能夠看到射電波,那么你所在的房間中就會顯現出一大堆令人眼花繚亂的射電信號:無線網絡發出的射電波足以形成云狀,附近手機的零星閃光也能發出射電波,甚至路過汽車的火花塞產生的微小火光也有射電波相伴而生。
要想阻止這些稀奇古怪的射電波淹沒來自宇宙的數據,一種方法是限制望遠鏡附近的人工射電信號。實際上,西弗吉尼亞的格林班克天文臺就是這么做的。這座天文臺位于美國國家無線電靜默區深處。為了把射電噪聲降到最低,無線電靜默區嚴格限制了相關技術的使用,比如:禁止使用無線網絡、手機和微波設備,且在這一地區內行駛的所有車輛都使用柴油發動機。(即便如此,此地的研究人員還是曾經因為射電干擾而失去寶貴的觀測時間。當時產生干擾的是一群在叢林間飛躍的松鼠。附近的一項保護研究為了掌握有關松鼠遷徙習慣的資料而給這些嚙齒動物戴上了GPS項圈。)構成事件視界望遠鏡的各座天文臺散布在全球各處,但所有地點都有一個共同點——無論是南極,還是阿塔卡瑪沙漠,抑或是夏威夷最高山峰——那就是都位于極其偏僻的地方,盡可能地遠離人類不斷發出的射電噪聲。
人類掌握的新技術不斷增加著射電噪聲的影響范圍,這點無疑令人沮喪,但同時,這也帶來了一種誘人的可能性:我們是否會在未來的某一天觀測到不是我們自己產生的人工射電波?

坐落于美國國家無線電靜默區深處的西弗吉尼亞格林班克望遠鏡。這一地區禁止使用某些設備,以保證從宇宙中收到的射電信號不會受到干擾
一直以來,天文學界始終把射電天文學看作搜尋其他世界信號的絕佳方式。實際上,第一項射電天文學實驗可以追溯到比央斯基收到銀河系中心信號更早的1924年8月。當時,火星來到了近100年內離地球最近的位置。美國天文學家趁此機會為“國家無線電靜默日”做宣傳,呼吁大家在固定的時間間隔內停用無線電設備,以便接收鄰居“火星人”發出的無線電信號。美國海軍天文臺甚至往一艘飛艇里發射了一個無線電接收器,為的就是收集潛在的火星人訊息,同時還專門配備了一位密碼學家以便隨時破譯這些信息。
如今,地外文明搜索行動(SETI)已經是一項正式的科學項目了。在弗蘭克·德雷克(Frank Drake)和吉爾·塔特(Jill Tarter)等著名科學家的帶領下,SETI項目研究者通過使用加州艾倫望遠鏡陣列等難得的設備,擁有了在射電領域作出驚人發現的可能。畢竟,我們在地球上為遠距離通信而使用的無線電波同樣也會向外傳播,也即向整個宇宙廣播我們的文明擁有相當程度技術的能力。同樣地,遠方的文明也完全有可能發出類似的信號,甚至是有目的地傳遞這些信息,因為他們使用的電磁譜和我們并沒有任何不同。
毫無疑問,射電天文學為我們帶來了無限可能:有了它,我們就能看到遙遠黑洞中本來完全看不見的內容,就能打開全新物理學的大門,甚至可能發現第一件有關地外文明的證據。雖然在外行人看來,射電望遠鏡或許在外觀上有些滑稽,但它們卻是天文學研究中的無價之寶,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未來,它們都會不懈地為我們揭開一個又一個宇宙之謎。
資料來源QuantaMagaz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