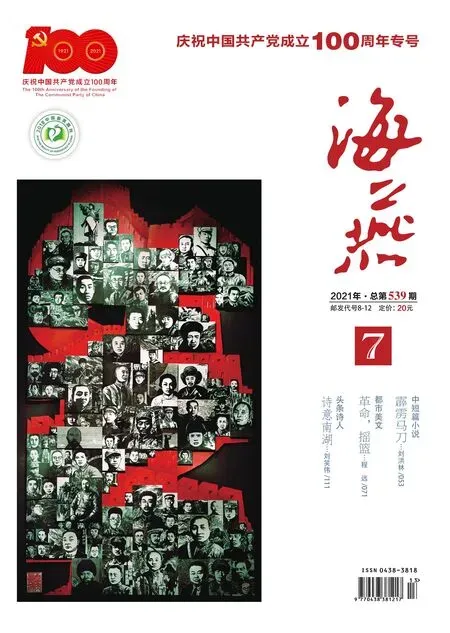田園之夏
萬華偉
我去銅嶺村時,正是夏天。陽光從婆娑的枝葉縫隙里灑下來,在路面落下不同形狀的斑點。四周安靜,風穿過漫無邊際的林子,各種鳥的啁啾聲傳進我耳膜的時候,變得如羽毛一樣輕柔,輕吸一口氣,每一片肺葉里,都是草木的清香。
出了丘陵,便是豁然開朗的平原。遠遠望去,大片的綠色掩著錯落的農舍。拐進路邊的牌坊,進入一個蔬菜主題公園。水渠兩邊種著薰衣草,穗狀的花序舉起一片幽藍,倒映在水里。有風的時候,影子慢慢洇開,平靜的水仿佛注入了色彩和香氣。彩葵就在路邊,尺把高的苗兒,密密匝匝,心形葉片上爬過清晰的脈絡,白里帶紫。這些都是通往陽光的道路。離花開還有些時日,只能面對著它們,想象各種顏色的花瓣在陽光下燦爛綻放的光景。遠一點是辣椒,青椒指向土地,白色的花朵面朝天空,這是花和果的特質,輕盈和厚重,涇渭分明,一種最尋常的植物,詮釋了春華秋實的哲理。玉米長得比人還高,葉子宛如一柄長劍,交叉糾纏,刺向繽紛的陽光,拳頭般的棒子鑲嵌在綠葉之間,紫色的須微微蜷曲。像武士頭盔上那一簇鮮艷的紅纓,正好暗合了這片土地的意蘊。
這里有一片古墓群,是楚文化的標志地。這里曾是一個古戰場,曾經有數不清的紅纓在鐵馬秋風里飛揚。一路踩過來的是歷史的塵埃。伸手可觸的是楚人的血淚和榮光。走過玉米地,看到一畝畝稻田。晚稻剛插下去不久,水光托起開始返青的葉片,流動著一片盎然的生機。水稻是貼在南方村莊上的一枚標簽。每一片葉片后面,都藏著一條路。這條路通向某一個農家院子,院子的門口,坐著皮膚被太陽曬成古銅色的男人。遠處的荷塘邊,幾個女孩子在拍照。她們反復擺著造型,不停地調整著自己的肢體動作。最后似乎是滿意了,身子后仰,雙臂張開,頭微微抬起望著天空。飛揚的青春后面,荷葉亭亭如蓋,風隨意地搖動著白色的、粉紅的荷花,送來淡淡的荷香。幾只黃色的蝴蝶扇動翅膀拍打著鏡頭,它們并不知道,就在這一瞬間,短暫的影像獲得了永恒,成為了這片熱土上的一個符號,供很久以后的長夜里作為記憶來打撈。

插圖:邢安贏
出了公園沿著公路走一段,就到了另一邊的梅園。入眼全是梅樹。修直的、彎曲的、虬枝密布的、截掉了樹梢的。它們以不同的姿勢攻陷了這片五百畝土地的一角。路還在修,路邊堆了些長條形的麻石。大概是準備用來鋪路的。石頭邊上,月季好似在靜靜地燃燒,火焰從綠色的葉子中升起。黃金蝶開得正旺,花形如蝶,仿佛能聽到拍打翅膀的聲音。我一邊信步走著,一邊想著梅花盛開時的景象,寒風獵獵,白雪皚皚的平原上,浮動著一片云霞。云霞里晃動著一個個人影,從中傳來風聲、笑聲和雪花翩然飛舞的聲音,還有一雙雙腳踩在雪地上的“嚓嚓”聲,熱烈與冷寂形成鮮明的對照。古老的土地被這樣一種全新的形式喚醒。眼下,梅花早已凋謝。花影在時間里淪為塵土,而風中似乎還殘留著冬雪的凜冽,能聞到梅花的香味,看到風雪潰敗時丟棄在花瓣上的冰紋。梅子黃時家家雨。但雨并沒有下,陽光均勻地灑落,把枝條上一串串的梅子染得金黃。柔軟的枝條被壓向地面,呈現出一個個難以察覺的弧度。梅子挨挨擠擠,滿懷喜悅。沒有誰去動它們,聽其落向露水滴落的早晨、悠長的午后,或者雨水淅瀝的黃昏。在路過一處水塘時,看到成群的青蛙在岸上撲騰。很快一只接一只撲進水里。水花四濺,受到驚嚇的野鴨鉆出草叢,在水上輕盈地掠過。
大半個上午,我就這樣漫無目的地在村莊里走著。路過一家家農舍。屋邊的菜地里,黃瓜蒂上還綴著花,茄子彎彎地墜在植株上,南瓜藤悠閑地爬過,黃豆郁郁蔥蔥。菜地邊上,石榴樹綴滿嫣紅的花朵。偶可遇見一群群的雞鴨中間,夾著幾只大白鵝,在屋后的小樹林里自由自在地歌唱。偶爾有一口池塘,有人搬了凳子坐在樹蔭下垂釣,清冽的池水,恰到好處地捕捉到了云朵、屋檐、人影及樹影。地上是一種生活,水里是同一種生活。一條魚彈出水面,“咚”的一聲又落進水里,蕩起一圈圈漣漪,把水里的煙火揉成一幅層次分明的畫。
走累了,去村部歇腳。經過一棟小樓,走進一個院子。圍墻邊的玉蘭花開了,樹上像掛著一盞盞乳白色的燈。從樹下經過,我第一次感到玉蘭花香氣原來那么濃郁。幾個老人坐在那里看書,趁著放下書的間隙,我和其中的一位攀談起來。老人姓鄭,已年近古稀。他告訴我,這個村莊原來叫銅鈴崗,傳說關羽在這里馴馬時一只銅鈴掉落,然后這里就變成了銅鈴的形狀。后來改名為銅嶺村。大凡傳說都是有共性的,無一例外的帶著人格傾向,寄寓了熾熱的情感和美好的祈愿。楚人的先輩們希望腳下這片土地像一只銅鈴,堅如青銅,風雨不摧,一代接一代在大地之上清脆地搖響。愿望美好,而現實總愛與之為忤,殘酷地碾碎希望的光芒。有很長一段時間,這里和眾多的村莊一樣苦難沉重,一度成為荊州地區典型的貧困村。這片土地與水的關系一度不甚和諧,河流曾經來過,那是在很早很早的時候,后來因為各種原因逃往了別處,一年又一年風沙淹沒了它們流過的痕跡。有一年大旱,導致莊稼顆粒無收。許多人只好外出謀生,以至人口大量減少。農耕時代,偏僻、干旱、貧窮、饑餓,這些帶著冷色調的詞語,成為銅鈴村曾經夢魘般的痛。村民們拖家帶口,背井離鄉都是迫于無奈,就像當年山東人闖關東、山西人走西口,無不是為了混口飯吃,不在通往異鄉的路上越走越遠。一步一回頭,一堵斷墻,一樹槐花,一片高梁地,都是插在他們心里的刺。
改革的春風吹來后,這片沉默的土地開始煥發出生機。村里抓住這個契機,硬化了道路,修好了水庫和標準化的水渠,完成了基礎設施。從2015年開始,采取土地租賃、自愿入股、招商引資等多種形式,自籌資金150多萬元,走上了現代農村觀光旅游的致富路。
銅嶺村的發展有自己的特色。開發了那么多項目,卻沒拆一棟房子。即使在公園內,沒人住的空房子依然會保留下來,經過修葺后做民宿。在這里,我就見到了一棟這樣的房子。房子并不大,普通的民居。木窗,白墻,黑瓦依偎在一棵大樹下。里面空蕩蕩的,什么也沒有。不久之后它將在設計者的手下,迎來別具一格的轉身,成為城市的棲息者喚醒鄉愁的驛站。綠化做得這么好,但從未在外面買過一根苗木,村里有自己的苗圃,所有用來綠化的苗木都由自己的苗圃提供。不管是什么項目,除了技術性特別強以外,都不用外地勞動力,道路硬化、蔬菜栽種、綠化、餐飲、接待都由村民自己來做。這樣做,發展速度是慢了一些,但是環境沒有被破壞。山巒、田土、林木、農舍像鐘表一樣固守著原來的秩序,村莊還是熟悉的村莊,不是城市的翻版。它面目溫和,既有“陽春白雪”的景致,又有“下里巴人”的煙火。同時節省了成本,為村民提供了就業崗位,解決了剩余的勞動力。
“發展最快是近幾年的事。”老人自豪地說。我笑著問他:“假如現在在城里送你一套房子,請你去城里住,你去不去?”老人呵呵一笑,“那我不去,還是這里好!這么好的環境,多少錢都買不到。不光我不會去。現在一些出去的人都回來了。”
老人說的話不假,村里完成基礎設施后,一些在外創業的村民也看到了巨大的變化,陸續回鄉發展。金用武是土生土長的銅嶺人,一直從事園林綠化,早年將本地的苗木運往公安縣銷售,后來生意越做越大,業務遍及浙江、上海等沿海省市。他看到家鄉的發展勢頭后,選擇回鄉建了一個梅園,先期投資2000萬元,流轉土地450畝,現已栽種各種苗木,分為梅花園、海棠園、櫻花園、采摘園。對他而言,效益并不是最重要的。環境的美化、故鄉的發展、帶動更多人創業,才是他念念不忘的所在。
不到三十歲的馬聶,從國有單位辭職回來,已成為蔬菜產銷合作社的發起人。合作社通過各種渠道籌措資金1200萬元,流轉土地1000畝,集瓜果蔬菜采摘、農家趣味體驗、果樹菜地認購代租、年豬家禽認購代養、親子種植體驗于一體,另建成一座游客服務中心,日接待量可達1000人。在馬聶的心里,故鄉并非只是一般人心中的概念那么簡單,早已賦予了新的內涵,不僅僅是從那里傳來過自己第一聲帶血的啼哭,也不僅僅是身體里蘊藏著這方水土的氣息,而是他心中的藍圖。他要在這里揮灑色彩,實現自己生命的價值。
告別老人,已是中午時分。我來到了游客接待中心,這是一個四合院,白墻黛瓦,紅色的走廊圍繞著一個巨大的水池,池水清幽,偶爾有幾條魚游到邊上,像在窺視走廊上來回穿梭的腳步以及一張張浮著笑容的臉。這里供應的都是農家土菜,產自蔬菜主題公園。綠色食品,農家口味,從田園到餐桌,簡單清爽,正好慰藉繾綣的鄉愁,撫平心中的憂思。
我從鄉村走出來,故鄉與他鄉。鄉愁與鄉土,一直沉沉地壓在心中。這些年讀書,我往往會在一個個深夜里,在書本中走進一個個村莊,似乎只有蕭索、破敗、空寂這些元素。似乎在一夜之間,大地上的村莊都已人去屋空,只剩下一片荒蕪。馮驥才、十年砍柴和黃燈等一批作家把這里歸結為城鎮化進程的后遺癥,他們試圖用過度的焦慮來拯救村莊。事實上,這樣的村莊終究是極少數,隨著時間的流遠,只要留得住綠水青山,只要留得住鄉愁。很多人從一片土地上出走,還會重新回到了那一片土地。畢竟那里是他們血脈的源頭,精神之旅的歸宿,是生他養他的故土,那里有他的父老鄉親,有他摯愛的親人,有他兒時的玩伴,有血濃于水的親情,有無盡的鄉愁。只要身體里的血還在流動,生命還在延續,村莊就不會消失,它們只會以新的面孔出現在我們的面前,這正是中國農村和中華民族新的希望所在。
離開銅嶺村是午后時分,車行駛在公路上。平原遼闊,但見姹紫嫣紅。輕風拂來,鼻腔里進進出出的是滿滿的花香,布谷鳥的聲音遠遠地傳來。我真希望,時間就這樣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