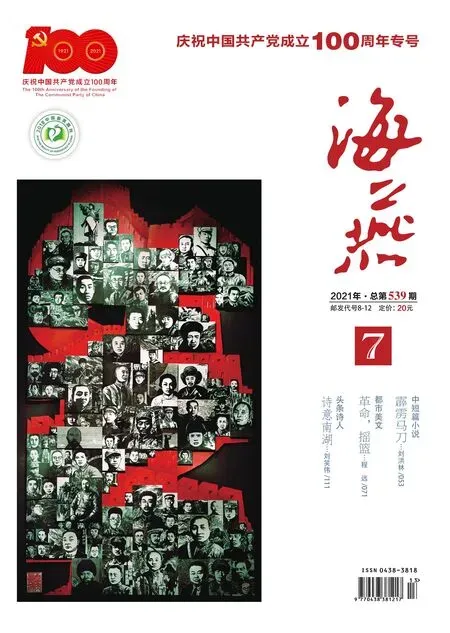尋找桃花島
周勝春
剛來濕地不久,張嚴馮村的一個朋友打電話給我,說有兩箱桃子放在停車場的門衛室里,叫我下班去拿。我一怔,三垟特產不是甌柑嗎?干嘛到別處買來桃子送給我,我自己可以去買。他說就是本村人種在島上的本地桃子,不是舶來品,很是好吃。我方才知道,這片溫水氤氳的土地上,特產品種除了聞名遐邇的甌柑、黃菱,作為配角的楊梅和桃子也占據了一席之地。
關于桃子的前世今生,我在已經寫完還在修改階段的街道志里找不到相關的內容。負責編寫的鄭老師告訴我說,在志中甌柑、黃菱自是長篇累牘,不惜筆墨,楊梅也有按其地位詳略不同的篇章,但是桃子是前幾年才開始種植,況且也就張嚴馮那一小片地種植了一些,沒有歷史沉淀需要的年代感和區域的普遍性,而其個體的獨特性也還沒凸現出來,因此寫不出來。但桃子的品種,出自名門正派,純正血統的水蜜桃,據說與奉化的玉露美人同一血脈,是村里人經過精挑細選而來。當初在選擇時,跟其他特產一樣,是結合了濕地的特性,選擇適宜在水陸之交島上種植的品種。實踐證明,這個選擇是正確的。
正確的原因在于,桃子果實個子又大又圓,皮又薄又細,汁水恰到好處。它的汁不多不少,全都流到嘴里,致使滿嘴芬芳四溢,軟硬度也恰如其分,韌性跟牙齒的咬合力天然配備,無縫銜接。還處于換牙期的兒子吃了之后,嘖嘖稱贊,從此跟菜市場和水果市場上的桃子告了別,每年專等濕地桃子成熟期的到來。
因為有河,有島,我尋探桃花島的心也就順理成章。不光是要印證這桃花朵朵,在這濕地里盛開,與藍天、與白云、與流水的結合,會是怎樣美妙絕倫的一幅美景,還有從此以后,關于尋找桃花島的過程和心境,就像陶淵明筆下的武陵人尋找桃花源一樣,成為我的目標和方向,可以拿出一輩子后半部分的時光,與它來一個無法確定的約定。張嚴馮的村長說,水波漫漫,云霧深邈,桃樹林不知何處,找到村委會,便會知端倪。鄭老師說,遠在天邊,近在眼前,我尋探的是歷史,其他不關乎歷史的物事,沒有印象。
這一耽擱就是四年,雖然一直想著,但一直沒抽出空來。期間有花期過了,有春雨的簾幕阻擋,有忙碌的日常,自然也有自己懶惰的天性。
2021年清明放假之機,我借值班的間隙,開車過去欲進濕地查探,圓一個多年的心愿。但在節日里濕地公園的熱度達到沸點,甌海大道上行人和車子像三峽大壩里堵滿著的水。最怕堵車的我選擇了落荒而逃,但由此也暗暗下了決心,一定要趕上今年的花期,否則又是一年長長的等待。
2021年四月春夏之交的一個下午,趁著陽光正好,春風正煦,想起正是百花盛開之際,桃花應該也還是艷麗芬芳,我再一次開啟了尋找桃花島之旅。車子從沙河路口進入,兩邊有坐著靜眸河水的老人,沿著瑤池浹河岸邊的小徑到頭,對于目標沒有明晰路線的我選擇了往右處拐,那是一座橫跨在湖上面的鋼結構新橋,名叫水鄉橋。莊稼成熟的氣味似透過屏幕鉆進我的鼻孔,明媚敞亮打開的心門在上面飛翔,那溫暖的浪漫讓我心旌蕩漾。不想這條四五百米長的路是出外的單行線,蒙騙了我,一圈過后我又回到了進口的原點甌海大道上。
憑著若無若有的記憶以及中午從同事處問過來的路徑,我轉左邊,經過沙河橋,沿著沙河右轉,在田野之間的一條僅容一輛車子通行的水泥路一路往南。此時春風拂面,神清氣爽,四周鮮花盛開,花香撲鼻,青草蔥籠柑樹搖曳,水流輕漾鷺鳥躍空,羅山隱隱白云迢迢,人間芳菲沒有盡,這人間的四月天,霎時讓我將所有對于眼下的糾結拋置腦后。打開車子所有的窗門,一降到底,讓所有的風物、溫度和氣息全都進來,使整個世界都站了進來。河流、田野和山川,鮮花、石頭和泥土,它們各綻風姿,像一個個小天使,活蹦亂跳,剎那間好像打開了一扇一直閉塞著的山門,“山門中斷夢江開”。頓時整個腦殼和胸膛被打開,心曠神怡,難得人間好風景,難得人生多瀟灑。我只想停下車子,站在田野間,四周花木簇擁,高歌一曲,如在電影《音樂之聲》里一樣,在陽光與山坡田野之間,在碧波與藍色氤氳之間,在白云與青水之間,在鮮艷與芬芳之間,像個孩子,騎上不羈的野馬,不停奔跑。
張嚴馮村委會前的張嚴馮橋上的轉彎迂折幅度很大。我根據同事的提醒,打滿方向盤的半徑,慢慢轉道上去,幾條只有1米來高的鐵欄桿已經銹跡斑斑,下面是碧波蕩漾的張嚴馮河。我有點戰戰兢兢地開過,經過村委會后,再行經過一座筆直的老橋,將車子停在河對岸一個荒地里,決定用腳步來尋找桃花島。
我心目中的桃花島,應該是“島上郁郁蔥蔥,一團綠、一團紅、一團黃、一團紫,繁花似錦……東面北面都是花樹,五色繽紛,不見盡頭,只看得頭暈眼花。花樹之間既無白墻黑瓦,亦無炊煙犬吠,靜悄悄的情狀怪異之極。”它也應該是“墨痕乘醉灑桃花,石上斑紋爛若霞。浪說武陵春色好,不曾來此泛仙槎。”或者至少也是我腦海里虛構的畫面,水中央的小島上,在水流的氤氳中,在天上陽光、藍天和白云的倒映里,像一個空中花園,又像一個水中迷宮。綠油油的桃樹枝葉可垂水,花朵盛開在枝頭,花瓣白里透紅,艷紅欲滴。它們緊挨在一起,像火焰烈唇燃燒煥發,像晨曦晚霞燦爛乍現,花比葉大在虬枝上像鑲上的一個個小球,漫天的紅星飄灑飛舞,少數垂掛沒有迎著朝陽,在盈盈水間映照,在耀眼光處相映紅。誰又犯著了誰,誰綻開了第一朵,誰又落下了第一朵,誰在雨里哭成了淚花,誰又失去了那一縷陽光,誰的萎縮在夜里含著清淚,誰的綻放讓白天風華絕代。在這青山眉黛,在這綠水輕泛,在這綠意繽紛處,它的風貌,自是別出一格,風姿綽約。
河岸邊垂釣的人們,依靠在柑樹下或者小葉榕下,不知道他們有沒有發現桃花島的蹤影。平時三三兩兩在田里忙活的老農,此時倒不見了蹤影,就連停在樹梢的麻雀,泛河剪水的甌鷺,也沒有啪啪飛起,或橫掠過水,或輕偎綠枝。
我終于在老橋西首岸邊一個殘垣斷壁處發現了一棵一人多高的桃樹。從地形方位和遺跡來看,它是人家房子的院子里,房子拆掉后,桃樹幸運地留了下來。想必它也曾用果實串起孩子的竹桿與那一雙清澈渴望的眼睛,也曾用朵朵花瓣串起下面人們欣喜愛情的眼神,用果實換來他們的笑臉。如今它的花期已過,在綠葉蔥籠處的枝頭和枝椏間,結出了一個個如紐扣大小的果實。可惜了桃花,四年的遺憾,還要在上面再加一年。
一斑窺豹,桃花島就在這附近?我開始尋找,即使沒有花開,也要找到它們。但是行經一片片水域,碧波微漾中沒有給我消息;踏過一段段阡陌,縱橫交錯間沒有指路;轉過一排排甌柑林,隨風搖曳著沒有方向,除了遠處的水蓮宮在水中蕩漾著,一如既往的風情萬種。我腳下萋萋芳草在搖頭擺尾,四周樹枝綠葉簇簇,似乎在調侃著我的無知和盲目。
此時陽光的強度增大,我不免焦躁起來。
我到達每條河岸,看到一個一個在水中聳立的小島,如果再行拉長距離的話,其地界已不在張嚴馮。我垂頭喪氣,只好折回身子到車上打道回府。就在車子拐上半月形的張嚴馮橋上中央至高點時,往西漸墜的陽光突然沖開了層層云霧,在混沌蒙昧一般的凝重之中突然射出一束光亮來,亮堂堂地照在張嚴馮河上,似乎天被盤古開天辟地割開了一道口子。頓時春和景明,晴光四射起來。此時我看到水中的一座孤島,它似乎是從水中升起來,又或是從天上降下來。它的上面外圍種滿了桃樹林,我沒看到它們艷麗的花骨朵,一葉知秋,那顆桃花就已給出了答案。
我再次停下車子,跑過田埂,穿過樹林,踏過芳草,跨過田野,在一垛坍塌的舊房墻旁,一條U形清波攔住了我的腳步。水中有一座開滿桃花的小島,在微波之中輕扭腰肢,輕灑綠光,在光亮之下清翠欲滴。原來張嚴馮人都是通過擺渡來種植桃子的。
這個島會不會就是桃花島,就是桃花源的入口,直通水底,有與世隔絕世代相傳的原始居民,有金華雙龍洞一般的內部翻天覆地變化的玄機,有地底800米的水下遠古世界……
在返回的路上,風吹在頭上,吹干了發上和臉頰的汗珠,我渾然不覺。我的結論是:這就是桃花島,而桃花源,整個濕地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