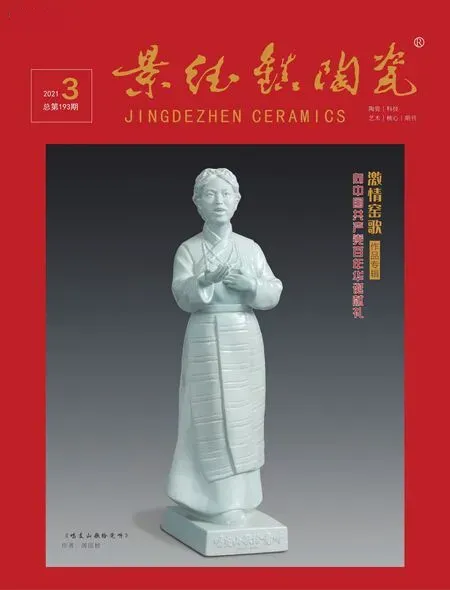明成化青花海水白龍紋天字罐之特點
李秀普 李曉希
(1.湖北省收藏家協會;2.中國建設銀行湖北省分行)
此件明成化青花海水留白暗刻五爪九龍紋天字蓋罐,通高11.3厘米、口徑6.9厘米、底徑9.6厘米、腹徑12.5厘米、蓋徑8厘米。器型為直口、短頸、圓肩、鼓腹、廣底、圈足、圓蓋。成化天字罐非常美麗稀罕,中外館藏展品只有十來件斗彩的,足見這件青花天字罐的珍稀程度和藝術魅力。本文就其質地、紋飾、款識等方面特點,談一談初淺的看法,以拋磚引玉。
一、器型玲俊奇秀,質地溫潤素雅
天字罐器型玲瓏、俊俏、奇秀,質地溫潤、潔凈、雅致(圖1),直接體現了明成化官窯青花瓷追求胎質、彩質和釉質精致完美,且“三質”各臻其妙、相互襯托的瓷藝成效。
一是胎質精美。首先,白細瑩潤。天字罐的底圈足與蓋沿底邊露胎,前者平切,后者平切且兩邊棱斜削,有多處粘沙,胎面干燥、緊皮等氧化特征典型,看上去潔白致密,細潤晶瑩。其次,巧薄輕盈。主要體現在透影和重量兩方面。在透影方面,從內透視,青花圖案一目了然;從外透視,暗刻紋飾清晰可見。在白熾燈光下,內外透視,胎色牙黃閃紅(圖2)。在重量方面,天字罐帶蓋只有552克,與宣德體量相仿的蓋罐相比,重量格外顯輕。若考慮天字罐內外釉質更為肥厚,胎體更輕。再次,剛勁穩固。此罐型制別致,線條優美,全憑薄胎塑造和支撐,歷經了分段拉坯、高溫焙燒等多道工藝和數百年的光陰洗禮,至今無任何變形、綹裂,展現了胎質的剛性和韌性。
二是彩質精美。天字罐青花彩質靛藍、亮麗、柔和、沉靜的風格,極具時代特色。與進口青料蘇麻離青發色艷麗、濃淡不一、鐵斑豐富、泛紫明顯、暈散突出的特點相比,天字罐青料呈發色清新、濃淡相近、鐵斑稀少、泛紫隱約、暈散輕微的特點;與國產青料平等青雜質近無、色澤淡雅、藍中閃灰的特點相比,天字罐青料呈雜質較少、色澤明快、藍中閃紫的特點。天字罐這一青料特點,是成化前期官窯瓷器繼續使用宣德剩余的進口蘇麻離青,并將國產的平等青參兌其中混合應用的結果,由此一改宣德濃艷為成化幽婉,使成化官窯早期青花彩質極富魅力,獨歩一時,成為絕唱。反映了成化本朝對前朝青花工藝的繼承和創新,也證明了天字罐為成化早期作品。

圖1 罐身罐蓋一側

圖2 胎色黃中閃紅
三是釉質精美。天字罐身、底、蓋的內外施釉色質同一,豐腴瑩澤,如脂似乳,光清晶亮,潔白溫潤。看透度,釉質肥厚,蒙脂感強,釉下紋飾如云遮霧障,為青花平添淡雅,為暗刻隱身潛形。看開片,外釉布滿深度老化的冰裂紋,而里釉無一絲裂紋,非常奇妙。看氣泡,釉中氣泡因釉下有無青花而不同。青花處,小氣泡密集,大氣泡眾多,且沿著青花筆道分布排列。正視,大氣泡之上的釉面平光瑩亮。側視,大氣泡之上的釉面如同棕眼;留白處,小氣泡密集,大氣泡無幾。看表面,總體上均勻光平,比較特別的是,鐵銹斑個小量稀,鉆胎入骨,釉面隨之下凹,形成小窩點;罐的內口沿積釉一圈,外底釉微有起伏,有波浪感。這兩種現象都不明顯,不經意很難以發現,為部分成化官窯瓷器所特有。
二、青白相間互映,紋飾生動精妙
天字罐除蓋沿為白底青花金錢紋外,蓋外頂和罐身外壁均為青花弧線水紋,留白浪花和暗刻九條五爪龍紋,呈現出群龍行走騰飛于海浪之中的景象。細品龍紋,形態生動而精妙。
第一,胎體藏工筆。在釉下留白的胎體上,暗刻龍紋,線條細如游絲,工正細致,有工筆畫的風格(圖3)。其上白釉肥厚,自然光下難見蹤影,有一種“藏”的感覺。借助強光透視,龍紋頭形扁方、閉嘴瞠目、鼻端凸起、雙角后傾、頭發上揚、眉須豎立、身體修長、鱗甲密集、背尾帶鰭、身出綬帶、四肢肌健、肘毛飛動、爪如圓輪。諸如這些,均是通過清晰而準確的雕刻呈現的,對進一步從細節上把握成化龍紋特點,大有脾益。
第二,釉面如寫意。與釉下留白胎體暗刻龍紋的精雕細刻相比,釉上的白釉龍紋簡略了具體細節,突出了身軀修長,英俊秀麗的基本神態,富有寫意畫風格。通景觀察,白釉龍紋與青花海水銜接的所有邊沿,無青花描繪,龍紋的嘴、牙、五爪、身鰭、頭發、眉毛、胡須、肘毛等均有朦朧感,白釉龍紋的全身幾近無青花描繪,存有幾絲“卡通”味道,只有雙眼以青花點繪,有畫龍點睛的神妙,展現出一幅白釉龍紋與青花海水紋青白分明、相應成趣的美麗畫卷。
第三,形態各相異。以形態大體相似為標準,天字罐上的九條龍,可分為五類。一類為單龍,位于罐蓋之上,頭部在下方,往左方平沖。其余四類分別是,頭部低背繞環龍、頭部高背繞環龍、行走龍和轉身回頭龍,四類各一對,每對分別位于罐身的上下兩層,形成蓋頂一龍,罐身兩層八龍的陣列。在“九龍五類”中,各個類別形態不同,同類中的兩龍相似而不相同。以頭部低背繞環龍為例,此類中的兩龍,相同之處是,都是龍頭向右繞環,頭部低于背部。差別之處是,一條龍頭繞環朝前,低于龍背的幅度大,龍尾在右;另一條龍頭繞環朝后,低于龍背的幅度小,龍尾在左(圖4)。這種“九龍五類”,形態各異,神形兼備,栩栩如生的表現手法,增強了紋飾的藝術效果 。

圖4 龍頭低背繞環
第四,九龍潛規矩。前文說到的天字罐“九龍五類”,不見文字記載,卻在一些明清瓷器和建筑物上,有前承后啟的脈絡。山西大同九龍壁建于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是朱元璋第十三子朱桂在山西大同王府門前的照壁。該照壁上的“九龍五類”用五種顏色區分。正黃色龍是一類,稱主龍,排列中間。其他四類分別是,淡黃色龍、金黃色龍、黑紫色龍和黃綠色龍。每類兩龍,以主龍為中心,依次分列在主龍左右兩側,形成九龍“一”字陣列。建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的北海九龍壁和建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的故宮九龍壁,均是“九龍五類”,陣列形式與大同九龍壁一致。事實表明,存在于明清不同瓷器、建筑物上的九龍紋飾,盡管每條龍紋和每類龍紋的具體形態有別,陣列形式不一,但“九龍五類”的基本規矩卻一直在延續。這種潛藏的龍文化現象,是有待于研究的新課題。
三、字體端莊清勁,款識獨特寓趣
天字罐底心楷書青花“天”字款識,書風端莊清勁,為成化朝所首創和獨有。其有何用意、用于何器物、特征何在、何人書寫等,至今說法不一,恰似猜迷,別有寓趣。
其一,關于天字款的用意。一種說法是,古代宮廷器物常常用《千字文》字的先后順序編號排序,而《千字文》開篇的第一個為“天”字,將“天”字書于成化皇帝喜愛的瓷罐上,以示其為“天下第一罐”。另一種說法是,成化皇帝下旨制做精美的天字罐,告誡群臣,自已受命于天,是真命天子。雖然兩種說法不同,但都將天字款的用意歸結為成化皇宮御用物品的標示。天字罐的五爪九龍紋飾,為這個結論提供了最直接的佐證。原因是,從元代延祐起,已有明確規定,皇室采用五爪龍紋,同時用在瓷器上,在往后包括明代成化在內的近600年中,都只能皇室御用。
其二,關于天字款的器物。對書寫天字款的器物,最主流的說法是只見斗彩天字罐。這種觀點的依據是館展實物。過去,各地展出的館藏天字罐,都是繪天馬、海水龍、纏枝蓮等主題紋樣的斗彩天字罐,沒見青花天字罐。但從歷史的經驗看,沒見館展,不一定沒有館藏,更不一定沒有民藏。青花天字罐的面世,證明了天字罐不光有斗彩的,也有青花的,由此將天字款只見斗彩的認知推到一個新的階段。
其三,關于天字款的特征。對此,中國著名古陶瓷專家孫瀛洲先生總結為:“天字無欄確為官,字沉云濛在下邊。康雍乾仿雖技巧,字浮云淡往上翻”。意思是,官窯天字款的“天”字,外圍無邊無欄,青花下沉,因釉厚而顯朦朧。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時期都仿過此款,但青花飄浮。青花天字罐的外底中間以青花楷書的“天”字(圖5),其周圍無邊線,青花沉穩,鐵銹斑隨筆跡自然分布,深入胎體,其多少與運筆的重輕相關。豐腴的釉層和眾多氣泡覆蓋,給人一種云霧隱現的感覺。這些特征與孫先生的四句訣高度吻合,再一次印證了它的客觀性和權威性。

圖5 楷書青花款識
其四,關于天字款的書寫。討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天”字是誰的字體、誰的手筆兩個方面。談及此事,還得看可靠的物證。在1980年第三期《紫禁城》上發表的《皇帝畫的漫畫——一團和氣》中,插有故宮博物院藏的成化皇帝朱見深的《御制一團和氣圖贊》書法照片(圖6),其中有“天”字和“一”、“大”、“二”、“人” 等與“天”字局部相同的字。將天字罐的“天”字與之對比,無論全部,還是局部,都筆跡相近,書風相同。由此推測,天字款應是成化皇帝的字體,是工匠仿成化皇帝字體書寫的。至于天字罐上的“天”字與題跋上的“天”字筆畫不盡相同,是仿寫難以避免的,可怱略不計,既便是皇帝親筆書寫,也不可能像鈐印彼此一樣。
青花天字罐風格別具,青花水紋、留白浪花和暗刻五爪九龍等工藝,在當今屈指可數的天字罐中,僅見于此,堪稱珍中之珍,其型制、胎骨、青花、釉質、紋飾、款識等都呈現了成化官窯瓷器特征,存載大量的、珍貴的、有些是唯一的物證信息,對學界拓展認知范圍,建立認知體系,更客觀、科學地賞析成化天字罐的風采,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圖6 成化皇帝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