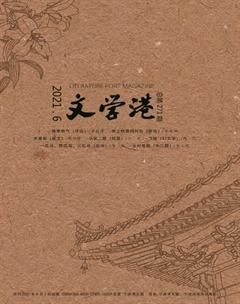紙上桃源歸何處: 胡竹峰的“文化思愁”
季亞婭
當代有胡竹峰這樣的文字,一定有它的深意。
我喜歡看他交待文字來源,從先秦到魏晉到唐宋到晚明再到民國,說自己寫的是有自主意識的“中國文章”。如此重視傳統與來路,理論和創作完成自問自答的完美閉環,足見其諄諄之心。自問自答何嘗不是因為孤獨。新文學百余年的歷史推崇創新,復古和傳統一向不合時宜。他像一位生錯了時代的穿越者,著昔時青衫返身逆行,嘆一聲吾道孤矣。
在散文閱讀上我的偏好是洞見和新意,以及在這洞見和新意中呈現的作者的胸襟、品質、情懷和世界觀。我喜歡智識性內容勝過搖曳多姿的文辭,喜歡呈現當代新的經驗、延展我經驗地圖的文字;或者它雖然在經驗范圍之內,但讓我重新認識這種經驗、帶來新的思考角度的文字。同時也在反省,我這種對于散文的觀念來自于哪里。往下細究,相比詩歌和小說,目前關于什么是好的文章、好的散文的標準,出現了共識分裂。什么是當代散文?今天我們要如何理解散文與傳統文章的關系?散文的敘事形式如何與當代生活的復雜度形成對應關系?胡竹峰提供了一個契機,在五四之后、在楊朔式的應試體散文和當代新散文運動之后,再次去思考散文的傳統和現代轉型問題。
談論它要回到五四。相對于小說、詩歌、戲劇等其他文學門類,散文在新文學運動中是轉型最成功、受眾最廣泛,也是常常被當成白話文運動成功范例的文學門類。民國時期的散文絢爛多姿,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散文有著可以借鑒自先秦諸子一路而下的文章傳統,而這個文章傳統又與當時新的媒體形式報刊平臺十分相稱。傳統與現代的結合所形成的文章之“變”,形成當時關于白話文應該怎么寫的共識,我們關于現代散文的想象和審美標準是那時候形成的,并通過語文課教學將這個標準固定下來。成功來得太輕易,后來者們享用著這個傳統所帶來的審美與接受的諸多便利,也必然承當“影響的焦慮”之負擔。我們太容易陷入到什么是好文章、什么是美文的窠臼中。白話詩歌的絕處逢生、奮力一掙,反而完成了現代詩歌的新范式建構,散文寫作在當代生活和當代人前所未有的復雜經驗面前出現了惰性。因此,本世紀初周曉楓、張銳峰、寧肯、祝勇等人的新散文運動,正是試圖從理論、文體形式、寫作內容等方面對五四形成的文章標準全面越界,對什么是好的散文的共識預設來一次全方位的修正。后來的寫作者,包括雜志編輯們的趣味選擇,仍處在當年這一次變革的余蔭之中。可以說,散文的現代轉型,對適合表現現代人經驗的文章形式的探索,迄今仍然在進行之中。
在這樣文學史流變的框架下再來看胡竹峰,他竟是不理會這個“新”的,“偏偏喜歡舊氣”(《舊氣》),“滿心舊人”(《腔調》),他的核心時間詞匯是“舊時”。可以猜測同樣是不滿于時文腔調,他的方式是把被前人嚼過、簡化了的傳統在清水里洗滌一遍。如果說創新必得先熟知、認知傳統,民國的這群寫作者對所謂“中國文章”,是熟知在心、是他們無意識的寫作資源的一部分;后來白話文寫作的第二代、第三代,卻沒有這個幸運,他們是二手傳統喂養大的人。胡竹峰慕古人、讀原典,有他一整套古典文化理想或曰“文化思愁”。換言之,他通過閱讀和記錄這些閱讀,確認自己與傳統、與前人的關系,進而確認自己的寫作坐標。
《木屑集》寫的是故園與古書。他讀古書留意系譜,《筆記》自先秦諸子一路而下到民國,胃口大而駁雜,但也講究氣息相通、心跡相投。說起來他還是受民國人文章偏好的影響,顯然喜歡六朝文字多一點,明清小品多一點,唐宋文章少一些。少時他以一冊《古文觀止》打底,習的是好文章的樣態和章程,筆墨俊秀卻仍有規束過的痕跡。但他也想看看文廟之外的天地,所以他讀碑讀簡,說中國文章有三神,銘文精神,竹簡精神,碑帖精神。他以筆記體梳理的文章譜系顯然也受傳統文論的影響,重評點、感悟和體認。比如辨認文字的音色和腔調,說柳宗元有玉佩從容之音,而漢賦如箜篌石破天驚,皆是玲瓏慧眼。更重要的是,他把這些文章安放在一個特定環境里,比如雪夜讀書,雪落在萬古也落在紙間;農人與學童在田間往來問答,云霧自宋畫里翩然而出,燈下細品紙上紅梅,門前癩葡萄可入畫。他的鄉村景觀里沒有當代時間,江山社稷皆是雪泥鴻爪,惟明月前身亙古不變。這些瑩然可喜的事物,在他筆下終歸都是“通往安靜故園”。
在故園讀古書,胡竹峰這樣的姿態意味深長。他所謂文化思愁,是在說這樣的文字、語匯與感受所涵育的中國文章,正是唯有從這樣的故園里才能生長出來,也只有這樣的姿態才能更好地抵達他所懷念的那個傳統本身。這是一整套美學典范與古典時代人們生活方式、情感方式的統一,胡竹峰將目光從遠方拉回到萬古,將故園與古書合二為一,搭建了一座復古主義的紙上桃源。至此,他完成了寫法和活法的統一,把時間問題置換成了空間,把現代以來我們一直在眺望的那個遠方變成了故園。
一個悖論是,故園因何而成“故”?如果傳統本身也是“現代”的發明,怎樣才是進入傳統、繼承傳統的方式?當年古文運動,韓愈借復古之名行革新之實。胡竹峰所追慕認同的民國諸位先生,雖在舊傳統里浸染長大,想的卻是那“新文章破殼而出”。實際上《木屑集》提到早年接觸的民國文字,大概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到本世紀初出版界的“民國文章熱”,與新散文運動大致同時,其初心也是對楊朔體言志派散文不滿而引入其他資源以求變革。今天講民國文章之美,是否依然要寫得和周作人、汪曾祺一樣?脫離語境把民國文章當成標本來模仿,把它的美學標準固定化,學得越像就越違背它當初出現時的求新初衷,變成了民國文章的反面。古典語匯所對應的風聲雨聲、紙間白云的傳統審美形式,它背后這一整套古代生活和農耕文明的世界觀、一整套感受和描述世界的古典智識,已經和仍然在發生變化。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當代田園有機器轟鳴、有高鐵穿行還有里程和經緯度。進入傳統只是繼承傳統的第一步。要成為傳統延續和生長的一部分,必然包含這樣的命題,怎樣從故園和古書里長出我們自己的當代性。當代作家與田園的關系里還有張煒和韓少功。這是我對胡竹峰下一步的期待。不是把故園僅僅簡化為一種審美形式,一座紙上桃源或烏托邦,而是嘗試用這種形式去處理現代化了的田園,以及這現代田園里必然復雜化了的當代情感,這情感也許不是那么自足圓滿、平和雅正而必然包含了焦慮。學我者生,似我者死。什么是當代散文,當代散文又將以何種形式去處理和回應當下生活的復雜性,千年文脈仍在叮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