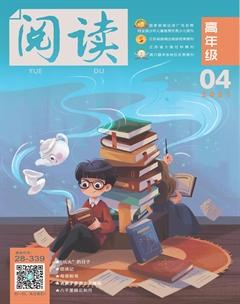讀書瑣憶
琦君

我自幼因先父與塾師管教至嚴(yán),從啟蒙開始,讀書必正襟危坐,面前焚一炷香,眼觀鼻,鼻觀心,苦讀苦背。桌面上放十粒生胡豆,讀一遍,挪一粒豆子到另一邊。讀完十遍就捧著書到老師面前背。有的只讀三五遍就瑯瑯地會背,有的念了十遍仍背得七顛八倒。老師越生氣,我越發(fā)心不在焉。肚子又餓,索性把生胡豆偷偷吃了,寧可跪在蒲團(tuán)上受罰。眼看著裊裊的香煙,心中發(fā)誓,此生絕不做讀書人。何況長工阿榮伯說過:“女子無才便是德。”他一個(gè)大男人,只認(rèn)得幾個(gè)白眼字(家鄉(xiāng)話形容少而且不重要之意),不也過著快快樂樂的生活嗎?
但后來眼看五叔婆不會記賬,連存折上的數(shù)目字也不認(rèn)得,一點(diǎn)辛辛苦苦的錢都被她侄子冒領(lǐng)去花光,只有哭的份兒。又看母親用顫抖的手給父親寫信時(shí),總埋怨辭不達(dá)意,十分辛苦。父親的來信,潦潦草草,都請老師或我念給她聽。母親勸我一定要用功,我才發(fā)憤讀書,要做個(gè)“才女”,替母親爭一口氣。
古書讀來有的鏗鏘有味,有的拗口又嚴(yán)肅,字既認(rèn)得多了,就想看小說。小說是老師不許看的“閑書”,當(dāng)然只能偷著看。偷看小說的滋味,不用說比讀“正經(jīng)書”好千萬倍。我就把書櫥中所有的小說,一部部偷出來,躲在遠(yuǎn)離正屋的谷倉后面去看。此處人跡罕至,又有陽光又有風(fēng)。天氣冷了,我發(fā)現(xiàn)廂房樓上走馬廊的一角更隱蔽。阿榮伯為我用舊木板在墻角隔出一間小屋,屋內(nèi)一桌一椅。小屋三面木板,一面臨欄桿,坐在里面,可以放眼看藍(lán)天白云,綠野平原。晚上點(diǎn)上菜油燈,看《西游記》入迷時(shí)忘了睡覺。母親怕我眼睛受損,我說欄桿外碧綠稻田,比坐在書房里面對墻壁熏爐煙好多了。我沒有變成“四眼田雞”,即緣于有此綠色調(diào)劑。
小書房被父親發(fā)現(xiàn),勒令阿榮伯拆除后,我卻發(fā)現(xiàn)一個(gè)更隱蔽安全處所。那是花廳背面廊下長年擺著的一頂轎子。三面是綠呢遮蓋,前面是可卷放的綠竹簾。我捧著書靜靜地坐在里面看,絕不會有人發(fā)現(xiàn)。萬一聽到腳步聲,就把竹簾放下,格外有一份與世隔絕的安全感。
我也常帶左鄰右舍的小游伴,輪流地兩三人擠在轎子里,聽我說書講古。轎子原是父親進(jìn)城時(shí)坐的,后來有了小火輪,轎子就沒用了,一直放在花廳走廊角落里,成了我們的世外桃源。游伴們想聽我說書,只要說一聲:“我們進(jìn)城去。”就是鉆進(jìn)轎子的暗號。
在那頂“轎子書房”里,我還真看了不少小說呢。直到現(xiàn)在,我對于自己讀書的地方,并不要求如何寬敞講究,任是多么簡陋、狹窄的房子,一卷在手,我都能怡然自得,也許是童年時(shí)代的影響吧。
回想當(dāng)年初離學(xué)校,進(jìn)入社會,越發(fā)感到“書到用時(shí)方恨少”。而碌碌大半生,直忙到退休,雖已還我自由閑身,但十余年來,也未曾真正“補(bǔ)讀生來未讀書”。如今已感歲月無多,面對爆發(fā)的出版物、浩瀚的書海,只有由著自己的興趣,與有限的精力時(shí)間,嚴(yán)加選擇了。
我倒是想起袁子才(即清代詩人、詩論家袁枚)的兩句詩:“雙目時(shí)將秋水洗,一生不受古人欺。”我想將第二句的“古”字改為“世”字。因他那時(shí)只有古書,今日出版物如此豐富,真得有一雙秋水洗過的慧眼來選擇了。
清代名士張心齋說:“少年讀書,如隙中窺月。中年讀書,如庭中賞月。老年讀書,如臺上望月。”把三種不同境界,比喻得非常有情趣。隙中窺月,充滿了好奇心,迫切希望領(lǐng)略月下世界的整體景象。庭中賞月,則胸中自有尺度,與中天明月,有一份莫逆于心的知己之感。臺上望月,則由入乎其中,而出乎其外,以客觀的心懷、明澈的慧眼,透視人生景象。無論是贊嘆,是欣賞,都是一份安詳?shù)南硎芰恕?/p>
(文章有刪節(jié))
感悟:
少年時(shí)期,對知識的渴求促使作者想方設(shè)法地去讀書。也正憑著這一腔熱忱,作者逐漸感悟到書海無涯,須日日積累、細(xì)細(xì)甄選。這樣,才能成為一個(gè)真正快樂的讀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