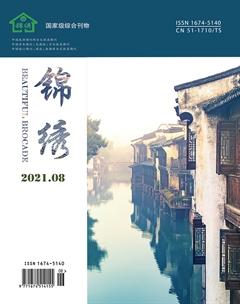中國(guó)當(dāng)代攝影中的鄉(xiāng)愁文化
馮子琪
鄉(xiāng)愁是中國(guó)文化自古以來(lái)的重要情愫。李白旅居洛陽(yáng)時(shí)寫(xiě)道“此夜曲中聞?wù)哿稳瞬黄鸸蕡@情”;范仲淹的思鄉(xiāng)之情凝結(jié)成“濁酒一杯家萬(wàn)里,燕然未勒歸無(wú)計(jì)”的悲涼詩(shī)句;余光中的鄉(xiāng)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我在這頭,大陸在那頭”,這承載著幾代人的家國(guó)鄉(xiāng)愁。可見(jiàn),有關(guān)故鄉(xiāng)的思愁一直是伴隨著中國(guó)社會(huì)的發(fā)展而行的,這也成為了許多經(jīng)典不朽的藝術(shù)作品的靈感來(lái)源。在當(dāng)代攝影語(yǔ)境的建構(gòu)中,鄉(xiāng)愁意識(shí)也作為一粒種子在攝影創(chuàng)作中蔓延開(kāi)來(lái)。
21世紀(jì)的中國(guó)處在現(xiàn)代性轉(zhuǎn)型和變革的關(guān)鍵時(shí)期,而這一由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過(guò)渡的歷史階段早在幾個(gè)世紀(jì)前就在歐洲國(guó)家已經(jīng)發(fā)生。隨著西方工業(yè)革命和市場(chǎng)革命的推進(jìn),現(xiàn)代科學(xué)技術(shù)和城市化不斷普及,地方與地方之間的差異性縮小,取而代之的是跨越民族和國(guó)家的全球一體化。現(xiàn)代性把人類(lèi)統(tǒng)一在了一起,基于這種現(xiàn)代性帶來(lái)的共同歷史境遇,一種區(qū)別于傳統(tǒng)鄉(xiāng)愁的“現(xiàn)代型鄉(xiāng)愁”隨之出現(xiàn)。
自上世紀(jì)80年代開(kāi)始,國(guó)內(nèi)攝影群體逐漸成長(zhǎng)和進(jìn)化,國(guó)外各種藝術(shù)思潮傳入中國(guó)這與我們的傳統(tǒng)藝術(shù)觀念相互滲透影響,再加上當(dāng)代社會(huì)文化及藝術(shù)變得多元而復(fù)雜化,這都是促進(jìn)藝術(shù)走向自覺(jué)的因素。相比其他藝術(shù)門(mén)類(lèi)而言,在表現(xiàn)人與世界的關(guān)系上,攝影這一機(jī)械復(fù)制媒介無(wú)疑是最直接而有力的創(chuàng)作方式之一。它不僅可以真實(shí)地記錄人類(lèi)所依賴(lài)的真實(shí)世界,同時(shí)也為我們觀照自我提供了條件。
一、自我意識(shí)的回歸
有些攝影師以“文化鄉(xiāng)愁”為情感依托,選取現(xiàn)實(shí)生活中曾與自己息息相關(guān)的懷舊之人或物作為拍攝素材,在拍照這一行為中理解和尋找自我。攝影師魏壁在廣州、大連生活了二十余年后重返家鄉(xiāng)湖南夢(mèng)溪,回歸至最原始的生活狀態(tài)。在尋鄉(xiāng)和回到故鄉(xiāng)的過(guò)程中他分別創(chuàng)作了作品《夢(mèng)溪》、《夢(mèng)溪2》系列,用詩(shī)意化的影像記錄了故鄉(xiāng)的人和景,也有一些鄉(xiāng)村器物,也許是留有親人指紋和體溫的器物,將鄉(xiāng)愁視覺(jué)化、可視化。形式上,魏壁深受古人書(shū)畫(huà)理論的影響,將詩(shī)、書(shū)、畫(huà)相結(jié)合,最后裝裱在宣紙上,以此向宋元畫(huà)家對(duì)話(huà)。魏壁從馬遠(yuǎn)、董其昌、黃賓虹等大師那里汲取靈感,將古人心中的理想與他看到的現(xiàn)實(shí)相疊,以此試圖找回自己的精神家園。近幾年國(guó)內(nèi)與之類(lèi)似的作品還有李止《山行》、顏長(zhǎng)江和肖置安的《歸山》、塔可《詩(shī)山河考》等。他們像修行路上的游子一樣,將情感投射至土地和傳統(tǒng)中去,形成這種帶著觀念意識(shí)的影像語(yǔ)言,從而達(dá)到物我之間的相互映照,疏解作為現(xiàn)代人的困惑和糾結(jié),回歸寧?kù)o的精神家園,找回個(gè)體在時(shí)代變化中的自我認(rèn)同。
二、民族身份的確立
鄉(xiāng)愁意識(shí),實(shí)際上是歷史滲透在血脈和精神中的民族心理體現(xiàn),它包含的是一整個(gè)民族的自我認(rèn)同和歸屬問(wèn)題。新銳攝影師呂格爾的《羌的山》系列是一個(gè)基于家鄉(xiāng)汶川羌族的創(chuàng)作計(jì)劃,他用虛構(gòu)紀(jì)實(shí)的方法呈現(xiàn)了羌族文化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化之間的矛盾,進(jìn)而實(shí)現(xiàn)對(duì)個(gè)人及地域的身份和歷史的探索。整個(gè)項(xiàng)目分為《羌的山》、《上山尋海》、《星海》三個(gè)章節(jié),攝影師用田野考察和民族志的方式記錄羌的影像,通過(guò)對(duì)于時(shí)間和空間的回溯,將受現(xiàn)代化沖擊的古老文明與現(xiàn)實(shí)對(duì)峙,進(jìn)而尋找兩者之間的某種制衡。他的圖像不是工整的檔案式陳列,而是在尊重和構(gòu)建歷史的基礎(chǔ)上進(jìn)行的半虛構(gòu)的“體驗(yàn)性”創(chuàng)作。例如《上山尋海》中,攝影師帶著鏟子爬到姜維城的山上去“考古挖掘”,把這一過(guò)程用照片和視頻形式記錄下來(lái),進(jìn)而印證小時(shí)候從長(zhǎng)輩那聽(tīng)來(lái)的“汶川過(guò)去是海”的言說(shuō)。這種將個(gè)人記憶與集體記憶相結(jié)合主客觀并存的拍攝手段成為當(dāng)代攝影中一種慣用的敘事模式,這類(lèi)影像也正是基于民族精神和傳統(tǒng)文化的關(guān)注,通過(guò)去記錄逐漸消退與流動(dòng)的民族文化和地方特性,從而達(dá)到喚起人們對(duì)個(gè)人和地域身份的認(rèn)知和思考的目的。
三、城市景觀的隱喻
鄉(xiāng)愁作為一種創(chuàng)造性的情感投射,既可以映射到田園鄉(xiāng)村中,也可以呈現(xiàn)在現(xiàn)代城市里。人們對(duì)現(xiàn)代鄉(xiāng)愁的需求一方面源自對(duì)田園生活和慢生活的懷念,另一方面也是對(duì)資本侵入過(guò)后的工業(yè)化、城市化的反抗。1976年,由喬治·伊斯曼之家策劃的攝影展《新地形:人為改變的風(fēng)景的照片》中,攝影師就將鏡頭不約而同地面向城市中的建筑、人造景觀和被改變的自然風(fēng)貌,記錄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中波德萊爾所說(shuō)的“中間性的臨時(shí)狀態(tài)”。攝影師唐晶《生長(zhǎng)》系列即呈現(xiàn)了中國(guó)城市化高速發(fā)展中的城市景觀。他選擇北京和武漢為拍攝對(duì)象,記錄了那些不斷向天空擴(kuò)張和拆除改造的老房子。在照片中,可以看到城市空間與建筑的個(gè)性化喪失、逐漸趨于一致的現(xiàn)代性問(wèn)題。作為生活的主體,在舊城區(qū)和歷史建筑大量滅絕的過(guò)程中,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和思索我們所生存的環(huán)境。類(lèi)似這種表現(xiàn)城市化進(jìn)程中所帶來(lái)的懷舊、異化和擴(kuò)張問(wèn)題的作品近幾年也不斷涌現(xiàn),例如李林《消逝的風(fēng)景》、曾瀚《超真實(shí)中國(guó)》等,他們關(guān)注的內(nèi)容最終都指向一個(gè)問(wèn)題,即在物質(zhì)世界大行其道,人們的精神生活變得異化和模式化的當(dāng)下,人所面臨的境遇如何?
總的來(lái)說(shuō),隨著社會(huì)轉(zhuǎn)型和藝術(shù)家的自我覺(jué)醒,攝影藝術(shù)中的鄉(xiāng)愁“基因”已從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轉(zhuǎn)變,從單一的懷古走向自我身份與民族文化的找尋,鄉(xiāng)愁文化也作為中國(guó)攝影的“母題”不斷滋養(yǎng)著攝影藝術(shù)的成長(zhǎng)。鄉(xiāng)愁基因激發(fā)著攝影語(yǔ)言的探索,同時(shí)也成為創(chuàng)作者進(jìn)行生命精神探索的重要工具。沒(méi)有得到反思的懷舊會(huì)制造出魔怪。懷舊不永遠(yuǎn)是關(guān)于過(guò)去的,懷舊可能是回顧性的,但也可能是前瞻性的。對(duì)于過(guò)往的懷念,應(yīng)該對(duì)于未來(lái)的現(xiàn)實(shí)具有直接的影響。當(dāng)現(xiàn)代型鄉(xiāng)愁滲透到攝影中,一種新的視覺(jué)樣式開(kāi)始形成,個(gè)人傳記或群體或者民族傳記之間的關(guān)系,個(gè)人記憶和集體記憶之間的關(guān)系也在攝影中呈現(xiàn)出了新的內(nèi)涵。
(中國(guó)藝術(shù)研究院?北京?1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