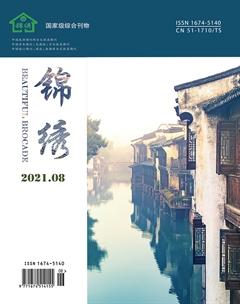論知識產權屬于私權的法理基礎
《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在前言中指出“知識產權屬于私權”,并且不允許成員對該條款作出保留,這表明知識產權作為私權在國際條約當中得到承認和強調。但是,由于科學技術特別是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公權力干預社會經濟領域的深度和廣度不斷擴大,甚至滲透進了傳統私權調整的領域,有學者據此認為知識產權發生了公權化轉變,提出了知識產權“私權公權化理論”。但是,筆者認為,知識產權“私權公權化理論”是對知識產權權利屬性的錯誤認知,知識產權本質上是一種私權,它不可能公權化。
一、知識產權“私權公權化”的質疑
“私法的公法化”、“國家干預論”以及“利益平衡理論”對于知識產權“私權公權化理論”從不同角度進行了解讀,但這些學說都能不否定知識產權的私權屬性。
(一)私法的公法化不等同于 “私權公權化”
西方國家堅持“私權神圣”的理念,在早期推動了資本主義制度的確立和發展,但隨著生產方式的社會化程度不斷提高,過度強調“私權神圣”理念造成了貧富差距加大、社會矛盾叢生等問題,為了緩和社會矛盾,很多學者對“私權神圣”理念進行了反思,私法公法化學說便是代表性的理論之一。可見,“私法公法化”是一種緩解社會矛盾的工具性措施,是“私權神圣”理念在社會發展中的自我革新,并不能據此認為“私法公法化”理論否定了知識產權的私權屬性。
(二)國家干預不等同于“私權公權化”
法律上的權利一定是受限制的,無論這種限制來自于外部公權力還是來自權利自身。如果知識產權受到公權干預就認為具有了公權屬性,那么幾乎所有的權利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公權力的干預,比如物權、人身權等,是否可以認為這些權利也具有了公權性質呢?顯然是不能的,認為私權受到公權力干預就具有了公權屬性,那么只會混淆私權與公權的界限,甚至動搖私權制度的理論根基。
(三)利益平衡不等同于“私權公權化”
利益平衡理論并不是單獨適用于知識產權的一種理論,由于知識產權天然具有“合法壟斷”的特性以及存在權利濫用的可能性,法律必然要對其進行適度的限制。知識產權制度是調整人們在創造、運用知識和信息過程中產生的利益關系,是一種在肯定私權前提下的對私權范圍的必要限制,目的是平衡協調私權自治與公共利益之間的關系,并非要否定知識產權的私權屬性。
二、知識產權“私權公權化”理論可能產生的危害
如果認可了知識產權“私權公權化”理論,認為知識產權來自于公權力的授權,那么公權力就可以在公共利益或宏觀調控的名義下,強勢地干預知識產權人的自治空間。一是,為行政權對知識產權的非法干預提供法理借口。以行政權力壟斷知識產權性權利證書或稱號的授予、以政府的名義對私人知識產權客體的優劣或價值進行評判,背離了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極大傷害市場經濟的運作效率,損害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二是,可能將知識產權理論研究引入錯誤方向。知識產權私權公權化理論導致私權與公權的界限模糊,對知識產權的權利屬性進行了不恰當的定性,可能動搖知識產權制度甚至整個私權制度的根基,把知識產權理論研究引入錯誤的方向。三是,可能造成私權理念的倒退。由于社會制度的原因,私權觀念長時間屬于批判的對象,制約了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知識產權私權公權化理論把公權化思路加入到知識產權這個原本是私權保護的領域,可以說是不適宜的。
二、知識產權屬于私權的法理分析
(一)勞動價值論在認定知識產權私權屬性上的應用
洛克在《政府論(下篇)》中指出,每個人的身體所從事的勞動和他的雙手所進行的工作,是正當地屬于他的,所以只要他使任何東西脫離自然所提供的和那個東西所處的狀態,他就己經使它成為他的財產。就知識產權來說,創作人或發明人的創作發明實際上也是從自然狀態中加工提煉事物的過程,其自然應享有產權。侵犯知識產權就是侵犯別人的原始產權,就是侵犯別人的“自然賦予的”自然權利,就是侵犯社會的最基本倫理。
(二)知識產權私權屬性中的“自由意志”和人格財產權精神
德國法學家康德提出了“自由意志”理論,從個體意志層面來說,知識產權的客體是無形物,權利人很難對其進行有形的自然占有,因此知識產品作為權利人意志創造的外在對象,更加需要法律上的保護。從共同意志層面來說,知識產品之所以能夠成為財產權的一種,決定因素并不是自由意志的結果,而是社會全體成員對知識財產的承認和尊重。由于知識產品本質的無體性,因此它也更依賴于國家的暴力機關對其進行特殊的保護。
黑格爾將知識產品看作是個人人格的衍生品,它反映出的人格在更深層次上來說是意志自由。如果將知識產品的人格屬性歸屬于公權力的賦予,那么就為公權力恣意干涉個人意志自由提供了理論上的借口,這顯然不利于自然人的人格獨立和意志自由,勢必造成法學理論的退步。
(三)社會工具論對知識產權性質的認定
1996年,澳大利亞學者彼得·德霍斯( Peter Drahos)出版了《知識財產法哲學》,在當代知識產權法領域引發了理論研究的熱潮。
1.知識產權是在“抽象物”上設立的權利
在德霍斯看來,知識產權應當屬于無形財產,這就像“法律假定在某些抽象物中存在著權利”。[1]在識別抽象物時,應當注意到抽象物與有形財產之間的對應關系。其一,抽象物如果想被外界感知,需要以某種有體形式表達出來。正如在知識產權制度中,如果抽象物的創造者希望獲得知識產權保護,則需要將抽象物具體化、有體化,例如在專利制度中的專利說明書,或者在商標制度中的商標圖樣。其二,通過控制抽象物的有體形式展示出財產權的意義。德霍斯認為,抽象物被包含在有體物之中,知識產權人正當地獲得抽象物的財產權后,就能夠獲取無限多種類和數量的有體物,例如專利權人對專利技術下的機器設備等進行的壟斷。
2.抽象物是知識產權的客體并應當被賦予私有權利
當抽象物中的財產權利被法律認可后,就會對社會中的財產秩序發生重大影響,因此需要對抽象物引發的財產關系做出合理安排。在許多有形資產的背后,均有著抽象物的支持。美國的經濟學家、社會學家魏步倫認為,現代工業企業的主要資本已經從有體物形式轉變為無形物,企業在市場競爭中獲勝的核心要素是對無形物的壟斷,例如消費者可以通過商標來識別商品,為企業贏得聲譽獲取競爭優勢。
3.抽象物與知識產權制度的設立密切相關
知識產權是對抽象物上個人財產權的壟斷,在社會中構建了一種“人身依賴關系”,如果放任個人對知識產品進行利益追逐,不僅會限制公眾的個人自由,久而久之釀成個人權利濫用的危險,更為重要的是,知識產品的獨占性使得知識產權人能夠通過一個抽象物控制不特定多數的具體物或者壟斷更多相關抽象物,這樣一來,其他的社會成員必然在知識產權人的許可下進行活動,這必將打破公共的分配正義,引發社會沖突。
德霍斯提出的知識產權工具論從反向證成了知識產權的私權屬性,同時也說明了對知識產權私權屬性進行限制的必要性。
三、結語
知識產權屬于私權是無可懷疑的。無論公權力的干涉程度如何,都不應認為其屬于公權力范圍或者公權與私權交叉部門。只有確認知識產權的私權屬性,才能激勵創造者更加積極地為社會貢獻聰明才智,促進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的推陳出新、繁盛豐富。
參考文獻
[1]【澳】彼得·德霍斯:《知識財產法哲學》,周林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版,第134頁。
作者簡介:朱愛斌(1981.3-),男,漢族,籍貫:北京市,西北政法大學民商法學院,2018級在讀研究生,專業:民商法學,研究方向:商法
(西北政法大學雁塔校區?陜西?西安?71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