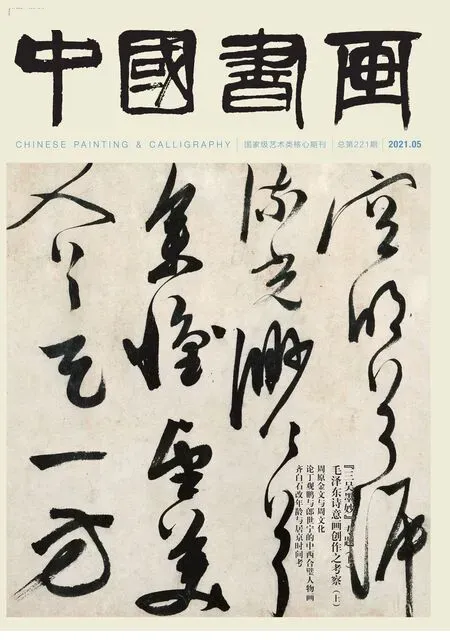三秦文化博大精深 青銅碑刻流連忘返
——陜西訪碑游學記
◇ 倪文東
陜西又稱“三秦”,地處中華腹地,黃河中游,自然條件優越,土地肥沃,物產豐饒,人杰地靈,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中國歷史文化的搖籃。早在遠古時期,我們的祖先就在陜西這塊黃土地上繁衍生息,開創華夏文化,為中國和世界創造了豐富燦爛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藍田猿人的化石,半坡先民的彩陶,軒轅黃帝的人文創造,神農炎帝的農耕稼穡,西周的青銅器和甲骨文,秦始皇的兵馬俑,漢唐的絲綢之路,法門寺的地宮寶藏,西安碑林的石刻墓志,大雁塔的鐘鼓聲,咸陽塬上的帝王陵,耀州窯的遺址,藥王孫思邈的藥池,“史圣”司馬遷之祠,漢中石門摩崖,昭陵的六駿,乾陵的石刻,榆林紅石峽的榜書,延安窯洞的燈光……所有這一切,都充分顯示了陜西豐富燦爛的歷史文化遺跡,反映了陜西作為中華文明發祥地的重要歷史地位和文化影響。所有這些,不僅在我國歷史文化發展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且在世界歷史文化發展史上也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
“秦中自古帝王州”,古代在陜建都的王朝達12個之多,在陜建都的王朝先后有西周、秦、西漢、新莽、西晉、前趙、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12個,歷時1200多年,譜寫了一部浩如煙海的中國歷史文化典籍。其中的周、秦、漢、唐時期,國富民強,經濟發達,文化藝術繁榮。當時國力強盛,疆土廣闊,中外文化交流十分活躍,歷史文化的發展成為當時中國甚至世界的最高水平。陜西又處于“絲綢之路”的起點和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勝地,它不僅吸收了西歐、西亞、中亞、南亞以及東亞文化中的重要和優秀部分,并且逐步融合這些文化并形成自己的特點,雄渾博大,樸厚雅逸,成為世界歷史文化的優秀組成部分。由于特定的歷史原因和文化環境,陜西的文化文物遺跡十分豐富,如刻符甲骨、青銅盤銘、秦石漢碑、銅鏡權量、秦磚漢瓦、碑石墓志、摩崖壁畫等等。這些不僅是古代勞動人民的偉大創造和智慧結晶,也是人類文化進步史上的珍貴遺產。

昭陵博物館及高大雄偉的唐碑

西安碑林《石臺孝經》
三秦大地,文物薈萃,名碑成林,書法遺跡留存十分豐富。陜西地區的書法遺跡是陜西歷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最優秀、最精華的部分,是陜西古代文化藝術的典型代表。打開陜西書法史的長卷,讓你驚奇,讓你陶醉,讓你自豪,讓你激動,讓你情不自禁,讓你流連忘返。周鼎秦石,漢碑唐刻,魏碑造像,磚瓦陶璽,塞上摩崖,舉不勝舉。中國古代歷史發展最輝煌的周、秦、漢、唐時期,就發生在陜西這塊黃土地上,留存了大量的歷史文化和書法遺跡。在中國書法史上,唐以前輝煌的歷史,也完成在陜西。所以,一部陜西書法史,包含和容納了中國書法史的精華,像一部微縮的中國書法史。當你穿梭在名碑林立的西安碑林,當你撫摸著漢中的石門摩崖,當你仰望昭陵高大雄偉的唐碑,當你贊嘆藥王山北魏造像記的率真野逸,當你盡情觀賞周原青銅的銘文,當你面對紅石峽摩崖榜書時,追蹤前賢腳步,“洗滌摩崖上,徘徊造像間”,訪碑游學,鑒賞金石,你會感覺到這些才是中國書法的源頭所在,根基所植,傳統所在,源遠而流長,博大而精深。
訪碑實踐由來已久,早在唐代,大書法家歐陽詢就曾經訪碑駐足三日,流連忘返;清代及民國時期金石學興盛,學者極其重視對碑石摩崖墓志的實地考察,如清代孫星衍寫過《寰宇訪碑記》,趙之謙又有《補寰宇訪碑錄》,近現代畢沅、于右任、康有為更是研究留戀于碑版間。這樣的實地考察不同于埋頭于故紙堆中,考察過程中所見之物會給人一種持久的深刻印象,正所謂“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現代人學習和研究書法更應該如此。
古代書法家通過訪碑游學,得自然感悟,啟發自己的想象和聯想能力,從而有了創作靈感的例子很多:蔡邕入嵩山學書得筆法,王羲之觀鵝掌撥水的姿勢取意為書,張旭觀公孫大娘舞劍而受啟迪,懷素見夏云多奇峰悟到了書法的氣勢,黃庭堅在嘉陵江上見船夫蕩槳而悟筆勢,文與可看見蛇斗而草書長,雷簡夫聽見江水漲潮而書興大發等等,不勝枚舉。古代書法家訪碑游學,鄧石如頗為突出,可以說他的大半生都是在訪碑游學中度過的。21歲那年,鄧石如就開始負笈遠行,訪碑游學,江蘇、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貴州、河北、山東等地的名山大川都留下了他的足跡。他先從家鄉安徽懷寧到九華山,聽說黃山上有碑碣,來不及仔細觀摩和游覽九華山的風光,便折向東南,直奔黃山。鄧石如飽覽了黃山的美麗風光和奇松怪石,但卻沒有找到一塊碑石。于是,他又南下九江,徒步上了廬山。在廬山的七八天里,他觀賞了云海松濤和一些摩崖石刻,使他的眼界大開。山東是孔孟之鄉,又有大量的秦漢和北朝刻石,所以鄧石如又去了山東的曲阜、鄒縣和泰安,在那里他如饑似渴地觀摩和考察秦漢的篆隸碑石和北朝的摩崖刻經,如癡如醉,心追手摹,獲益良多。到了62歲那年,鄧石如還來到泰山觀碑,在碑前流連忘返。通過對古代遺留下來的名碑摩崖的觀摩和考察,鄧石如的眼界大開,心胸豁然,拓展了思維,展開了想象,這才有了后來的脫化和創造,成為清代著名的碑學大家。
關于書法創作中的自然感悟,唐代篆書家李陽冰總結得比較全面,他說:“學書之得力,不徒在書也。于山川天地,可以得方圓流峙之形;日月星辰,可以得昭回經緯之變;云霞草木,可以得卷舒秀茁之態;衣冠文物,可以得周旋揖讓之容;眉目口耳,可以得喜怒哀樂之情;蟲魚禽獸,可以得屈伸飛動之趣;骨角齒牙,可以得安排分合之方;雷電風濤,可以得驚馳洶涌之勢。”我們說,世間萬物皆可寓之于書,用來啟發我們的想象和聯想,這和中國文字創造之初的“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的依據和原則是完全一致的。
近年來,我國高等書法教育蓬勃興起,書法學專業目錄明確了,形成了系統的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生培養體系。專業的書法教育,要求學生必須深入實際,調查研究,訪碑游學。古代遺存下來的碑碣墓志不僅是中國歷史的重要文獻來源,也是悠久的中國文化藝術的象征。碑碣墓志上漫漶的金石趣味,吸引著古往今來的金石學家、書法家們,他們撫碑瞻仰,浮想聯翩,暢懷幽情。追本溯源、回歸經典成為當今主流書法學術活動的基本認知模式。研究歷史、尋訪古跡不僅是學術的探索,而且是追古懷舊的精神需求。學術上的追本溯源、金石學的復興、訪碑活動的活躍,皆促進了當代審美品位的變化,也是提高書法創作水平的重要方式。我們的訪碑游學書法采風活動,正是本著正本清源、探索真相的一次文化之旅,也是一場穿越時空、對話古人的藝術之旅。
書法創作不是孤立的書齋活動和藝術行為,他是和書法家所生存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有關聯的。書法家不能整天把自己關在書房里或工作室閉門造車,長此以往,就會限制和扼殺藝術家的想象和聯想能力,是很難產生藝術精品的。所以,書法家要經常外出采風,和大自然親近,從大自然中獲得豐富的創作原動力,獲得豐富的想象和聯想啟示。有人不提倡書法家外出采風,認為采風和寫生那是畫家的事情,書法家就應該在書齋里臨帖和創作。對此,我有不同意見。為什么畫家可以外出到名山大川去體驗生活,寫生畫畫,而書法家就不能外出采風和訪碑呢?我非常欣賞已故西北大學教授楊春霖先生的觀點,他不但提倡書法家外出采風考察,而且還給這一藝術考察活動命名為“訪碑游學”。所謂“訪碑游學”,就是經常去全國各地的碑林、博物館和名山大川去考察古代的碑刻、摩崖、造像記、墓志及新出土的磚瓦陶文和簡牘帛書等,直接去面對和觸摸書法家心中的“真佛”。這種真切的感受,是我們無論如何在書齋里都無法獲得的。因為,我們平常所臨摹的碑帖大都是印刷品,都是經過剪貼裝裱、印刷加工過的紙本,它和原刻石有很大的不同。通過原刻石,碑的材質、形狀,所鑿刻的文字的大小、字口的深淺,石質的殘破、剝蝕等,我們一目了然。這時,我們才好像找到了與古代書法家對話的環境、平臺和機緣。所以,每次我外出訪碑,觸摸著千百年來留存的古碑,激動不已,感慨萬千。

昭陵碑林藏王知敬《李靖碑》拓片局部

《石門銘》拓片局部

藥王山《吳洪彪造像記》原石照片
2019年1月5日至11日,我帶領三位訪問學者王偉(遼寧盤錦市文聯副主席、書法家協會主席)、郭名峰(海南師范大學書法專業副教授)、王棟(臨沂大學書法專業講師)和三位在讀研究生王淵、張培艷、薛婷一行7人組成金石書法遺跡考察隊,前往陜西省境內全面、系統參觀考察金石書法遺跡。
7天時間,我們先后參觀考察了陜西歷史博物館、大雁塔及褚遂良《雁塔圣教序碑》、寶雞中國青銅器博物院、漢中石門遺址、漢中博物館、西安碑林博物館、昭陵博物館及碑林、耀州區藥王山碑林、蒲城縣博物館及《云麾將軍李思訓碑》等。除了路途遙遠、路況不好,我們沒有去長武縣考察《唐昭仁寺碑》、麟游縣九成宮遺址考察歐陽詢的《九成宮醴泉銘》和李治的《萬年宮碑》及白水縣倉頡廟、榆林紅石峽摩崖石刻外,保存在陜西省地區的金石書法遺跡,我們幾乎都參觀考察到了。這樣連續、集中、系統地參觀、考察、錄視頻、拍照片,對我來說也是第一次。我出生在陜西,在西安學習工作有26年之久,西安碑林、大雁塔、陜西歷史博物館等經常帶學生去考察,但去漢中、寶雞、榆林、蒲城就不是那么方便。特別是漢中,每次到西安帶學生進行專業考察,大家都希望去漢中開課石門遺址和漢中博物館,但那個時候從西安到漢中坐普通火車需要十幾個小時,時間根本來不及。但現在情況就不同了,現在從西安到成都的高鐵通車了,從西安到漢中只需要1個多小時,抓緊時間一天可以打個來回。我們真是要感謝高鐵時代了!

漢中石門遺址
我們每到一處書法文物的珍藏之地,就預約采訪當地的文物考古及書法研究專家,如在西安碑林博物館,我們就專題采訪了原西安碑林博物館館長、著名金石書法研究專家趙力光先生。寒冷的冬天,先生站在《石臺孝經》前面,一口氣講了將近一個小時,讓我和我的學生們十分感動。在漢中博物館,漢中博物館原館長,現陜西理工大學漢水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馮歲平先生,從漢中古代交通的歷史沿革、石門棧道的歷史淵源、石門漢魏十三品摩崖刻石的歷史文化和書法特征,以及漢中的文化文物等幾個方面給我們做了詳細的介紹和分析。經過7天的系列參觀考察,大家大開眼界,收獲很大,了解到許多在書本里和課堂上學不到的知識。
為期一周的陜西金石書法遺跡考察雖然結束了,但我們的工作才剛剛開始。師生們要分頭撰寫考察小記和調研報告,整理視頻資料、分類圖片資料。大家每每看到許多珍貴的國家一級文物的石刻摩崖,沒有受到應該有的重點保護:像蒲城縣博物館年久失修,房屋破落,著名的隋代名碑《蘇孝慈墓志》還裸露在破落的屋檐下面;像西安碑林博物館,是碑石成林,但所陳列的碑石過于密集,一方面不利于石刻文物的保護,另一方面也不方便觀眾參觀。后來趙力光館長說,陜西省人民政府不僅決定新建陜西歷史博物館,比現在的陜西歷史博物館大出三倍,而且決定礦建西安碑林博物館,并將延續“西安碑林博物館”的名稱,因為它是西安的文化符號,是世界上唯一以“碑林”命名的專題博物館。聽到這些消息,我們真是太高興了。因為現在每天參觀陜西歷史博物館的觀眾人山人海,許多珍貴的文物根本來不及仔細考察和觀賞。而目前西安碑林館藏有4000余通碑石,只展出了不到四分之一。希望五年以后,一座最新擴建的西安碑林博物館會矗立在現在的西安市三學街舊址,到時會展出更多的珍貴書法石刻,供全世界愛好文化文物和漢字書法的人們學習觀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