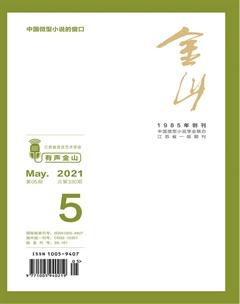“跑鮮”,真正的好文章是汪曾祺的



我不是文學圈內人,連縣市的作協會員都不是,因為我幾十年都沒有作品,哪怕是在縣市級刊物,他們(文學圈)不帶我玩。偶然一次機會認識了某雜志主編,在他的朋友圈里,我認識了相裕亭、認識了楊海林,可惜,他們也不認識我。
我沒有看過相裕亭先生的《鹽河舊事》,不知某雜志主編以后是否會送我一本。《跑鮮》,我也是從他的朋友圈里看到的。但是,論寫“跑鮮”,真正的好文章是汪曾祺的,他才是一代高手和祖師爺。
汪曾祺小說《鑒賞家》中的男主──葉三也是一個“跑鮮”專業戶,他也和《跑鮮》里的汪福一樣,賣果子的方式,不是開鋪子,不是擺攤,也不是挑著擔子走街串巷,他專給大宅門送果子。我并非有意說相裕亭模仿了汪曾祺,大概是因為汪曾祺老先生是蘇北高郵人,舊時的“兩淮鹽場”也應該在江蘇鹽城、淮安、連云港一帶。同是蘇北地區,也許鄉風民俗相同,因此,相裕亭的《跑鮮》與汪曾祺的《鑒賞家》,有很多“撞車”之處。
比如:汪曾祺《鑒賞家》中的葉三挎著一個金絲篾籃,籃子上插一把小秤,去送果子,這些人家他走得很熟,看門的和狗都認識他;與主人見面的方式,也是他(葉三)走進堂屋,揚聲稱呼主人。主人有時走出來跟他見見面,有時就隔著房門說話。“給您稱——?”“五斤。”稱好放在八仙桌上,道一聲“得罪”,就走了。至于葉三的果子,第一是得四時之先。市上還沒有見這種果子,他的籃子里已經有了。第二是都很大,都均勻,很香,很甜,很好看。他的果子全都從他手里過過,有疤的、有蟲眼的、擠筐、破皮、變色、過小的全都剔下來。第三,不少深居簡出的人,看到葉三送來的果子,才想起現在是什么節令。
相裕亭《跑鮮》中的汪福,也在紫荊籃邊插一把烏桿油亮的小盤秤,去給豪門大戶送果子。他也是“看門的都認識他,院子里的狗見到他,都直搖尾巴。”汪福與主人的交易方式,也是“直奔后院老爺、太太的窗下,喊一聲:‘剛下枝的麥黃杏?或‘頂花帶刺的脆黃瓜?窗子里的主人,有時掀開簾子張一眼,有時看都不看,隔著簾子,說:“‘來五斤,或‘都放下吧!”汪福的果子,也是第一,“什么時節,哪家太太、小姐喜愛吃什么,不愛吃什么,他熟記在心中,搶在四時之先。”第二,“那汪福送來的瓜果,個大,好看,沒有疤痕,沒有蟲眼,破皮的、擠筐的、變色的,他一概不往大宅門里送。”第三,“鹽區不少深居簡出的太太、姨太們,全是看到汪福送來的新鮮瓜果,才想起現在外面是什么季節的。”
再往下看,《跑鮮》就比《鑒賞家》略遜色了些。但凡文章,都有個文章眼,特別是微短小說。汪曾祺的《鑒賞家》旨在講述兩個身份迥異的人,畫家和果販一段“高山流水遇知音”的生死情義。汪老先生將這個“文章眼”演繹得一浪翻過一浪,高潮迭起,從畫家季匋民為小販葉三題詩:“紅花蓮子白花藕,果販葉三是我師。慚愧畫家少見識,為君破例著胭脂。”到日本人辻聽濤要買葉三收藏的季匋民的畫,要多少錢都行,葉三卻說:“不賣。” 一直到葉三死了,他的兒子遵照父親的遺囑,把季匋民的畫和父親一起裝在棺材里埋了。讓人讀來蕩氣回腸,為這人間“真善美”而感動不已。
《跑鮮》的文章眼則是,大鹽商吳老爺終于發現,那“跑鮮”的汪福并不是什么窮人,他裝扮成跑鮮的菜農,是為了混入鹽區的大宅門,感化、誘騙大鹽商,以求發財之道。其實,“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汪福只不過代表了其中的一種生存狀態,并不算什么卑劣之徒。在中國的古代和近代社會,跑大宅門是一種職業,一種小生意,我們熟悉的《水滸傳》里賣梨的鄆哥,就是這種角色,鄆哥假裝找西門慶賣梨,去幫武大郎捉奸;還有一種,就是賣珠花頭飾的婆子,她們也跑大宅門,除了向太太、小姐們兜售珠寶,還兼做馬泊六,說媒拉皮條,以期博取一些賞金。這些人一般都處于社會底層,單靠賣幾個水果得些賞金,竟能做成潑天大富,似乎有點缺少合理性,那大戶人家也應當有大戶人家的規矩,無論是賞賜還是待人接物。因此,我很想善意地與相裕亭先生商榷,您的《跑鮮》很容易給讀者造成這樣一個印象──前面“借”汪曾祺老先生的《鑒賞家》,后面您自己給按了個尾。
最近,網絡上很多關于“抄襲”“模仿”的話題,特別是青海省美協副主席王筱麗抄襲天津老畫家馬寒松事件持續發酵。固然,抄襲甚可惡,但是,我們也不要過分“談虎色變”,其實,名家也“模仿”。
──去年夏天,我突然心血來潮,想起要學畫畫,于是,手機里翻了很多名家的畫來看,其中,我最喜歡傅心畬,特別是他的荷花,清新脫俗,有一種令人震撼的韻味。當然,我也依樣畫葫蘆地臨了幾張,雖然筆墨、氣韻遠遠不夠,但自己覺得有三分形似,便有點沾沾自喜,放在手機里,偶爾給相近的朋友“show”(秀)一下。沒多久,我又看到一張畫,是冰心畫的。因為是我臨過的,一眼便看出冰心是臨的傅心畬,可我卻沒有冰心老太太厲害,敢裱了送人。但是,馬上我又釋然了:冰心的成就在于文學,并不在于畫畫,在丹青名家面前,她也是個學習者。如果她看到一張她喜歡的畫,臨了送給她相近的朋友,愿打愿挨也是他們兩個人之間的私事,有何不可呢?
又比如一些縣市級作協,麾下有一批文學愛好者。作協的宗旨主要在培養文學新人,繁榮本地文學創作。可是現在有多少期刊雜志能夠維持生存,更不用說有后輩青年練手的一席之地。因此,有的縣市作協幾個“文青”湊在一起,申請個公眾號,或者有企業家贊助時,出一本期刊,發幾篇習作,或擬個欄目,幾個志同道合之友,各寫篇文章湊個趣。說白了,這也就是文學愛好者的一個學習園地,即使有人“模仿”,又有何妨?
現在還有一批“老文青”,大多是一些退了休的老頭老太太,年輕時工作忙忙碌碌,現在老了閑了,便重拾一些舊時的愛好。我有一老朋友,經常在微信里發他寫的文章給我看,我看到他一些佳句,甚至段落,都是抄來的,不禁罵他:“人家千錘百煉才得一句,怎么寫到你文章里,就變成你的了?你看到人家老婆漂亮,也搶來算你老婆?”該老兄卻不以為然。最近,他告訴我想出書,我卻也支持──這么大年紀了,自掏腰包印幾本書,找個“樂子”哄自己玩玩,有什么不可以?這種書,賣不了錢,送朋友,有人還嫌書柜里占地方,因此管他抄的也好,模仿的也好,自個兒開心就好!
但是,對于成熟作者,特別是知名作家,我卻主張要管好您自己。你們的大作,不僅關乎替你們發表作品的平臺的權威性,還關乎著你們自己的個人品德和聲譽。如果你們也“模仿”或者“抄襲”別人的作品去換“名”換“錢”,不僅您的同行和讀者瞧不起您,連我也瞧不上您!文壇之上,如果我“模仿”了別人的作品,第三方又來“模仿”了我,那也簡直成了笑話!同時,我也希望,某些成熟作家、文學前輩們,在“嚴于律己”的同時,“寬以待人”,格局、氣度該大一些的時候,就大一些吧!千萬不要您講個故事(除非您事先就申明,這是您小說的創作構思),別人就是偷了您的“故事核”。當年蒲松齡還端個板凳到路口去聽人家講故事,因此寫成了《聊齋》。當然,如果您堅持,您就住進“獨家村”,我們今后不聽您講故事就是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