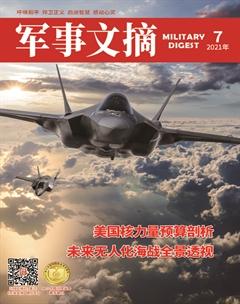未來混合戰爭形式解析
2021-07-19 09:38:55王湘穗
軍事文摘 2021年7期
關鍵詞:國家
王湘穗
戰爭隨時發生,尤其是局部地區發生戰爭的情況一直存在。我們所擔心的是大國之間的戰爭,更具體的講,是中美之間會不會發展到大規模熱戰。我認為這種可能性極低。按照馮·克勞塞維茨的觀點,戰爭是政治集中體現,是政治的繼續。同時戰爭也存在經濟利益的算計,需要計算收益成本。發動戰爭如果僅僅是為了互相毀滅,顯然不劃算。如果中美發生全面戰爭,兩個核國家直接導致雙方毀滅。從國家理性和國家利益的角度看,任何一方都不會選擇這種結果。這就基本框定了中美沖突的范圍。大國之間很難發生全面的大戰,但局部的軍事沖突是可能存在的。雙方能夠較快實現危機風險管控,不會影響到整個經濟大格局。
二戰時期的戰爭,更多的是大兵團作戰,職業軍隊之間相互廝殺,體現兩個國家之間的對抗。近年來的戰爭都有一個明顯特點:高科技+局部戰爭。軍事往往是作為一種撬動資本流,進而贏得國家利益的杠桿,而不是作為一個整體毀滅性的工具來使用。
從現在的軍事技術角度來說,戰爭擁有的破壞力、殺傷力遠遠超過了需求,和以前殺傷力不足是不一樣的,這也制約了各國對于戰爭工具的應用。
在我看來,以后的戰爭包括正在發生的戰爭往往都是一些帶有“潰瘍面性”的戰爭。在關鍵節點上,用軍事杠桿進行破壞,不造成致命打擊,但有一定制約作用。比如白俄羅斯事件、烏克蘭事件,都有類似的特點。軍事作為手段之一,綜合金融、科技、經濟等手段共同發力。未來的戰爭極有可能是混合戰爭模式,涉及到不同的領域,軍事力度未必很強,但可以收到較好的經濟收益。混合戰爭模式下也會出現“殺傷”,但并不以“殺傷”為目的。而是希望通過擾亂行為改變對手國家正常的經濟運行。所以我認為現在需要重點關注的是金融領域制裁導致的類似于戰爭級別的破壞。
猜你喜歡
環球時報(2022-12-14)2022-12-14 16:46:27
加油站服務指南(2021年8期)2021-11-04 08:19:06
學生天地(2020年22期)2020-06-09 03:07:52
青春期健康(2019年23期)2019-12-19 08:45:06
當代水產(2019年4期)2019-05-16 03:04:56
小天使·一年級語數英綜合(2018年6期)2018-06-22 10:25:54
華人時刊(2017年23期)2017-04-18 11:56:38
中國現當代社會文化訪談錄(2016年0期)2016-09-26 08:46:12
小學閱讀指南·低年級版(2016年1期)2016-09-10 07:22:44
上海國資(2015年8期)2015-12-23 01:47: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