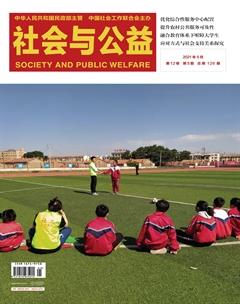“視頻慈善”的倫理風險與引導策略
項寅浩
摘 要:近年來,短視頻領域成為互聯網行業的新風口,一些從業者通過拍攝并上傳幫助弱勢群體的視頻獲利,創建了“視頻慈善”模式。營利性目的與慈善性內容被緊密捆綁,使得這種模式的商業化傾向十分嚴重,導致“視頻慈善”出現收益正當性存疑、監管缺失、公信力下降等問題。針對這些問題可以通過實現專門化管理、核定分配比例、推動良性競爭的方式加以解決,從而逐步剝離營利性,發揚慈善性,實現對“視頻慈善”的合理引導和改造。
關鍵詞:短視頻;慈善;倫理風險
短視頻是繼微信公眾號后新媒體領域的又一流量入口,二者的傳播形式不同,但營利模式是類似的,即通過內容形成、鞏固和擴大粉絲群體,產生巨大的流量,最后依靠流量變現。但因視頻內容創作的技術壁壘不高,可模仿性強,想要打造出爆款視頻就需要創作者另辟蹊徑。“視頻慈善”就在這一過程中被開發成新的類型。這些視頻的內容大多是創作者看望貧困老人或殘障人士,贈送他們生活必需品或衣物,再搭配感人至深的背景音樂來吸引觀看者。在積攢足夠的流量之后,經由平臺分紅、付費廣告、電商運營、賬號轉讓等多種渠道迅速營利。當這種營利模式逐漸成熟,并吸引了大量模仿者后,倫理問題也逐漸顯現。
一、“視頻慈善”的性質
“視頻慈善”的快速走紅得益于較強的營利能力,而多渠道的流量變現模式以及極具傳播力與感染力的視頻內容是其營利的關鍵。游走于營利與慈善之間為“視頻慈善”帶來巨大收益的同時也令其陷入爭議。因此,梳理“視頻慈善”的營利模式及其性質,有助于我們認清隱藏其中的倫理風險。
(一)內容的慈善性
慈善性內容是“視頻慈善”的核心競爭力。流量變現是短視頻營利的普遍路徑,“視頻慈善”的營利模式并不具有特殊性。隨著短視頻領域從業者人數的增加,競爭逐漸激烈化,創作者需要提供優質的內容才能產生足夠的流量。要提高內容的質量首先要專注于某一領域,提升自己在這一領域的專業性,形成一定的模仿壁壘。其次,是要形成鮮明的個人風格。同質化越嚴重的視頻越不容易引起瀏覽者的關注,且無法形成牢固的粉絲群體。“視頻慈善”的內容不僅簡單而且同質化嚴重。與其他內容的視頻相比,“視頻慈善”幾乎沒有技術含量也沒有在本領域內形成差異化空間,但依然能夠獲得相當的流量,關鍵在于內容的慈善性。視頻中貧困老人的生活狀況引起了觀眾的同情,同時制作者為老人做飯、贈送生活用品等行為也滿足了人們樸素的正義感。此時,觀眾是以圍觀者的視角觀看視頻,難以意識到視頻背后的營利邏輯,而是將視頻內容單純地看作一種幫助弱勢群體的公益性行為,由此產生了關注和支持心理。
(二)行為的營利性
“視頻慈善”本質上是一種通過慈善性內容吸引流量的營利方式。2016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以下簡稱《慈善法》)規定“本法所稱慈善組織,是指依法成立、符合本法規定,以面向社會開展慈善活動為宗旨的非營利性組織”。根據《慈善法》的精神,非營利性組織是不以營利為目的的社會組織。首先,我們很難通過對“視頻慈善”營利額的考察來判斷創作者是否是以營利為目的,因為無法排除慈善商業化的可能性,即制作者通過商業化的方式為慈善事業籌集資金。但制作者不公開自己的住所及名稱、沒有形成系統的章程和財產管理制度等行為都不符合《慈善法》對慈善組織的認定條件。其次,即便是個人慈善行為,也存在公布收益的使用明細的必要,而“視頻慈善”的制作者并沒有公布相應的數據。由此,我們排除慈善商業化和個人慈善行為兩種可能,因此“視頻慈善”本質上是一種營利行為而不是慈善行為。
二、“視頻慈善”運行中的倫理風險
如前文所述,“視頻慈善”本質上是披著慈善外衣的營利途徑。慈善性與營利性緊密捆綁,同時又相互矛盾,產生了一系列倫理問題。在商業與慈善邊界模糊的情況下,寬松的監管環境與存疑的收益正當性交織,最終使得“視頻慈善”趨于脫離倫理的軌道。
(一)商業與慈善的邊界問題
商業和慈善之間既有交集,也有不可逾越的邊界。商業與慈善的關系大致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慈善組織引入商業模式。20世紀60年代興起了一種戰略慈善,慈善組織引入了企業經營管理模式,通過商業模式管理慈善資金,極大提高了慈善組織的運營效率[1]。20世紀90年代,金融產業不斷成熟后,一些基金會和慈善組織實現合作,以拓寬慈善組織的資金渠道。這種模式的合理性在于以慈善為主,為慈善所用,并不以營利為目的。另一種是商業組織承擔社會責任。商業組織參與慈善事業能夠樹立正面的公眾形象,間接實現營利目標。企業參與慈善事業的動機之一是實現企業利潤,將慈善作為擴大企業影響力的手段,而并不是直接通過慈善本身來營利。但“視頻慈善”既不是慈善商業化的產物也不是企業發展的戰略,而是將孝老愛親這種本該具有公益性的行為作為利潤的直接來源,徹底模糊了慈善與商業的邊界,以利他主義為核心的慈善精神被追求超額利潤擴大化的營利目的所取代,必然產生正當性問題。
(二)視頻收益的正當性問題
貧困老人或殘障人士的受惠程度決定“視頻慈善”收益的正當性。“視頻慈善”以幫助老人或殘障者的內容,將自己包裝成正能量團隊吸引流量并轉化為收益。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可以將制作者吸引流量的行為看作慈善機構籌措資金的行為,觀看視頻的觀眾給予視頻團隊可以轉化為現實收益的關注就像捐贈者向慈善組織捐款。慈善組織使用捐贈資金的正當性是依法將資金運用于慈善事業。同理,視頻團隊使用收益的正當性來源于運用收益使得老人或殘障人士獲益。《慈善法》對慈善組織的資金使用做出了規定:“慈善組織中具有公開募捐資格的基金會開展慈善活動的年度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總收入的百分之七十或者前三年收入平均數額的百分之七十。”但出現在視頻中的老人獲得的只是一些簡單的生活用品,扣除這一部分成本剩下的資金全部成為團隊收益,貧困老人在其中的獲益程度遠低于在慈善組織中的獲益程度。退一步講,視頻團隊本身并不是一個慈善組織,可以不受《慈善法》約束。但視頻團隊對資金的分配現狀也不符合羅爾斯提出的第二條正義原則中的差別原則:“在與正義的儲蓄原則一致的情況下,適合于最少的受惠者的最大利益。”[2]“視頻慈善”作為一種營利行為,貧困老人在分配過程中本就處于弱勢地位,是最小受惠者,但他們在分配中的占比極低,且沒有得到持續的援助,分配的結果并沒有保障他們的最大利益,這顯然不是一種正義的分配。此外,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學原理》中提出:“你的行動,要把你自己人身中的人性,和其他人身中的人性,在任何時候都同樣看作是目的,永遠不能只看作是手段。”[3]視頻中的受助者不僅無法得到正義的分配,還被視作吸引流量的噱頭,成為工具人,背離了康德的絕對命令理論。因此,“視頻慈善”的收益存在缺乏正當性的問題。
(三)視頻受眾的疏于監督問題
“視頻慈善”的營利模式具有迷惑性,決定了其觀眾難以產生較強的監督意愿。一方面,視頻團隊以較低的成本塑造了“干實事”的形象,獲得了受眾足夠的信任。視頻的慈善性內容,滿足了觀眾樸素的正義感,從而產生暈輪效應。觀眾在感動之余往往忽略了視頻背后的營利性,即使察覺到營利企圖的存在,也會為視頻團隊開脫,從“好人應該有好報”的樸素正義觀出發,認定其營利的正當性。另一方面,視頻團隊的營利本質是獲取流量,即觀眾通過捐贈流量的方式參與“視頻慈善”。魯籬在對水滴籌的研究中發現,“捐贈者在‘水滴籌進行捐款時,捐贈金額較小,小金額捐款的設置在強化引流的同時弱化了捐款者識別、獲取真實求助信息的意愿,從其主觀上更愿意直接相信平臺提供的信息”[4]。換句話說,捐贈成本越小,捐贈者的監督意愿越低。捐贈流量同捐贈貨幣與實物相比,并不是一種自身利益的讓渡,更難激起受眾對視頻團隊后期資金使用、持續救助等行為的監督意愿。
(四)捐贈者群體的逆向選擇問題
逆向選擇主要是由于市場交易主體之間占有的信息存在質和量上不同而產生的市場失靈現象[4]。在“視頻慈善”市場中,一方面,視頻團隊在收益分配方面始終處于信息優勢。在營利目的驅使下,收益分配大幅傾向于團隊內部人員。同時,處于信息劣勢的觀眾不但監督意愿不強,且無力介入監督,勢必放縱不正當收益行為。另一方面,當收益不正當問題日趨明顯時,觀眾難以出于樸素的正義感對團隊的分配行為進行合理化解釋,又無法通過掌握信息介入監督,就會對視頻團隊持質疑和不信任態度。視頻受眾群體作為慈善事業的潛在利益相關者,也會處于一種信息劣勢,即無法分辨哪些是依法履職的慈善團體,哪些是以慈善為噱頭的營利組織。因此,當人們對視頻團隊產生懷疑時也會損害其他合法慈善團隊的公信力,從而導致捐贈者群體的逆向選擇。
三、對“視頻慈善”的引導策略
“視頻慈善”雖然在運行過程中存在倫理風險,但它對弱勢群體的關注與援助仍具有慈善意義。一方面,“視頻慈善”借助新媒體增加了貧困老人、殘障人士等弱勢群體的曝光度,使得他們重回大眾關懷的視野,這是傳統慈善組織的影響力所不能及的。另一方面,為了吸引流量,視頻團隊傾向于尋找典型人物作為視頻的主要素材,這也符合慈善市場的捐助倫理。楊方方認為,慈善市場高效的資源配置就應該是符合慈善事業內在的“人道”倫理訴求的配置,即“優先救助需求最緊迫的人”,也就是“弱者優先”[5]。視頻團隊尋找典型人物的傾向其實也就是優先救助弱者的傾向。因此,對“視頻慈善”的治理應該側重于引導改造,而非強制性管控。
(一)建立視頻專區,實行專門管理
“視頻慈善”的性質要求視頻平臺進行專門管理。一方面,對“視頻慈善”的引導要不斷發揚其慈善性,著力改造其營利性。現在的短視頻更多的是娛樂性較強,通過增加更多的娛樂元素,討好觀眾,是在流量爭奪中獲勝的重要途徑[6]。但“視頻慈善”并不以娛樂為導向,若要將“視頻慈善”從泛娛樂化的短視頻市場中剝離出來,就必須建立視頻專區進行專門管理,提高其慈善性的辨識度。另一方面,在設立視頻專區后可對該類視頻設置專門的審核標準。當前,各平臺的審核標準并沒有涉及慈善相關內容,無法滿足對“視頻慈善”的審核需要。因此,在建立分區之后,平臺可設置專門的標準考核視頻制作者的資質并審核所傳視頻。首先,在資質考核方面可借鑒嗶哩嗶哩(bilibili,簡稱B站)的用戶審核模式。在B站的制度設計中,只有通過嚴格的考試才能參與評論、發送彈幕和上傳視頻,而視頻考試的內容是基本的網絡道德。同理,平臺可以將相關慈善原則與捐助倫理作為考核“視頻慈善”上傳者資質的依據;還可以將廣告時長、救助力度、救助對象出鏡率等指標作為視頻審核的依據,引導視頻團隊將救助弱者作為創作的重心,發揚其慈善性。
(二)確定分配規則,彰顯慈善倫理
如前文所述,“視頻慈善”收益的正當性取決于受助者的受惠程度,因此制定合理的分配規則是改變其營利性的必然要求。第一,平臺應將收益分為個人收入與慈善資金兩部分,并參考《慈善法》有關慈善財產使用的相關規定確定二者的合適比例,保障并增加慈善支出。第二,慈善資金與個人收入必須嚴格分離,避免資金混同。首先,平臺可以建立慈善專門賬戶,對資金進行托管,保障專款專用;其次建立賬目公開制度,由平臺定期公開賬戶的資金使用狀況,確保視頻受眾群體對資金使用的有效監督;再次建立退出機制,對沒有按照要求使用資金的,或賬目存在問題且定期內沒有有效整改的,禁止上傳視頻,加大監管與懲戒力度。
(三)引入專業機構,推動良性競爭
如前文所述,“視頻慈善”的道德風險根源于內容的慈善性與目的的營利性之間的矛盾,因此對其引導和改造的核心任務就是盡可能剝離營利性動機與慈善性業務。最佳的制度安排是邀請各慈善組織入駐視頻平臺,通過競爭方式進行改造。一方面,引入慈善組織,擴大其網絡影響力。各慈善組織在短視頻領域中的缺位為“視頻慈善”獲益提供了空間。慈善組織可借鑒“視頻慈善”的相關做法,將短視頻作為信息公開、活動宣發、在線籌款的載體,與“視頻慈善”展開流量競爭。與“視頻慈善”相比,慈善組織因其專業性和相對較高的社會公信力往往會獲得受眾更多的關注與信任,成為網絡慈善市場的主流,增加網絡慈善市場的供給。另一方面,專業機構的加入能在競爭過程中形成榜樣效應。因為專業慈善組織在競爭中具有優勢,所以“視頻慈善”保持競爭力就需要效仿慈善組織的相關制度與做法。雖然競爭并不能徹底消解“視頻慈善”的營利性,但在優化分配的前提下,平臺的激勵機制可以保障其不斷向專業的慈善機構靠攏,恪守慈善倫理,發揚慈善精神,創造社會價值。
參考文獻
[1]王海燕.公益慈善組織從事商業營利活動法治初論[J].理論月刊,2015(10):165-171.
[2]約翰·羅爾斯.正義論[M].何懷宏,何包鋼,廖申白,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302.
[3]伊曼努爾·康德.道德形而上學原理[M].苗力田,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48.
[4]魯籬,程瀚.網絡慈善眾籌平臺監管的困境與規制優化:以“水滴籌”為研究樣本[J].財經科學,2020(9):121-132.
[5]楊方方.慈善市場的信息不對稱與結構性失衡研究[J].社會保障評論,2017(3):96-115.
[6]加強網絡短視頻平臺管理和內容審核[J].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19(3):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