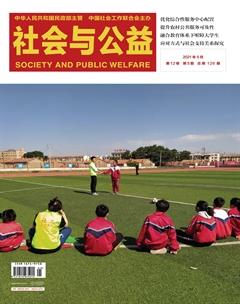“90后”志愿參與對其社會認同的影響研究
左嫣然
摘 要:本文就“90后”志愿參與對其社會認同的影響效應進行探討。基于社會認同理論和社會信任理論,文章提出相關假設,構建志愿參與、政府信任、社會認同和政府回應之間的關系模型,利用“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CSS)2017年的數據資料,運用SPSS 25.0_Process3.3進行實證研究。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在控制性別、政治面貌和受教育程度方面,“90后”志愿參與對其社會認同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作用;政府信任能夠在“90后”志愿參與與其社會認同的關系中起中介作用;政府信任在志愿參與和社會認同二者關系中的中介作用會受到政府回應的調節。研究結果不僅有利于從政府回應及政府信任的視角理解“90后”志愿參與與其社會認同間的關系,而且對鼓勵“90后”志愿參與、提升其社會認同、凝聚社會中堅力量具有啟示意義。
關鍵詞:政府信任;社會認同;政府回應;“90后”志愿參與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暴發以來,“90后”志愿者逐漸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群體,他們以不同的身份扮演不同的角色,出現在抗疫全線的各個角落,積極參與救治工作和志愿活動。不僅有大批的“90后”一線救護人員,而且有無數未統計在內的“90后”基層志愿者。習近平總書記在給北京大學援鄂醫療隊全體“90后”黨員的回信中提到,“廣大青年用行動證明,新時代的中國青年是好樣的,是堪當大任的!”“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領、有擔當,國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1]。
社會認同理論認為,滿意的群體認同是一個有凝聚力的社會制度的基本前提。而從功能主義來看,信任又是認同的基礎,組織的認同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之上。因此,志愿參與和社會信任、社會認同之間的關系也得到了學者的廣泛關注。張網成質疑普遍認同的“志愿參與性善論”這一前提假設,并通過實證研究,得出志愿參與對志愿者人際信任的影響不具有一致性,這種影響可正可負也可能是中性的結論[2]。志愿參與與社會認同的關系研究多集中于社會認同對志愿參與的影響研究,學者多主張高度的群體認同可以凝聚社會力量,社會群體對于國家認同層面的獨特而又正面的社會認同,促使群體成員產生志愿參與的心理和行為。
為進一步探究“90后”志愿參與對其社會認同的影響作用機制,本文以“90后”志愿參與為背景,以社會認同和社會信任理論為支撐,以“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CSS)2017年的數據為基礎,構建了“90后”志愿參與對其社會認同的影響作用模型,探討了政府信任的作用機理,比較了政府回應的影響差異,為提升“90后”社會認同提供理論支撐,并根據研究結論從優化政府作為、提升政府信任、強化政府回應角度,提出了有針對性的政策建議,以期為提升“90后”中堅一代的社會認同提供參考。
一、概念模型及研究假設
(一)志愿參與和社會認同的關系
“認同”理論源于心理學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心理防御機制,他認為這種心理防御是由人的生物本性決定的,從而忽視了社會關系和文化因素的重要作用。社會學依據認同建構的基本要素將認同分為兩類:第一類個體認同是個體基于自身獨特性建構的認同,第二類社會認同則是基于個體所傾向的群體成員資格來建構。通過社會分類和積極區分,社會認同同時具備群內相似性和群際差異性兩種屬性[3]。社會認同理論強調社會認同與個體認同之間的聯系,個體在提升其社會認同的過程中,不僅實現了社會身份的重構,而且通過維護所屬群體的榮譽和利益進一步提升了個體歸屬感,滿足了個體自我價值的實現。“90后”在志愿參與過程中將自我歸入“志愿者群體”,便接受與內化了志愿者群體的“正向特質”,在志愿參與中實現個人社會價值,滿足個體社會需求和尊重需求,從而產生群體認同感,表現出維護群體利益的行為。因此,可以假定志愿者在志愿參與中實現了社會認同的提升,提出如下待檢驗的假設:
H1:“90后”志愿參與對其社會認同產生顯著的正向直接影響。
(二)政府信任的中介作用
社會資本理論認為,公民參與中形成的參與網絡和互惠規范相互作用產生社會信任。其中,普遍互惠可以有效限制機會主義行為,將增加那些經歷重復互惠的人之間的信任水平;而由志愿性團體和公民組織構成的稠密社會交換網絡將增加博弈理論中關系的重復和聯系,從而提升社會信任水平[2]。學者依據信任對象特定與否將社會信任分為一般信任和特殊信任,一般信任的對象不特定,是對普通社會成員的信任,所以又被稱為“普遍信任”;而特殊信任的對象特定,也被稱為“人際信任”,其測量對象是與調查對象處于特定關系狀態的群體。在一個社會信任程度較高的社會中,以特殊信任為基礎向外拓展而形成的制度信任對社會認同具有促進作用,有助于提升公眾的社會認同感,促進社會參與和有效的政府治理[4]。因此,依據社會資本理論對社會信任與公民參與的關系認定,以及信任對認同的作用機制,提出如下待檢驗的假設:
H2:政府信任在“90后”志愿參與與其社會認同之間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三)政府回應的調節作用
政府服務及時有效性、回應公眾滿意度直接影響“90后”志愿參與的積極性,進而影響其對政府的信任水平和社會認同。政府對公眾訴求的回應在社會參與的過程中,當公眾的訴求得不到及時、有效的回應時,公眾對政府的信任感就隨之弱化;相反,當政府對公眾訴求和社會需求作出積極、有效的回應時,公眾的信任感會更高[3]。因此,政府回應是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有效途徑,政府對公眾訴求的及時回應,可以提升公眾社會參與積極性,使得公眾在社會參與中增強對政府的信任,從而提升政府形象和政府公信力,構建互惠的社會信任文化,進而提升公眾的社會認同。因此,提出如下待檢驗的假設:
H3:政府回應在“90后”志愿參與和政府信任之間起到調節作用。
H4:政府回應在“90后”政府信任與社會認同之間起到調節作用。
綜上所述,本文以提升“90后”社會認同為目標,研究“90后”志愿參與對其社會認同的影響。同時吸收先前學者的研究經驗,將政府信任作為中介變量,將政府回應作為調節變量加入模型。通過檢驗“90后”的志愿參與意愿和行為對其社會認同感的影響,分析政府信任和政府回應在其中的作用途徑與大小。
二、數據收集及變量測量
(一)數據資料
本文以中國社會科學院開展的“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CSS)2017年數據為實證研究基礎。該調查是雙年度的縱貫調查,調查區域覆蓋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的151個縣(市、區)、604個村(居委會),采用概率抽樣的入戶訪問調查方式,調查對象為18~69周歲的城鄉居民。調查問卷采用成熟量表,核心模塊涵蓋勞動就業、家庭及社會生活、社會態度等方面,該數據在目前我國國內關于社會問題的研究上具有權威地位,為本文的實證研究提供了翔實的數據支持。由于本文研究對象為“90后”志愿參與對其社會認同的影響研究,因此通過對樣本數據進行篩選,共提取1284份出生年份在1990—1999年的研究樣本,同時為保證研究結果的可靠性,進一步剔除相關的缺失樣本、無效樣本,最終有1198份有效樣本納入數據分析。
(二)變量測量
本文因變量為社會認同,提取國家認同(您在多大程度上同意“我經常為國家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的說法?)、社會規范認同(請用1—10分,來表達您對現在社會上人們普遍的道德水平的評價,1分表示非常不好,10分表示非常好;請用1—10分,來表達您對現在社會上人們的遵紀守法水平的評價,1分表示非常不好,10分表示非常好)和社會滿意度(請用1—10分,來表達您對現在社會的總體情況的評價,1分表示非常不好,10分表示非常好)三個方面的四個問題來反映。其中,關于國家認同的量表,將原始數據中“不好說”選項變更為“一般”,形成5級量表,并賦予1—5分的分值(得分越高則認同度越高),使之與社會規范認同和社會滿意度評分方向保持一致。解釋變量為志愿參與,本文中的志愿參與主體是“90后”群體,包含了自組織的志愿參與和他組織的志愿參與,兩類志愿參與又都包含了志愿參與行為和志愿參與意愿兩個維度,測量問題分別是“最近2年,您是否參加過自發組織的社會公益活動,比如義務獻血、義務清理環境,為老年人、殘疾人、病人提供義務幫助?如果沒有,是否愿意參與?”以及“最近2年,您是否參加政府、單位、學校組織的公益活動,如果沒有,是否愿意參與?”。控制變量為性別(男性=1,女性=2)、政治面貌(中共黨員=1;共青團員=2;民主黨派=3;群眾=4;其他=5)和受教育程度,其中,受教育程度調整為受教育程度與其平方項之和。中介變量為政府信任,包括人員信任(請問,您信任警察、法官、黨政干部人員嗎?)和機關信任(請問,您信任中央政府、省市政府、縣鄉政府、法院這些機構嗎?)。調節變量為政府回應,包含政府對民眾需求回應的及時性和高效性(您認為,政府在有服務意識,能及時回應百姓的訴求方面的工作做得好不好?),以及民眾對政府工作的評價(您認為,總的來說,地方政府的工作做得好不好?)兩個維度。
三、數據分析及效應檢驗
(一)各變量的平均數、標準差和相關矩陣
研究中的潛變量取值為觀測變量的平均值,進行平均值、標準差和相關系數檢驗。描述及相關分析結果表明:志愿參與和政府信任呈顯著正相關(t=0.076,P<0.01),與社會認同之間呈顯著正相關(t=0.089,P<0.01),與政府回應之間呈顯著負相關(t=-0.031,P<0.05);政府信任與社會認同之間呈顯著正相關(t=0.208,P<0.01),與政府回應之間呈顯著負相關(t=-0.445,P<0.01);政府回應與社會認同之間呈顯著負相關(t=-0.157,P<0.01)。
(二)中介效應分析
采用SPSS 25.0_Process3.3中的Mode4(Mode4為簡單的中介模型),在控制性別、政治面貌和受教育程度的情況下,對政府信任在志愿參與和社會認同之間關系中的中介效應進行檢驗,其中t表示相關性指數,P表示相關程度,P<0.05表示相關,P<0.01表示高度相關。結果表明,志愿參與對社會認同的預測作用顯著(t=2.894,P<0.01),且當放入中介變量后,志愿參與對社會認同的直接預測作用依然顯著(t=2.414,P<0.05),即假設H1得到驗證。志愿參與對政府信任的正向預測作用顯著(t=2.571,P<0.05),政府信任對社會認同的正向預測作用也顯著(t=7.167,P<0.01)。此外,志愿參與對社會認同影響的直接效應及政府信任的中介效應的bootstrap 95%置信區間的上限、下限均不包含0,表明志愿參與不僅能夠直接預測社會認同,而且能夠通過政府信任的中介作用預測社會認同,即假設H2得到驗證。該直接效應(0.192)和中介效應(0.042)分別占總效應(0.234)的81.96%、18.04%。
(三)有調節的中介效應分析
采用SPSS 25.0_Process3.3中的Mode58(Mode58假設中介模型的前后兩段路徑受到調節,與本研究的理論模型一致),在控制性別、政治面貌和受教育程度的情況下,對有調節的中介模型進行檢驗。結果表明,將政府回應放入模型后,志愿參與和政府回應的乘積項對政府信任的預測作用不顯著(回歸系數為0.083,t=2.40,P>0.05),說明政府回應在志愿參與對政府信任的直接預測中不起調節作用,即假設H3不能得到驗證。而政府信任與政府回應的乘積項對社會認同的預測作用顯著(回歸系數為0.099,t=3.4004,P<0.01),說明政府回應在政府信任對社會認同的直接預測中起調節作用,即假設H4得到驗證。
繪制調節效應分解圖,進一步進行簡單斜率分析表明,當政府回應度較低時,隨著“90后”政府信任度的提高,其社會認同表現出顯著的上升趨勢,而當政府回應度較高時,隨著“90后”政府信任度的提高,其社會認同仍然表現出顯著的上升趨勢,且相較于政府回應度較低時,增長幅度較大。表明隨著政府回應度的提高,“90后”政府信任對其社會認同的正向影響作用呈逐漸上升趨勢,即隨著政府回應度的提升,“90后”志愿參與更易通過增強其政府信任進而增強其社會認同。
由以上分析結果可知:“90后”志愿參與與其社會認同之間存在顯著的相關性。引入中介變量政府信任后,志愿參與和社會認同之間的關系減弱但仍然顯著,表明政府信任只能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此外,在政府信任中介作用基礎上引入調節變量政府回應,發現政府回應對于志愿參與影響政府信任的關系沒有起到調節作用,對于政府信任影響社會認同關系的正向調節作用顯著。
四、結果討論及實踐建議
研究可得以下結論:第一,“90后”志愿參與行為和志愿參與意愿對于增強其社會認同具有顯著的直接正向影響;第二,政府信任在“90后”志愿參與影響其社會認同的過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第三,在“90后”志愿參與通過政府信任影響其社會認同的作用過程中,政府回應通過影響政府信任的高低程度來實現對“90后”社會認同的調節。
本文揭示了“90后”志愿參與對其社會認同的影響機理,研究結論對政府提升“90后”群體社會認同具有政策啟示。研究結果證實了“90后”志愿參與對于提升其社會認同的重要意義,通過刺激“90后”進行志愿參與,并利用志愿參與來加強個體與社會之間的相互關系,有利于“90后”在心理和行為上產生向所處社會傾向的趨勢和為所在社會爭取利益和聲望的心理,從而提升其社會認同。這條路徑的開展對于政府提升“90后”志愿參與積極性提出了方式方法的要求,如何更廣范圍、更大力度刺激“90后”積極參與志愿服務成為解決該群體社會認同提升的重點問題。
同時,研究結果也證實了政府信任的中介作用和政府回應的調節作用,特別是政府信任在志愿參與影響社會認同路徑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政府回應僅在政府信任影響社會認同過程中起到正向調節作用。一方面,政府信任的中介作用肯定了政府信任在志愿參與和社會認同之間的橋梁作用,這就要求在利用志愿參與手段來提升“90后”社會認同感的過程中,政府機構和工作人員要就制度體系的健全和完善、政策執行中的規范和守法、志愿參與的支持與鼓勵等維度問題及時“補短板”和“強弱項”,以構建“90后”中堅力量對政府體系和政治制度的堅定信任;另一方面,政府信任雖然對社會認同具有正向影響,但其影響社會認同的程度受到政府回應度高低的影響。政府回應度高,政府信任度的提升,能夠更大程度上提升“90后”社會認同;反之,政府回應度低,政府信任正向帶動社會認同的影響效果便不明顯。因此,如何貼近民生,“俯下身去”做好調研,憂民之所憂,急民之所急,打造人民滿意的政府形象成為通過志愿參與實現“90后”社會認同感提升的重要方面。
因此,建議一方面通過政府積極作為促使“90后”積極參與志愿服務,另一方面通過完善政府體制機制來提升志愿者群體對政府的信任,同時深化服務型政府理念來達到強化政府回應力的效果,從而逐步提升“90后”群體的社會認同。
參考文獻
[1]央視網.習近平回信勉勵北京大學援鄂醫療隊全體“90后”黨員 讓青春在黨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綻放絢麗之花[EB/OL].(2020-03-16)[2021-02-14].http://m.news.cctv.com/2020/03/16/ ARTICfgtnfrmOEdnYzw8ouCr200316.shtml.
[2]張網成.大學生志愿服務及其對社會信任的作用[J].青年研究,2016(3):21-30.
[3]閆丁.社會認同理論及研究現狀[J].心理技術與應用,2016(9):549-560.
[4]甘開鵬,王秋.社會信任對政府環境治理績效的影響研究[J].中國行政管理,2020(3):153-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