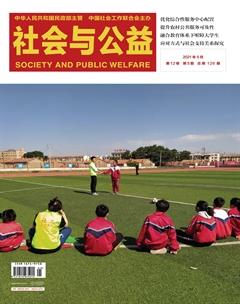基于敘事療法創新留守青少年教育幫扶工作
羅匡 張珊明
摘 要:本研究團隊在高校完成了對有留守經歷大學生的質性敘事訪談研究,訪談和觀察的結果證明敘事療法可以幫助有留守經歷的大學生更好地自我成長,提升內在力量。研究團隊利用高校服務平臺,在湖南省某縣城隨機抽取3名留守青少年進行以敘事訪談為主的教育幫扶工作,進一步探討敘事療法在留守青少年(學校、家庭和社區)教育幫扶工作中的創新意義與作用。
關鍵詞:留守青少年;敘事療法;教育幫扶
一、研究背景
自 2006 年來,關于留守話題的研究主要涉及我國社會升級發展中留守群體生活、機遇、問題及改變等方面 [1]。其中關于留守青少年群體以及問題的研究和討論不斷增加,大部分學者認為留守青少年在其成長過程中,因為父母缺位,隔代撫養,會產生教育問題,繼而出現生活問題、心理問題及道德行為問題,甚至厭學輟學,從而對社會和個體造成負面影響[2]。由此可見,“對留守兒童來說,最重要的就是教育問題”[3],解決留守兒童的教育問題,除了形成完善的社會支持系統外,是否還有其他創新之路?因此,對這一群體的教育幫扶工作的創新就有較為重要的作用與意義。
從20世紀90年代引進至我國教育教學與心理咨詢服務領域的敘事療法,其療效逐漸被證實,如貝格爾(Baerger)提出心理健康與連續生命故事有密切關系[4]。敘事治療對個體的精神或心理疾病有一定的療效[5]。團隊成員以質性的敘事訪談了解幾名留守大學生內在的自我世界,發現敘事療法能喚起留守大學生內在力量進行自我認知改善,并增強自信。在此基礎上,團隊成員提出了留守青少年教育幫扶創新途徑——通過高校平臺“三下鄉”、農村實踐、鄉村支教等活動對留守青少年開展敘事服務[1]。正如胡適先生所言:“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提出基于敘事訪談服務教育幫扶工作的創新,需要驗證其科學性和可行性。因此,本團隊借助高校教育平臺,深入湖南省岳陽市某縣城,尋找到3名不同生活、學習背景的留守青少年,在本人和家人的同意下對其進行質性敘事訪談,并對教育幫扶過程進行觀察。本研究團隊借助當地社區、學校和教師的幫助,進一步探索在敘事療法的基礎上如何創新留守青少年的教育幫扶工作。
二、研究方法與過程
研究采用的是敘事訪談法和觀察法,訪談對象包括三名留守青少年、青少年所在社區工作人員、所在學校教師及其家人等。經當事人允許可刊載部分文字。本研究采用麥克·懷特的敘事進行數據分析和成長干預。敘事療法重視“故事、順序、外化和重寫”[5],在故事的解構中,幫助留守青少年尋找生活、學習的意義和亮點。因為留守青少年年齡偏小,其自我表達能力和思考能力較低,加上對陌生人有防御心理,因此訪談中無法做到一對一訪談,基本上是邀請其親屬、班主任或者社區工作人員一同參與。
(一)班主任關愛引導在幫扶中的關鍵作用
留守小學生A,女,11歲,年幼時喪母(具體年月表述不詳),父親一直在外打工,和年邁的爺爺一起居住,性格內向靦腆,不愛和人說話。在班主任胡某的陪同下進行敘事訪談。A的敘事,大多都是一些學校的學習瑣事,A說自己的成績不怎么好,爺爺經常說初中要還是這個樣子就跟爸爸一起出去打工。說到“打工”,A覺得也很不錯,“那樣就和爸爸在一起,不用天天對著生悶氣的爺爺了,但就是看不到胡媽媽了”。咨詢師注意到了這一句話,可見在A的心目中,班主任胡某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在與班主任和A的訪談中,團隊發現該班主任對A做得最多的是無言的關注和愛護,如給A梳理辮子,或者A中午沒有帶飯時就讓A和自己一起吃飯。A回憶曾悄悄去班主任的辦公室喊了一聲“媽媽”,她從來沒有叫過任何人媽媽,但那一次A自己也不清楚為什么會這樣叫。
“當時她(A)的聲音很小,我聽到那聲媽媽也愣住了,還問‘你叫我什么?A很不好意思地跑開了,我突然意識到,那可能是她第一次喊媽媽。我覺得那一聲真的很好聽。之后我對A更加關注,我希望A能活潑一點,她其實很聰明,如果用心學習,是一個好苗子。”這是A的班主任在和A共同回憶到那件事情時的一段話。而A在敘事訪談中的轉折點就在她聽完班主任胡老師的這些話之后。A在成長過程中缺乏母愛,父親長期在外打工,爺爺也只是解決A的生活吃飯問題。在敘事訪談之前,A認為除了班主任,誰也不會主動關心她的成長,她無法言說的苦惱就是無人關注。遇到關心A的班主任,是A人生故事中的一次亮點。在訪談的后期,團隊主要臨時培訓班主任胡某,對她進行敘事治療的培訓,讓她成為A人生故事的引導者,幫助A重構自己才剛起步的人生。作為A小學生活的參與者,班主任與她一起重尋以前生活中的閃光故事。例如:A的父親曾為了參加A的班級家長會,千里迢迢地從打工地點回來;A曾經在班上突然發高燒,班長和學習委員一起攙扶A去醫務室,等等。A意識到,其實有很多人關心自己,自己并不是“多余的一個”。在后期,A的學習動力逐漸變強,期末考試進入班級前十,這是A從未經歷過的值得驕傲的事情。除此之外,A的人際關系得到很大的改善,她明顯比之前更加自信。
馬斯洛在人的需求層次理論中指出,人在滿足生存和安全需求后,就是愛與歸屬的需求。
A代表著留守兒童的一部分,他們生活條件不錯,渴望被愛但缺乏對愛的感知。因為留守兒童的思維能力還處于發展的狀態,難以去尋找問題的本質,需要其生命中較為關鍵的人來進行結構化的故事解構,而這個引導者必須有足夠的耐心和技能。有學者發現了班主任在做好留守兒童教育工作中的關鍵作用,提出建檔、引導、關愛和管理的工作步驟。然而,作為一名班主任,除了要嚴謹有序地做好以上幾個步驟外,還應適當接受敘事療法相關培訓,用內在的愛與耐心幫助留守兒童澄清個人生活史的形成軌跡,借助某些閃光事件幫助他們轉變生活態度[6]2。
(二)父母角色的適當回歸改寫故事方向
留守中學生C,男,14歲,父母長年在外打工,現在鄰近的城市做水果批發生意。C是家中獨子,由遠房阿姨專門照顧。C小學時成績很好,初中厭學叛逆,與父母基本不溝通。C主動尋求幫助,在訪談過程中,其父母也主動通過網絡連線一起進行敘事訪談。訪談早期,親子關系較為緊張,經常一言不合就中斷訪談;訪談后期,父母轉移手中生意,回到家鄉與C一起居住,可見舊事回憶和故事外化使他們有所改變。C的回憶里,開始都是小學努力學習的生活片段,因為父母的口頭禪就是窮人只能靠自己,所以C從小自卑且自負,不斷用成績來證明自己。初一某天,他去父母工作的水果店,無意中發現原來父母早就成為水果店的小老板,他頓時怒不可遏,感覺受到了巨大的欺騙,從此叛逆厭學。咨詢師要求C停留在那個事情上,引導C外化成第三人來看故事,C漸漸理解了父母苦心——在傳統的“窮養兒、富養女”的觀點浸潤下,C的父母因擔心C一個人在家會容易結交到壞朋友,所以刻意營造了一個貧窮的家庭環境,希望C能一直保持奮斗之心,卻沒有預想到青春期的少年對于謊言的憎惡以及可能產生的激烈反抗和防御行為。C在咨詢師的幫助下與當時憤怒的自己和解,同時也與父母和解。訪談中,C的父母通過C的回憶事件,才領悟到一直將C看成童年期的孩子,忽略了C已經長大的事情。C父母經過慎重考慮,結束了鄰市的生意回到C身邊,并用欣賞的眼光看待C的變化和他的學業,而C則開始積極對待學習的挑戰,正如他的原話:“爸爸媽媽為了我暫時放棄了他們的事業,那我要為了他們重拾我自己的學業。”
在與C的訪談中,咨詢師主要充當聆聽、疏導、引導C尋找特殊事件的角色,而父母則見證了孩子獨特的結果,鼓勵孩子去改寫自己生命里的故事。C很幸運,其父母有能力回歸家庭中的角色,也有能力思考、表達、引導和行動,但在中國現階段,以農民工為主體的打工父母中像C的父母類型的還是少數,畢竟新生代農民工是具有成年前留守流動,成年后外出務工、多次流動甚至終生流動等典型共性的群體,他們的生命軌跡中隱含著親情疏離的代際傳遞特性[7],而要破除這些異化的深層危機,以敘事療法為基礎的家庭幫扶教育工作有著重要的實踐意義。
(三)社區指導、幫助青少年重構人生理想
L,20歲,從16歲開始參加工作,4年時間已經換了快30次工作,平均兩個月換一次工作,從3歲時就和外婆生活,父母一直在外打工。初中畢業后輟學,無論是繼續教育還是工作培訓都無法堅持3個月。父母曾帶著他一起外出打工,但他嫌棄工作環境艱苦又回到家鄉,在家鄉的工作也因為自己的原因無法持久,當他被第30份工作辭退后,由所居住的社區推薦找到本團隊。L很胖,經常面帶微笑,但帶有防御心理,經常以“你覺得呢?”“不然呢?”等問句回避咨詢師的問題,在談到每一份工作時,他有種才華得不到施展的失落,并一再強調自己是有夢想的,應該創業而不是打工。與L回溯故事,才得知L的父親曾是個成功的商人,卻在L出生后破產,從此父母外出打工。L的母親經常在L面前抱怨父親沒用,而L的父親罵L是沒用的廢物。L很希望能一夜暴富,但卻在生活面前感到無力。咨詢師和L回到他初中輟學待在家里時父親責罵他的故事里,他看到了家中三個人相互指責的循環,L說:“如果這里面,有一個人不是指責而是支持,可能故事就是另外一個結局。”
與L的訪談遇到數次瓶頸,中間數次訪談中,L在發掘成長故事中的積極例外時,會產生內在力量重構故事,但當他走出訪談室,踏入真實的社會環境就業時,就會很輕易地被現實情境中具體的小問題阻礙,并產生莫名的無力感。L表示:
我前兩天在理發店找了學徒的工作,之前我已經在5個店當過5次學徒了,那些以前跟我一起共事的學徒現在都是理發店的什么首席發型師了,而我還是在當一個熟練的學徒。昨天老板在夸我上手快時,我就只笑了笑,他還不曉得,我其實是個廢柴(網絡稱呼:指沒有用的人),干活熱情不超過三天,我真沒用……
留守青少年經常會出現一種莫名的無力感,其來源于系統支持的缺乏:或源于家庭的壓力,或源于朋輩的比較,或源于標簽的固化[8]。要想匯集家庭親情陪伴、社會多元救濟與國家制度保護為強大合力[9],進而形成強大的支持系統,就要落腳于真實的場景。毋庸置疑,社區是其中要點之一。與L的敘事訪談較為曲折,L的職業能力、素養及未來規劃混沌而無序,重啟他對未來的激情,除了他對例外事件的不同認知和領悟,還需配備社區提供的硬件方面的支持,如提供與L匹配的職業規劃、相關培訓、就業指導,以及家庭溝通交流的指導等。而且,我們必須承認,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對于留守青少年的教育幫扶工作越早越有效,以社區為依托,發揮社群中社會工作者、公益社會組織等的力量,增強他們的社會工作能力和敘事訪談技能,讓他們參與留守青少年教育幫扶工作,不失為一種有效的途徑。
三、總結與討論
對于留守青少年的教育幫扶,需要高屋建瓴的政策建議和理論體系建設,也需要微觀細致的幫扶細節體驗和總結。在對留守青少年進行訪談和觀察時,他們不是文章里的某個群體或某種符號,也不是社會學理論當中假定的經濟人、社會人或者復雜人,而是一個個鮮活的人,有著不一樣的生活故事和情景體驗的人。對他們進行教育幫扶,就要真實地了解他們,真正地理解他們,真心地欣賞他們。研究團隊曾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出一種假設:高校搭建平臺,建立相對應的教育服務方案,開展幫扶計劃和實踐,邀請一批優秀的有留守經歷的大學生用自己比較勵志的故事,去改變一些和他們曾經命運相似的留守兒童自卑敏感的內心世界。經過此次研究后,團隊建議高校應根據學校學情,邀請心理學、社會學等專業的學生以及一批優秀的有留守經歷的大學生一起進行此項服務。同時,高校的相關教師可開發免費的線上教程,便于學校教師、社區工作人員及家長線上學習。當然,在高校的心理教育機構的設計中,需要貫穿終身學習理念,并在敘事咨詢技能培訓的基礎上增設以人生體驗為基礎的督導課程,因為敘事治療過程“崇尚一種生生不息、不斷發展的意境”[6]51-55,重構年輕人的人生故事充滿張力與迂回,咨詢師所需的不僅是技術,而且需要內在境界的提升。
參考文獻
[1]羅匡,張珊明,祝海波.留守經歷與大學生自我概念發展研究[J].江漢大學學報,2021(2):102-111.
[2]田杰,方瑞芬.“問題兒童”標簽下留守兒童研究述評[J].現代教育科學,2017(11):145-149.
[3]許傳新.“留守兒童”教育的社會支持因素分析[J].中國青年研究,2007(9):24-28.
[4]BAERGER D R,MCADAMS D P . Life Story Coherence and Its Relation to Psychological Well-Being[J].Narrative Inquiry,1999(1):69-96.
[5]ZINBARG R E,ULIASZEK A A.The Role of Personality in Psychotherapy for Anxiety and Depression[J].Journal of Personality,2009(6):1649-1688.
[6]WHITE M. Re-authoring live:Interviews and Essays[M]. Adelaide:Dulwich Centre Publications,1995.
[7]李明,楊廣學.敘事心理治療導論[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56.
[8]陳雯,流動的孩子們:新生代農民工生命歷程異化與代際傳遞研究[J].中國青年研究,2019(2):47-55.
[9]熊丙奇.關愛留守兒童不能把他們標簽化[N].中國青年報,2016-08-30(2).
[10]李浩燃.別讓“留守”固化為成長標簽[N].人民日報,2016-02-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