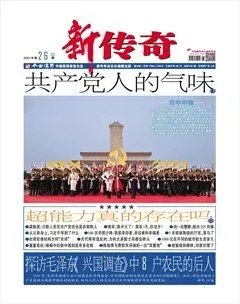陳潭秋之子:追憶父輩的家國(guó)情
初中畢業(yè)后,陳志遠(yuǎn)第一次見(jiàn)到了父親的照片。“我無(wú)法想象,這樣一個(gè)英俊帥氣的小伙子竟然有這樣堅(jiān)定的信仰,有這樣剛烈的氣節(jié)。”長(zhǎng)大后,陳志遠(yuǎn)慢慢理解了父親:“他顧大局,不計(jì)較個(gè)人得失,舍小家為大家,是心系國(guó)家存亡的共產(chǎn)黨員。”
在天津市南開(kāi)大學(xué)西南村的一處普通民居里,一名88歲的教授伏在案頭,翻開(kāi)一本文集,微微顫抖的手指在字里行間輕輕滑過(guò)。抬起頭,他陷入了沉思。
老人名叫陳志遠(yuǎn),是南開(kāi)大學(xué)的退休教授,也是中共一大代表陳潭秋的兒子。父親犧牲時(shí),他只有10歲,兩人從未謀面。一封收錄在《陳潭秋文集》里的《給三哥、六哥的信》,成為他與父親之間最特別的情感連接。
一封家書(shū),心系國(guó)之大者的選擇
“我始終是萍蹤浪跡、行止不定的人,今天不知明天在哪里,所以決心將兩個(gè)孩子送到外家撫養(yǎng)。兩個(gè)孩子都活潑可愛(ài),直妹(徐全直,陳潭秋之妻)本不舍離開(kāi)他們,但又沒(méi)有辦法……現(xiàn)在(她)又快要生產(chǎn)了。這次生產(chǎn)以后,我們也決定不養(yǎng),準(zhǔn)備送人,不知六嫂添過(guò)孩子沒(méi)有?如沒(méi)有的話,是不是能接回去養(yǎng)?”
這是一封“托孤”的家書(shū),寫(xiě)于1933年2月,寫(xiě)信的人便是陳潭秋。1933年初,組織決定讓陳潭秋、徐全直夫婦到中央蘇區(qū)工作。此時(shí),徐全直懷有身孕即將臨產(chǎn),不便轉(zhuǎn)移,陳潭秋只能先行前往。
1933年4月,陳志遠(yuǎn)在上海出生。此時(shí),陳潭秋已經(jīng)奔赴中央蘇區(qū)。陳志遠(yuǎn)出生兩個(gè)多月后,徐全直因被叛徒出賣(mài)被國(guó)民黨當(dāng)局抓捕入獄。次年2月,她在南京雨花臺(tái)犧牲,年僅31歲。
陳志遠(yuǎn)的六伯父和六伯母收養(yǎng)了他,對(duì)他視如己出。家人也在他懂事后,開(kāi)始向他講述其父母的故事。
1896年出生的陳潭秋是湖北黃岡人,青年時(shí)代參加五四運(yùn)動(dòng)。1920年秋,他和董必武等在武漢成立了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1921年7月,他出席了黨的一大。此后,陳潭秋為黨的事業(yè)四處奔波。
“我很小的時(shí)候就知道父母是共產(chǎn)黨,當(dāng)時(shí)我不理解父母選擇的事業(yè),但我覺(jué)得他們很了不起。”陳志遠(yuǎn)說(shuō)。從長(zhǎng)輩們的講述中,父母的形象漸漸豐滿起來(lái)。
1935年8月,陳潭秋赴莫斯科參加共產(chǎn)國(guó)際第七次代表大會(huì),之后又參加了中國(guó)共產(chǎn)黨駐共產(chǎn)國(guó)際代表團(tuán)的工作。回國(guó)后,他任中共中央駐新疆代表和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負(fù)責(zé)人。1942年9月17日,他被逮捕,在獄中堅(jiān)貞不屈。1943年9月27日,他被敵人殺害。
初中畢業(yè)后,陳志遠(yuǎn)第一次見(jiàn)到了父親的照片。看著照片中意氣風(fēng)發(fā)的父親,他覺(jué)得既熟悉又陌生。“我無(wú)法想象,這樣一個(gè)英俊帥氣的小伙子竟然有這樣堅(jiān)定的信仰,有這樣剛烈的氣節(jié)。后來(lái),我在父親的信中找到了答案。”
在《給三哥、六哥的信》中,陳譚秋寫(xiě)道:“生活當(dāng)然也很困苦,但這絕對(duì)不是一人一家的問(wèn)題,已經(jīng)成為最大多數(shù)人的問(wèn)題。”這番話讓陳志遠(yuǎn)思考了很久。
長(zhǎng)大后,陳志遠(yuǎn)慢慢理解了父親:“他顧大局,不計(jì)較個(gè)人得失,舍小家為大家,是心系國(guó)家存亡的共產(chǎn)黨員。”
一生追尋,感悟父親的初心與信仰
1953年,陳志遠(yuǎn)考入南開(kāi)大學(xué)歷史系,畢業(yè)后留校任教,深耕歷史研究。但他一度有意回避研究父親所經(jīng)歷的那段歷史。“我不忍心看到父親受刑的材料,也不愿將太多個(gè)人情感摻雜在學(xué)術(shù)研究中。”陳志遠(yuǎn)說(shuō)。
后來(lái),他意識(shí)到烈士教育不可或缺,開(kāi)始對(duì)父母革命歲月和革命精神的歷史資料進(jìn)行收集和整理。對(duì)他而言,揭開(kāi)歷史幕布的過(guò)程有欣喜,也有傷痛,但心中父親的形象愈發(fā)高大起來(lái)。
陳志遠(yuǎn)曾多次前往湖北黃岡的陳潭秋故居紀(jì)念館。看到有關(guān)父親的資料照片,他感慨萬(wàn)千:“父親的思想一直很進(jìn)步,他剪了辮子,穿著短褲,背著書(shū)包上新式小學(xué),可謂開(kāi)風(fēng)氣之先。”
陳志遠(yuǎn)曾3次前往新疆,在父親最后戰(zhàn)斗的地方緬懷悼念。“在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紀(jì)念館,我看到父親書(shū)架上擺滿了歷史書(shū)。我一輩子從事歷史教學(xué)研究,也算是跟父親的一種默契和傳承。”
在紀(jì)念館中,讓陳志遠(yuǎn)深受觸動(dòng)的,是有關(guān)陳潭秋的幾次審訊記錄。“當(dāng)新疆軍閥盛世才公開(kāi)走上反蘇反共道路后,1942年夏,黨中央同意在新疆工作的共產(chǎn)黨員全部撤離,父親把自己列入了最后一批。被捕后,敵人對(duì)他施以酷刑。父親的腳底都爛了,渾身上下都是傷,但鋼鞭和刺刀都無(wú)法刺穿他堅(jiān)定的信念。”陳志遠(yuǎn)說(shuō)。
陳志遠(yuǎn)沒(méi)有一張父母的合影。于是,他選了一張父親的照片和一張母親的照片放在了同一個(gè)相框里。照片中,兩人目光平和又堅(jiān)定,這張?zhí)貏e的“合影”一直擺在陳志遠(yuǎn)的書(shū)架上。他經(jīng)常看父母的照片,仿佛父母也在看他。“我沒(méi)有親耳聆聽(tīng)過(guò)父母的教誨,但他們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事跡始終是鼓舞我前進(jìn)的動(dòng)力。”
一路傳承,讓父輩的革命精神代代賡續(xù)
2004年,南開(kāi)大學(xué)圖書(shū)館第一黨支部在上海中共一大會(huì)址和浙江嘉興南湖紅船上組織黨日活動(dòng)。陳志遠(yuǎn)的女兒陳學(xué)清作為圖書(shū)館的工作人員,和同事們?cè)诋?dāng)?shù)嘏e行了入黨儀式。
陳志遠(yuǎn)不僅見(jiàn)證了女兒入黨的光榮時(shí)刻,還登上了承載著民族希望的“一葉紅船”,感受父親當(dāng)年的青春夢(mèng)想,祖孫三代的理想和信仰在這里有了交匯。
“我仔細(xì)看著父親曾經(jīng)戰(zhàn)斗過(guò)的地方,尋找著父親在船上的座位,想象著他就坐在那里。”回憶起這次經(jīng)歷,陳志遠(yuǎn)的內(nèi)心仍激動(dòng)不已。
在南開(kāi)大學(xué)工作期間,陳志遠(yuǎn)從普通講師成長(zhǎng)為知名教授,還擔(dān)任過(guò)系黨委書(shū)記。但無(wú)論角色怎樣轉(zhuǎn)變,他都兢兢業(yè)業(yè)、全心全意投入到教學(xué)中。
陳志遠(yuǎn)說(shuō):“多年來(lái),我一直在想,一定要健康地活著,帶著父母的DNA看看黨100歲的時(shí)候,國(guó)家是什么樣子。今年是黨的100歲生日,在黨的領(lǐng)導(dǎo)下,我們的國(guó)家越來(lái)越強(qiáng)大,越來(lái)越美好。”
從戰(zhàn)火中骨肉分離到秉承父母的精神砥礪前行,再到見(jiàn)證祖國(guó)的滄桑巨變……如果要來(lái)一場(chǎng)時(shí)空對(duì)話,88歲的兒子會(huì)對(duì)父母說(shuō)些什么呢?
“百年輝煌慶,敬告父母知。我想對(duì)他們說(shuō),他們畢生為之奮斗的夢(mèng)想已經(jīng)成真,后代沒(méi)有辜負(fù)他們的期望。如今,國(guó)家有了歷史性變化,我相信今后會(huì)更輝煌。”陳志遠(yuǎn)堅(jiān)定地說(shuō)。
(新華網(wǎng)、《人民日?qǐng)?bào)》(海外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