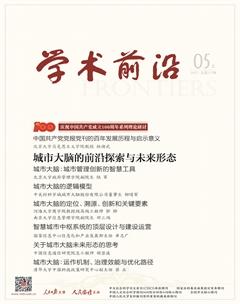財會監督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的定位及思考
張樂
【關鍵詞】 財會監督? 國家治理? 國家監督體系? 財政監督? 會計監督
【中圖分類號】 F812.2? ? ?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09.015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命題,確立了國家治理及政府治理的新方向、新任務。良治善治需要輔以有效的監督機制,在強有力的監督下方能實現令行政立、確保權力的正確行使。基于此,強化監督體系建設自然成為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題中之義。在國家監督體系中,財會監督是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所謂“天下未亂計先亂,天下欲治計乃治”,作為占據基礎性地位的監督形式,財會監督能為其他監督提供必需的數據支撐和執行依據,在維持良性經濟秩序、杜絕嚴重廉政風險、構建社會發展和國家治理的基石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進入新時代,財會監督應當立足自身定位,從滿足國家治理現代化實際需求的角度出發,持續進行體系建設和制度完善。
財會監督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的定位
財會監督是國家監督體系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是保障國家治理體系發揮效用的重要支撐力量。國家治理體系是一個國家制度優越性和先進性的具體體現,完善的國家治理體系既可以促進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也有利于增進實際治理效能。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監督體系是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對于穩步有序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具有重要作用。2020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屆中央紀委四次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要完善黨和國家監督體系,統籌推進紀檢監察體制改革”,“要繼續健全制度、完善體系,使監督體系契合黨的領導體制,融入國家治理體系,推動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治理效能”;還提出“要以黨內監督為主導”,推動包括財會監督在內的九大監督“有機貫通、相互協調”。上述重要指示不僅明確界定了財會監督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的位置,也拓寬了財會監督的內涵,同時還對財會監督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作為國家監督的重要組成部分,財會監督肩負著財稅政策實施、公共資源交易、社會財政支出、會計質量審核及地方政府信貸等重大事項的監督職責,是國家監督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優化社會資源配置、健全權力制約機制、打造清廉抗腐的執政環境等方面都發揮了關鍵作用。
財會監督是完善財政管理工作的內生性要求,是健全現代財政制度的必然規范。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科學的財稅體制是優化資源配置、維護市場統一、促進社會公平、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必須完善立法、明確事權、改革稅制、穩定稅負、透明預算、提高效率,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黨的十九大更明確地提出,要“加快建立現代財政制度,建立權責清晰、財力協調、區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建立全面規范透明、標準科學、約束有力的預算制度,全面實施績效管理”。上述政策表明,建設契合中國國情的現代財政制度不僅是提升國家治理能力的現實要求,也是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必要的制度保障。各級財政單位應遵從中央指示,全力貫徹推進財政體制改革的戰略規劃,狠抓決策部署落實,不斷完善財政治理體系,藉由制度現代化綜合提升政府財政績效。要完善現代化財政管理,財會監督是繞不開的基本內容,作為現代財政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貫穿財政及會計管理的整個過程,是財政管理形成有機閉環必不可少的環節,同時也是提高財政及會計管理的充分性、有效性,推動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保障。
財會監督的主要職能構成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正式確立并迅速發展以來,財會監督所發揮的作用愈發顯著,在有力保證中國財稅體制改革成功落地的同時,也有序形成了由財政監督及會計監督構成的職能體系。
財政監督職能。跟隨中國社會體制改革以及經濟市場建設的步伐,財政監督體系也經歷了數次重要變革,從20世紀80年代放權讓利階段的恢復重構,到90年代分稅制改革時期的優化發展,再到新世紀公共財政框架指引下的健全完善,最后及至201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修正版)出臺,財會監督逐步確立了財政管理主體業務的地位,并形成了監管范圍覆蓋財政運行全部過程、方位、口徑,監管要求由合規性為主轉向合規性、有效性共舉的格局。21世紀初,習近平總書記(時任福建省省長)曾撰文強調財政監督的重要性,指出健全的財政監督既能夠確保財政資金使用的有效性和正確性,也能夠擔負起社會經濟運行監測器以及警示器的角色。新時代背景下,財政監督需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中的職能安排及創建現代財政管理的客觀要求,從制度設計、技術升級兩個方面全力推進貫穿監督全程、覆蓋不同方位、囊括全部口徑的監督建設,并以合規性與有效性為原則導向,及時發現并應對財政管理實際執行中暴露的問題,為財政管理工作的順利開展保駕護航。
會計監督職能。會計監督必須依靠會計信息,會計信息是行政事業單位、市場主體及各類社會組織從事經濟活動的反映。科學的會計監督對于保障會計工作質量、減少會計信息不對稱、理順關聯主體利益關系、提高國家治理效率與能力都具有顯著作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會計法》的指導與規范下,中國會計監督體系持續成長完善,逐步形成了內部監督、政府監督及社會監督“齊頭并進”的總體監督框架。財政監督機構可以廣泛進行會計信息質量、注冊會計師行業執業質量及會計師事務所執業質量的審核檢查。2013年后,伴隨大批企業境外上市及《中華人民共和國資產評估法》的頒布,會計監督的監管范圍進一步延伸至跨境會計監管合作、資產評估行業執業質量檢查等領域,在穩定會計秩序、規避財務風險、維護市場經濟高效運行等方面都發揮了基礎性作用。立足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戰略需求,會計監督應以提高國家治理水平為根本出發點,并將保障經濟制度有效落實、協調社會各方利益關系、促進經濟秩序良性運轉作為最終目標。
財會監督助力國家治理現代化過程中面臨的主要問題
財會監督在當前國家監督體系內的地位有待加強。與財會監督所承擔的基礎性任務與保障性角色相比,其在當前國家監督體系內的地位偏低,集中體現在立法層級及執行效力方面。現階段,財會監督法律在權威性、體系化及約束力等方面都存在較大不足,具體而言:其一,財會監督法規的立法層次整體上相對偏低。規定財會監督具體事項的法律法規目前主要是由國務院及財政部頒布的管理辦法和處罰條例構成,如《資產評估行業財政監督管理辦法》《財政違法行為處罰處分條例》等。盡管現行法規體系已經能夠對財會監督主體進行較為全面的職能規范,但是由于其法律位階僅為行政法規,使得財會監督欠缺法律權威性。其二,財會監督的實際法律約束力不足。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會計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采購法》等重要的財政法律都對政府預算、采購、會計等重大事項的財會監督工作作出了規范性要求,但相關法條并未對財會監督主體的具體職能和實際操作作出詳細表述,這種偏原則性的規定所能產生的實際約束力相對有限。
財會監督與其他監督形式的協同配合尚存明顯不足。當前國家監督體系涵蓋黨內監督、司法監督、財會監督、輿論監督等十種監督形式,它們之間既有基于各自不同地位作用、層級類型而形成的分工關系,更有基于共性主旨和統一目的而形成的協同關系,就像一臺“機器”中相互獨立運作又彼此聯系支撐的不同“部件”,只有這臺監督“機器”的各個“部件”配合順暢、聯接可靠了,才能發揮出最好的監管效果。但當前我國各大監督主體在協同性方面還存在信息共享不順暢、協作機制不健全、整體成效不充分等缺點,亟需各方從實現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視角出發,持續推動聯動制度與協同機制建設,并運用大數據思維和信息化手段,增強不同監管部門的溝通便捷性、共享及時性和協作全面性,切實提高國家監督體系的綜合運行效能與整體職能水平。
財會監督結果未得到充分運用。開展財會監督最根本的出發點在于督促相關參與主體遵紀守法、規范落實各類財政及會計事項,減少人為原因和制度漏洞造成的風險損失,推進服務型政府建設,保障社會資源有效利用。而財會監督要完成以上職能,必須訴諸于監督結果的充分運用。但反觀現狀,無論是財政監督的結果還是會計監督結果,均沒有得到較為完善的應用,使得部分財會監督工作趨于形式化,難以發揮既定效能,距離形成監督和管理有機銜接的科學閉環尚存較大距離。
新時代背景下加強財會監督在國家治理體系中作用的建議
強化財會監督相關法律制度建設,促進財會監督發揮更大治理作用。為進一步確立并提高財會監督在國家監督體系中的地位,促進其更好地完成監督任務并在更大層面上發揮作用,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完善財會監督法律制度建設。首先,應盡快從概念層面對財會監督進行明確界定,并基于已經取得的改革法制成果,遵從新時代的治理要求,穩步推進制度體系構建,為提高財會監督執行成效搭好制度平臺。其次,應加快財會監督的立法步伐,借鑒國外先進財會監督法律的優點,正視當前存在的不足,在充分考慮中國國情的基礎上,提高財會監督法律體系的立法層級及系統化程度,加快制定和完善相關法律,以立法的形式來確立財會監督的監督程序、監督范圍及處罰措施,同時,明晰監督主體的監督職責和執法地位,強化監督頂層設計的構建。最后,還應優化財會監督的執法機制,藉由科學規劃及統籌安排,形成監督部門內部不同層級之間的高效運作與協調機制,創建分級合理、嚴謹規范、權責統一、運轉平穩、相互約束的監督管理體系。
深化協同機制與信息化手段建設,實現財會監督與其他監督形式的高度融合。一方面,應勠力推動各類監督力量在機制層面的有機貫通及在執行層面的相互協調。在全面堅持黨內監督高質量統領的前提下,結合財會監督在新時代背景下被賦予的新內涵、新使命,努力完善財會監督與其他監督聯動的監管生態,積極探索財會監督主體同黨政、司法、金融、稅務、統計等監督機構的協同路徑,并有效實現系統性、常態化的跨部門協作機制,通過制度化建設與實務性整合形成監督合力,激發國家監督體系發揮最大的監管效能。另一方面,應當利用先進的信息化工具,構建不同監督主體之間的監督結果共享機制。當前,不同監督方式間存在的協作壁壘與溝通障礙在很大程度上都與缺乏上下統一、互聯互通、完整有效的監督信息共享機制有關,因此,應當憑借現代通信、數據庫等前沿技術,打通監督協作的信息化關口,建立政府財政部門、司法機關、稅務機構、審計單位、人民銀行、金融監管機構等監督主體監督結果的數據共享平臺,突破單線監管體系,形成監督部門間的有機聯動,提升整體監督效率。
注重財會監督結果運用,助推財會監督提質增效。其一,要強化監督和管理的有機銜接,構建完整有效的監督閉環。堅持問題導向,完善從發現監督問題到反饋整改計劃、從追蹤治理進展到評估整改落實的閉環系統,推動監督結果向治理成果的高效轉化,保障社會資源的正確配置。其二,要進一步壓實主體責任,強化對違規事件的追責問責。一方面,應當通過提高財會監督相關法規的權威性和約束力來確保各類監督主體盡職開展監督工作,形成切實的監督成效,及時發現財政運行及政策貫徹中存在的漏洞。另一方面,要在明晰責任劃分的基礎上對違規單位及相關負責人實施嚴肅的追責問責,同時將履責評價納入干部提拔及人事考核的考評內容,推動責任落實到位,保障財會監督的實效。
參考文獻
胡少先,2020,《加強財會監督的思考與建議》,《中國注冊會計師》,第6期。
王宏、梁璐璐,2020,《堅持“四度”思維 提振財會監督》,《財務與會計》,第8期。
王清剛、曾怡、吳丹丹,2016,《財會服務與監督職能的前置——基于HBDL公司業財一體化的經驗》,《會計之友》,第13期。
王艷,2020,《加強財會監督的新視角:基于法務會計的思考》,《中國注冊會計師》,第8期。
習近平,2000,《財政監督就是政府監督》,《中國財政》,第10期。
徐慶紅、趙締,2020,《財會監督在新型國家監督體系下如何發揮重要作用》,《財務與會計》,第10期。
楊雄勝,2020,《財會監督需要新的認識視角》,《財務與會計》,第9期。
責 編∕陳璐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