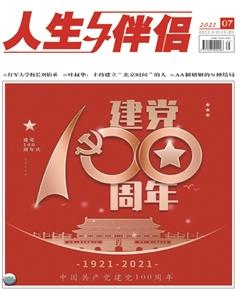印度新娘婚禮中猝死,妹妹當場頂替
吳陽煜
按照印度的陰歷國定歷,每年的5月通常是這個國家的結婚旺季。今年的5月下旬,在印度北方邦埃塔瓦地區,發生了一樁令人匪夷所思的婚禮。
在這場起初充滿歡慶氣息的婚禮上,新娘蘇拉比在撒落的碎花中,和新郎彼此交換戴上了花環后,就突然暈倒失去意識。蘇拉比的家人打電話喊來醫生,沒過多久,醫生就宣布蘇拉比因心臟驟停死亡。
婚禮的現場新娘猝死,這原本就足夠讓在場的人震驚和意外。更令人意外的是,新娘尸骨未寒,男方和女方家人坐在一起碰頭后,竟然當場就將新娘的一位妹妹許配嫁給了新郎,也就是她本來的未來姐夫。
根據印度當地媒體報道,蘇拉比的叔叔對侄女的猝死表達了悲痛:“這對我們家來說是一個艱難的決定。一個女兒躺在一個房間里,另一個女兒的婚禮正在另一個房間里進行。”
婚禮的歡樂還沒落幕,死亡的悲痛就已襲來,轉眼又是下一場婚禮的舉行。據印度媒體報道,蘇拉比的妹妹和新郎的婚禮結束后,才舉行了已故新娘的葬禮。
婚姻是人生大事,從中也可窺見社會文化淵源和流轉。在這起荒誕色彩濃厚的婚禮鬧劇背后,可以看出印度各地的婚俗文化,仍保有痕跡明顯的傳統色彩。這個“傳統”里,最為突出的特點就是印度女性地位低下問題。可以想見,在相當一段時間里,類似的魔幻事件在印度半島里的不同角落還會上演。
血泊中的孕婦
屋外的年輕男子滿臉焦急,等候著懷孕的妻子分娩。可當嬰兒啼哭的聲音傳出,他從接生婆那里得知是女嬰的消息后,臉上欣喜興奮的表情瞬間凍結,冷酷地把自己的女兒親手溺死。這是2003年上演的印度電影《沒有女人的國家》里的一幕劇情。
這幕劇情絕非藝術化夸張,而是對印度社會的“寫實”。印度社會各界早有共識,人工干預是造成該國人口性別比例嚴重失衡的主要原因。根據推測,到2030年時,印度人口將突破15億。而有數據統計表明,上個世紀中葉以來,印度人口男女比例失衡愈發突出:1961年時,印度每1000名男性約對941名女性;在2001年,與1000名男性相對的僅為933名女性;到了2018年,有些地區這一數字達到令人擔憂的152:100。
全國范圍的性別比例失衡加劇,具體到印度某些邦,情況則更為嚴重。而以選擇性別為目的的人工流產,是一個重要原因。2018年時,《柳葉刀》曾發布報告估算,僅在2015一年間,全印度就有超過1500萬例人工流產,其中78%是在醫療機構外進行的。
不安全墮胎無疑對該國孕婦的身體造成極大甚至致命的傷害——印度有醫藥界相關觀察指出,全印孕婦的死亡原因中,不安全墮胎高居第三位。
在更廣闊的印度農村地區,更為科學的現代避孕手段遠未完全普及,遑論更加理性的生育方案。根據《柳葉刀》所估算的數據,2015年這一年,在印度4810萬懷孕婦女中,大約一半都是意外懷孕。
印度女性的“生育之禍”如此嚴重,除了公共衛生意識缺位、傳統道德觀念束縛和經濟原因之外,還有極具印度特色的因素。有印度當地的援助機構指出,對于那些20歲左右、沒有穩定經濟來源的單身女性,在醫院尋求幫助時經常會受到醫生和院方的羞辱或騷擾。
生育和性健康話題在印度大部分地區,依然和恥辱以及禁忌劃等號。更為可怖的是,由于男女性別比例失衡嚴重,而傳宗接代需求又強勢存在,導致人口拐賣、對女性的暴力事件在印度成為社會頑疾。
從童婚到早夭
在1957年,印度政府統一了各地五花八門的歷法,正式制定了官方歷法印度國定歷。國定歷一年設六個季節,如上所述,5月是印度的結婚旺季,主要原因就是因為5月過后,在接下來的年內,所謂的“吉祥婚禮日期”一般都會大幅減少。這樣的吉祥婚嫁日,對眾多兒童新娘而言,往往意味著人生悲劇。
歷史資料顯示,早在印度還是英國殖民地的1929年,當局就通過立法明令禁止童婚。但這個法律,起初沒有任何震懾作用,后來推行過程中也是阻力重重。作為印度教曾經沿襲的舊規,直到1970年代,童婚制度仍然在印度不少邦盛行。
1978年,印度政府將男、女適婚年齡定為21、18歲,可童婚習俗仍可見于印度農村,甚至在某些邦的山區部族,每年5月的結婚旺季里,還保持著兒童集體婚禮儀式的古老傳統。
根據印度相關部門的統計,2005至2006年間,超過44%的女性在16~17歲間結婚,22.6%的女性在16歲前結婚,其中包括2.6%在13歲前結婚的童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發布報告稱,全球“兒童新娘”里,超過三分之一都來自印度,并且光在2007年一年中,就有接近2500萬印度女性滿18歲時,就屬于已婚狀態了。
按照印度教的傳統教典,童婚是被贊成、提倡的婚俗行為。當10歲出頭的女童到了“夫家”以后,她的命運就被完全交到其丈夫一家人手上了,因為身體過早生育的緣故,所以兒童新娘早夭事件比較常見。
居住在印度北部城市古爾岡的Bilas今年28歲。在他的經歷和記憶里,童婚是自己身邊確切發生的事情:“在過去,印度的童婚傳統在農村地區非常盛行。我的奶奶還未成年的時候,大約12歲左右就結婚了。”
在印度許多廣袤的農村地區,國家層面的經濟發展成果尚未惠及當地,在急著把女兒嫁出去的父母眼里,結婚成本相對更低的童婚有了延續下去的動力。“在新德里、班加羅爾、加爾各答和孟買這樣的大城市,男女平等的意識一直在被推廣,女性的社會地位確實在慢慢提高。在這些大城市里,女性能獲得的工作機會也更多,她們就可以自力更生,不用再依賴丈夫。”Bilas告訴看世界。
但與此同時,在印度許多貧窮的農村家庭,因為沒有穩定、自主的經濟來源,非常多的農村婦女終其一生不懂“自由戀愛”為何物,聽由家長決定出嫁的年齡和對象;婚后也只能惟丈夫是從,不能提一點反對意見或建議。
Bilas對看世界說,“在農村并沒有那么多好的工作機會,提供給女性的職位更是少之又少,可以說95%的農村女性婚后都是家庭婦女。自己想買一些小飾品什么的都要向丈夫開口拿錢。在這樣一個大男子主義的社會里,無論丈夫說得對或不對,她們基本都只會照做。”
有長期跟蹤印度社會的研究者發布報告稱,在印度,童婚女性更易進行三次以上的生育,生產兩個孩子的間隔不到兩年、多次意外懷孕、終止妊娠以及絕育的可能性也更高。
“幸福”的印度男性?
對于印度與婚姻相關的傳統,Bilas還說了這么一段故事:“在以前的印度農村,比童婚更過分的還有陪葬習俗。在有的邦,丈夫去世火化后,他的妻子也要跟著火化,按照宗教的解釋,這是村里的人希望這對夫婦可以到天上繼續團聚。有的地方不用妻子陪葬,卻要求她們在丈夫去世后終生吃素,并且一輩子只能穿白色的衣服,不能再結婚了,表示自己生活里的開心和快樂都隨著丈夫的離去而消失了。”
盡管在農村地區,這些驚悚的婚俗陋習逐漸被印度政府取締,但Bilas認為,大部分印度農村女性距離掌握婚姻自主權,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和埃塔瓦地區這起婚禮鬧劇有些類似,Bilas以身邊一位女性朋友的遭遇為例稱,這名女性在和男方訂婚后,她的未婚夫突然反悔,以“不想和這個女人結婚”為由,取消了婚約。但女方家庭為了遵循相關習俗,認為家中女兒訂婚后若不能順利結婚,也要立刻找另外的男性完婚,所以匆忙為其安排了新的結婚對象,并很快舉行了婚禮。
不難看出,Bilas所舉這個真實例子,與那起婚禮鬧劇相比,只是少了新娘猝死的悲劇,而Bilas那位女性朋友無法決定自己婚姻命運的悲劇,還是那樣扎眼。更為扎眼的是,造成印度女性悲劇背后的社會傳統、習俗。而這些傳統、習俗背后,是印度男性的“存在感”。
從印度教傳統文化的角度來看,絕大部分印度家庭都認為,家里的男人肩負著傳宗接代的重任,甚至覺得沒有兒子的家庭是殘缺、不完整的。從印度教以火葬為榮的習俗出發,在農村,這也和男尊女卑的觀念牢牢綁定在一起:若死后沒有兒子為其點燃火葬的柴堆,死者的靈魂則無法升入天堂。
而在另一方面,嫁妝制度在現代印度社會的沿襲,也影響著女性地位的改善。嫁妝糾紛經常引發嚴重的社會問題,還因此迫使印度政府在1960年代推出了《反嫁妝法》。但直到如今,嫁妝制度在印度并未被真正廢除,相反,不少印度富豪們的奢華婚禮排場,倒是經常登上全球各家媒體的新聞。
與東亞國家習俗幾乎完全相反,在印度,女性出嫁,女方家庭要拿出比男方更加豐厚的嫁妝。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印度傳統婚禮的嫁妝,也從過去的牛、首飾和一些家具,升級為更為直接的現金,甚至更為高端的汽車、別墅。
這也就意味著,一個家庭如果生出了男孩,就如同下了一顆金蛋,因為在未來有可能收獲不菲的彩禮。如果生的是女孩,那基本就是與負債劃等號。而且,女性出嫁所帶的嫁妝彩禮越少,在夫家的地位也就越卑微。男方因對女方嫁妝不滿而在婚后家暴女方,在印度社會時有發生。
“女方要給男方的嫁妝越來越好,彩電、家具、冰箱、洗衣機,我都見過用這些做嫁妝,當然還有必不可少的金首飾。有不少外國人聽說之后,都跟我說,覺得印度男人很幸福。”Bilas說這些話時,語帶嘲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