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春成:寫作不是戰斗,它有點像釣魚
蒯樂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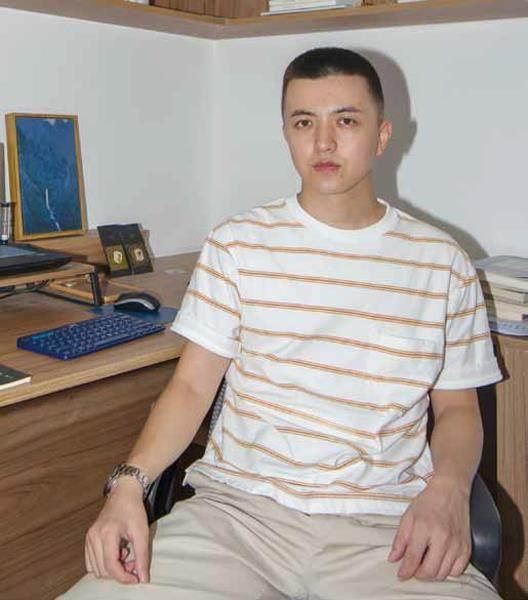
圖/受訪者提供
陳春成不善言辭,但這不影響他在需要的場合侃侃而談。有時候,當一個可以談論文學的對象突然出現在他面前時,這種談話會變得密不透風,像打開了一枚濃縮罐頭。在日常生活中略顯尷尬的談話內容此刻突然變得合理了:關于語言、節奏和文字的美感,這些東西輕易不付諸口頭,也是妙處難與君說。
《夜晚的潛水艇》是一本奇跡之書,作為90后文學新人的第一本作品,它的成績好得令人瞠目。上市短短數月,便已囊括《亞洲周刊》2020年十大小說第二名、豆瓣2020年度中國文學(小說類)的Top1、Pageone文學賞首賞,以及第六屆單向街文學獎年度作品等獎項。“陳春成給了我一個驚喜。我想起NBA,他們對那些充滿潛力的年輕球員有一個形容,天空才是他的極限,這話也可以用在陳春成的身上。他比較厲害的一點是,既飄逸又扎實,想象力非常豐富,寫現實的部分又很扎實,轉換和銜接都做得非常好,很老練的作品。我覺得他是一個前程無量的作家。”余華這樣贊他。
語言自成王國
這是一個90后的理科男生,在泉州一家植物園工作。讓他自己描述的話,便是“平淡上班族男子的業余寫作”,也像福建山野邊民的舊傳統,“忙時為農,閑時為匪”。“工作謀生如本分種田,悶了閑了,無可紓解,就去當一陣子‘土匪,興盡了再回來。寫作于我即是快馬、長槍、大碗的酒和阻絕兵馬的群山,是內在的狂歡,平息后即歸于日常。”
跟那些立足于寫實主義的作家不同,陳春成寫的大多是想象,而這種凌波微步,也激發出讀者的想象,他們在他的寫作中,看到了他們熱慕的大師的品質。非常有趣的是,有人說他像卡爾維諾,有人說他像博爾赫斯,還有人說他像納博科夫。都是他。
這種奇特的代入甚至讓寫作者自己感到驚奇,沒錯,陳春成確實是博爾赫斯的擁躉,但他更多的文學營養來自漢語傳統。他喜歡汪曾祺,喜歡杜甫,喜歡舊體詩和散文,對于翻譯小說,他對譯本的挑選很謹慎,西方小說太依賴于譯者的漢語水平了,他有時會擔心看得太多,影響到語感。
新文化運動以來,整個中國的白話文運動,都是建立在對西語體系(翻譯語言)的借鑒之上,但陳春成卻自覺地接續著一個更古老的文化傳統。
小說出版之后,有很長時間,他都沒有再寫。最近有點迷上了翻譯,為了文字上的快感,也因為看見翻譯家說,翻譯每天有一個固定的工作量,比較容易安心。
他翻譯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的詩作,后者也以低產著稱,常常一年里只寫三四首詩,也不局限于韻律,但是每一首都有著交響樂式的內在節奏。比如他翻譯的這首《舒伯特風格》:
“而那個從一生中捕捉著訊號/將其化為普通和弦/供五把琴演奏的人/那個使江河穿過針眼的人……每天早晨準時站在他的寫字臺前/讓那些精彩絕倫的蜈蚣爬滿稿紙。”
試譯之后,他會把自己的譯本,跟其他著名譯者的版本比較,看看不足和不同,“像是發現了一個可以一心貫注于語言的游戲,因為沒有人比翻譯家更在意語言了。”
想象力總是及時出手相救
中學時,他一直喜歡語文,語文老師也喜歡他。但他其實不太看得上作文的套路,平時只是應付,甚至覺得白話文很累贅。自己偷偷寫舊體詩,詩成亦懶于示人;讀文言文,沉迷其中。“我覺得那個是更高的。‘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什么段落能比擬得了這樣颯沓的節奏?暑假在家讀《后赤壁賦》,非常喜歡,‘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當時就覺得這個‘之很好,音調舒緩起來,如果刪去,就是文,他在《東坡志林》里會這樣寫,簡省;如果留著,就是賦,詩和文的合體。”他深知這種細嚼文字的能力,無論是應付考試還是做研究,用處都不甚大,但是依然“悟悅心自足”,似乎永遠可以這樣探究下去,悠然心會,當一個津津有味的讀者。
“寫小說讓我覺得自己并非一無所長、一事無成,但是閱讀、抄寫、品嘗那些古詩文的時候,會覺得長于什么、成了什么、何所得,似乎都不太重要了。在那種廣大與深微面前,完全消泯了競爭心和自我意識。”
這種深度的愛好,并沒有成為他的求學方向,他陰差陽錯地學了理科,考上了土木工程專業。對一個沉浸在古典文學里的人來說,土木工程真是毫無詩意的學科:累、難,沒女生,考試挺費勁,不花時間還不行,就業也不輕松,與他喜歡的文言文似乎分站兩極,一邊是實際的、具體的、經世致用的,另一側則是玄妙的、想象的、詩意的無用之用。
想象力總是及時來搭救他。他設想過自己學了一個研究古典文學的專業,大學時光因此變得愉快許多,“我看外國小說到一個程度有時會看不下去,但是對古文,我永遠也不會膩煩。”他甚至把自己寫的古典詩拿出來,假裝是古人寫的,去請教一位中文系的教授,竟然蒙混過關,沒有被教授看出破綻,于是心中竊喜。
他的小說《竹峰寺》是一個關于“藏”的故事。他寫了一個心事重重的少年,試圖藏起自己舊居的鑰匙,卻在無意中勘破了佛寺幾百年來秘藏的珍貴碑刻。小說已經寫畢付梓,他的想象力還沒有結束。于是額外題一首《清秋寄慧燈上人》,假托寫給竹峰寺里的慧燈和尚:“書案久冥搜,湖亭一騁望。林壑浸秋光,襟懷亦清曠。淵鱗安其寢,霜羽恣所向。息心古木邊,得句蒼煙上。禪林會相訪,披草說空相。竹峰暝色中,疏鐘繞青嶂。”
他總是有很多關于交通工具的想象,移動的封閉空間,可以把他帶離此地。還在讀書時,他有時會把教室想成一節一節的火車廂,一條走廊邊的許多教室,便是一連串的車廂,仿佛《東方快車謀殺案》,搖晃著,半夢半醒,火車在時間中行駛,每45分鐘,便到站一次,鈴聲響起,坐累了的乘客們如釋重負,涌向走廊邊,趴在欄桿上,要么看風景,要么向空中看不見的小販們伸出手臂,買賣貨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