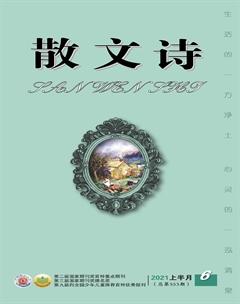截面,或筆記
潘玉渠,1988年生于山東滕州。作品散見于《散文詩》《星星》《揚子江》《詩潮》《詩林》《草堂》等刊物,參加第18屆全國散文詩筆會,獲揚子江·2016年度青年散文詩人獎。現(xiàn)居四川金堂。
天體論
能嗅到的不是花香,是星云——鼻子如此敏銳。
你蟄身其間,冥想,旋轉(zhuǎn),在腳步尚未抵達黑洞前,盡力清除視野中的埋伏。為了剝落心頭的針刺,你開始學(xué)習(xí)溫順,學(xué)習(xí)在迂回中找尋方向、信念,培植堅定的韌性。
——仿佛新生的嬰孩,積蓄著體量和力氣。
當行進的軌道日趨穩(wěn)定,從眼角撐開的枝杈,將以磅礴的光線,交出浩大的身影。你使勁敲打宇宙的拱門,哪怕它正一寸寸地裂變。你無數(shù)次矯正內(nèi)心的渴念,像對待險境那樣規(guī)范自身。
雖然,一些突襲而至的天外來客,屢屢試圖篡改你的周遭,但是,你總能堅守住陣腳,堅守住內(nèi)心那份獨立的孤寂。
不妥協(xié),不放棄——如同,春天堅守崢嶸的綠意。
一棵柿子樹
一棵柿子樹,孤零零地站在路旁,仿佛患有孤獨癥。
幾枚熟透的果實,明晃晃的,懸垂如燈;而異常纖弱的枝干,撐開晦暗的天色,像一位堅強的母親。
即便如此,亦未激發(fā)我們的憐憫,善待于她——
每人踹了一腳,以期震落幾枚果實。
她晃了又晃,盡力平復(fù)戰(zhàn)栗的身體,保全所有的孩子。
看到這一幕,我的心突然隱隱作痛,一種莫名的酸楚和愧疚蔓延開來。我想到,類似的惡行,是否也曾從別人的肢體里生出?
如果有,在我們到來之前,她是如何躲過那些摧殘和驚險的,又是如何守護好孩子們的……
我們繼續(xù)前行,層巒向腳下傾斜,內(nèi)心逐漸收緊。腦海里一直浮現(xiàn)著她孤苦的樣子,好像某種尖銳的教誨,被一點點加深。
重 游
二十天后,仍是晴日朗照,輕云低徊。
當我們再次來到集鳳鎮(zhèn),回到這片山水的深處,若有若無的風從身邊掠過,宛如一種低緩的密語——串聯(lián)著自然的譜系。
我們再次路過金雞寺、中藥加工廠、郵政局和雜貨鋪,接著聊起上次的話題,用嬉皮笑臉的打趣,整飭精神上的散漫。
對于我們來講,卸下心頭的負累,在陽光下悠然地走一走,要遠勝過一次禱告、一劑中藥和一場被柴米油鹽浸泡得變形的愛情。
我們說過的那些話,并不暗含任何企圖,卻能水過溪澗似的將眼前的世界,勾勒出锃亮的弧度。
或許,人間的本來面目就是如此:現(xiàn)實斑駁,理想懸空而立,不排斥轟轟烈烈的榮光,也希求淺唱低吟,能夠撫平那些意料之外的坎壈與悲辛。
郊 游
在山中漫步,便可忘掉層層壘疊的氐惆,讓機械的日子長出骨朵。
剔除風水之說和造物主的設(shè)定,我們還可憑空想象,在春天的稿紙上豢養(yǎng)明媚的琴音,讓寥廓的視野窯變出溫潤的冰裂。
我喜歡將大把大把的時間鋪展在群山深處——喧囂人間的外圍,隱者一樣輕輕綻放,打撈廢舊的夢囈。
我知道,山道下埋有土石斷折的骨頭、草木凋落的老靈魂,以及古戰(zhàn)場上倒下的凜凜奔馬……它們盤踞成團,注解著黑暗。
我亦知道,隨手撿起的那枚白色石子,是另一個來歷不明的自己,在遙遠時代留下的標記——
指引我逆著歲月的流向,探尋被忽略不計的卑微物什。
縱然體力漸漸不支,腳步似鉛,我也喜歡以這種修行式的郊游,復(fù)述理想的貧瘠和內(nèi)心的靜默。
金雞寺帖
寺門前的石獅子,以蹲踞的姿勢,敞開一己的肅穆。
自從被斧鑿馴服后,它們就開始守護方圓二十里的香客,引導(dǎo)塵世間的諸般不順,求得對癥之藥。
但不知從何時起,一種失控的頹敗之象,開始侵入基座:青苔如毯、刻線渾濁,門楣上的浮塵,連同舊楹聯(lián)令人警醒的禪意,一同顯示出某種無以為繼。
……或許,是觀念變了。
這些唯心論的載體——樸素的古物,被一再視作風景的贅余,乃至民俗學(xué)的注腳,被一筆帶過。
眼前,荒草蔓生,香火冷寂。
不可復(fù)原的熱鬧停留在了歷史深處。
呈現(xiàn)在我們面前的,是另一種截面:時代與人心的演進,稀釋了信仰的虔誠,空余下幾許恍惚,幾許冷漠——
漫無邊際地游蕩、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