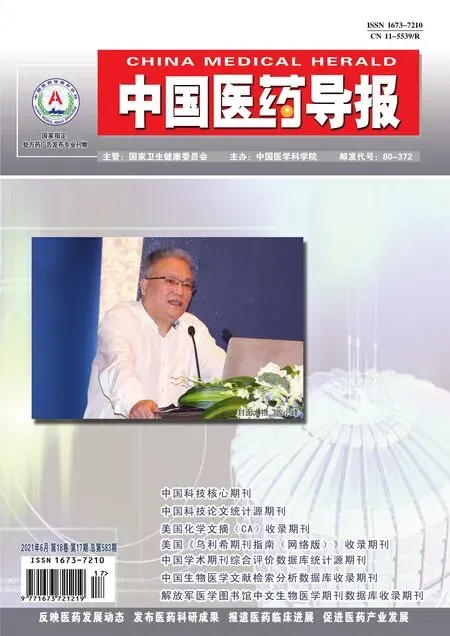基于數據挖掘的針灸治療功能性月經不調的選穴規律研究
劉楊杰 管鳳麗 孫 瑩 杜惠蘭
河北中醫學院研究生學院,河北石家莊 050091
月經不調是以月經周期、經量及經期異常為主要 表現的婦科常見病,常由器質性病變或功能失常引起。臟腑功能失調、沖任督帶損傷是導致功能性月經不調的主要病機[1]。目前現代醫學主要采取激素藥物治療[2],治療效果明顯,但均伴有不同程度的不良反應[3-4]。中醫針灸治療,以經絡辨證為主,結合臟腑辨證及八綱辨證,通過針刺、艾灸或針灸并用而達到通經脈、調氣血、扶正祛邪、調和陰陽之功[5]。已有研究表明,針灸輔助治療月經病能提高臨床療效,改善患者生活質量,并縮短病程[6-8]。臨床實踐及查閱文獻發現,針灸治療本病的選穴多樣,臨床醫家用穴各有特色。本研究旨在通過文獻數據挖掘方法,檢索中文主要醫學數據庫,選取十年來針灸治療功能性月經不調的臨床文獻,對腧穴進行提取及整理,分析腧穴的基本使用情況,發現選穴和組合規律,為臨床針灸治療功能性月經不調規范化循證提供理論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文獻檢索
計算機檢索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CNKI)、萬方學術期刊全文數據庫(Wanfang)、維普中文科技期刊數據庫(VIP)、中國生物醫學文獻數據庫(SinoMed),檢索2010 年1 月—2020 年9 月關于針灸治療功能性月經不調的臨床研究期刊文獻,檢索詞“月經不調”“月經先期”“月經后期”“月經先后不定期”“月經量少”“月經過多”“經期延長”“經間期出血”“崩漏”“功能失調性子宮出血”“功血”“排卵障礙性異常子宮出血”分別與“針灸”“針刺”“針藥”兩兩進行組合檢索。
1.2 文獻納入標準
①診斷明確;②以針灸治療為主要治療方式,單獨或結合其他治療手段,且作為試驗組;③文獻類型包括隨機和非隨機臨床對照試驗;④具有明確針灸穴位;⑤臨床總有效率≥85%。
1.3 文獻排除標準
①文獻類型:個案報道、綜述、經驗總結、病例總結、回顧性研究、學位論文及會議論文;②無對照組的文獻;③因器質性變、手術或藥物等因素導致的異常月經情況,如子宮肌瘤、子宮腺肌癥等;④穴位記錄不明確或穴位名稱不規范;⑤治療為單一的非針刺治療方式,如艾灸、穴位埋線、刺絡拔罐、耳穴、頭針療法;⑥辨證分型選穴未寫明具體癥狀選穴;⑦同一課題組不同時期發表的文獻保留發表年限最近者,余排除。
1.4 數據提取及處理
腧穴定位、歸經、特定穴、部位等均參照“十二五”國家級規劃教材《經絡腧穴學》[9]標準進行。若1 篇文獻存在2 組及以上的穴位處方,或除主穴外,存在辨證分型或分期或伴隨癥狀選用的配穴,則將處方進行拆分,采取以主配穴的方式為一處方進行錄入[10]。將文獻題目及穴位處方錄入到Excel 表格中,采用IBM SPSS Statistics 25.0 統計軟件對表中的信息進行頻次及聚類分析,如所涉及的穴位個數及頻次、穴位歸經、穴位部位分布等;采用IBM SPSS Modeler 18.0 進行關聯規則分析。
2 結果
2.1 文獻檢索結果
以“月經不調”等詞分別與“針灸”等詞結合作為檢索詞,分別檢索中文四大數據庫,共檢索到2787 篇文獻,將文獻題錄導入到Note Express 軟件中,去重后共得1269 篇文獻,通過閱讀題錄進行初步篩選,后對全文進行閱讀再次篩選符合要求文獻,最終共54 篇文獻納入研究,具體見圖1。

圖1 文獻檢索技術路線圖
2.2 處方穴位數目統計
按照主配穴方式進行針灸處方錄入,得146個處方。具體所選穴位數目及頻率見表1。

表1 針灸治療月經不調的選穴數目情況
2.3 腧穴使用頻次情況
在146個處方,涉及40個腧穴,腧穴總頻次797 次。腧穴出現頻次在10 以上的共有20個穴位,見表2。腧穴頻率=腧穴使用頻次/腧穴總頻次×100%。

表2 針灸治療月經不調的穴位頻次情況(頻次≥10)
2.4 處方選穴歸經情況
40個腧穴分布于10 條經脈,腧穴歸經及使用頻次見表3。

表3 針灸治療月經不調選穴歸經及數目統計
2.5 腧穴分布部位情況
腧穴主要分布于人體的胸腹部,頭頸及上肢部的腧穴選用較少。見表4。

表4 針灸治療月經不調的穴位分布情況
2.6 腧穴的特定穴使用情況
針灸治療功能性月經不調的40個腧穴中33個為特定穴,總共使用頻次為852 次,除去重復選穴,如關元既為募穴又為交會穴,實際總使用頻次為632 次。見表5。

表5 針灸治療月經不調腧穴的特定穴使用情況
2.7 腧穴關聯規則分析
采用IBM SPSS Modeler 18.0 分析軟件對40個穴位進行關聯規則分析,設置最小支持度為20%,最小置信度為80%,可得到16 條關聯規則。見表6。支持度是在所有選穴處方中前項和后項同時出現的處方所占的比率,置信度是前項出現的條件下后項出現的概率[11],如治療功能性月經不調時選用關元穴治療的同時選用三陰交穴的處方在總處方中所占的比率為89.73%,在選用中極穴后選用三陰交穴的概率是100%。

表6 針灸治療月經不調腧穴關聯規則分析
2.8 腧穴聚類分析
選用IBM SPSS Statistics 25.0 軟件對使用頻次10 次以上的腧穴進行聚類分析,得到相應的冰柱圖(圖2)和樹狀圖(圖3)。根據圖2 結果示,按群集數10 來分,可以得到5個有效聚類群,分別為脾俞-足三里、太溪-腎俞、歸來-命門、子宮-合谷-陰交、太沖-膈俞-行間-地機-期門-肝俞。根據圖3,若將使用頻次>10 的20個腧穴分為兩類:一類為治療功能性月經不調的主穴,即關元、三陰交;一類為辨證選穴。

圖2 針灸治療月經不調腧穴聚類分析冰柱圖

圖3 針灸治療月經不調腧穴聚類分析樹狀圖
3 討論
針灸治療功能性月經不調的選穴數目多集中于5~8個穴位。《針灸大成·頭不可多灸策》中記載“不得其要,雖取穴之多,亦無以濟之,茍得其要,則雖會通之簡,亦足以成功”,又有“寧失其穴,不失其經”之說,可見治療疾病不在于選穴數目的多少,而是謹守病機,辨析經脈,依法選穴,方能效如桴鼓,即“經脈所過,主治所及”之意。
本研究通過對穴位頻次分析發現三陰交、關元、氣海使用最為廣泛。關元、氣海均是任脈之穴,《素問·舉痛論》記載“沖脈起于關元”,關元連通沖任二脈,《針灸甲乙經》言“沖脈任脈者,皆起于胞中,上循脊里,為經絡之海”。三陰交位于脾經,為足三陰經交會穴,集三陰經之氣血。故此三穴配合,共奏調沖任、益氣血、調理肝脾腎之功。有研究證實通過對特定模型大鼠的實驗證明了針刺或艾灸關元、三陰交對下丘-垂體-卵巢軸的良性調節,可以改善激素水平[12-13],改善子宮環境[14-15],調節免疫功能[16]及因內分泌失調而導致的月經不調癥狀[17-18]。
選穴所涉及的10 條經脈,任脈居于首位,《婦人大全良方》言“婦人病有三十六種,皆由沖任損傷而致”。沖任失調是導致月經不調的主要病機,關元、氣海,本經取穴,從疾病的根源治療月經不調。《醫宗金鑒》云“女子陰類也,以血為主”。沖任隸屬陽明,足陽明胃經為多血多氣之經,與足太陰脾經相表里,為后天之本、氣血生化之源,氣血足,則胞宮得養,經血化生有源。因此,常選取脾胃二經,表里經配穴,調理氣血。
《類經·藏象類·奇恒臟腑藏瀉不同》:“女子之胞,子宮是也。亦以出納精氣而成胎孕者為奇。”本病病位在于胞宮,胞宮居于人體下腹部,而腧穴頻次使用最多者亦出現在胸腹部。子宮穴為經外奇穴,位于臍下4 寸,前正中線旁開3 寸,婦科疾病常用穴,常為辨證選穴[19]。針刺可引起深層肌肉被動節律性運動,進一步引起子宮等臟器的運動,從而改善血液循環[20]。背腰部的次髎、十七椎等均在解剖位置上與胞宮相鄰,乃近部選穴原則,即“腧穴所在,主治所在”。任脈、足三陰經、足陽明胃經均經腹循行,選取膻中、太溪、太沖等以補腎疏肝,寬胸理氣。
在特定穴的選穴中,交會穴使用頻次最高,交會穴是兩條或兩條以上經脈經過的穴位,不僅可以治療本經疾病還可以治療與之相交會經脈的疾病。腎藏精,主生殖,“經水出諸腎”,調經必先治腎。腎經與任脈交于關元穴,與沖脈并行;肝經、脾經與沖脈交于三陰交,又均與任脈相交,治療本病取任脈之交會穴亦達到補腎調肝健脾之用。募穴、背俞穴是臟腑之氣直接輸注的地方,俞募配穴“從陰引陽,從陽引陰”達到陰陽平和。太沖、太溪分別是足厥陰、足少陰經之輸穴,陰經以輸代原,故兩穴又同為原穴,《靈樞·九針十二原》中記載“凡此十二原者,主治五臟六腑之有疾也”。女性以肝為先天,肝藏血,主疏泄,肝氣調達,則胞宮藏瀉有度,經候如常。因此,從另一側面體現出月經不調的發病主要涉及腎肝脾三臟。
通過對腧穴進行關聯規則分析可以發現核心穴對為“關元-三陰交”,常用處方選穴為“中極、關元、三陰交”。《素問·上古天真論篇》記載“女子七歲,腎氣盛,齒更發長;二七天癸至,任脈通,太沖脈盛,月事以時下”,腎氣化生天癸,促生長,作用于任沖二脈,沖脈為十二經脈之海,任脈為陰脈之海,任通沖盛,血海滿溢,血至胞宮而來潮。督帶二脈司約束,故月經呈周期性滿溢。關元、三陰交選為主穴,以臟腑、經絡辨證為出發點,使所選之穴不離其臟。再加中極穴,三穴配伍采用了近部遠端配穴相結合,以調理沖任,溫經行氣。臟腑、氣血失常則導致月經紊亂,聚類分析得到脾俞-足三里可補脾益氣、調暢氣血,腎俞-太溪、歸來-命門可益腎填精滋陰,肝俞-期門、太沖可補肝疏肝,暢達氣機等,可治療因氣血虛、腎精虧、肝郁氣滯等引起的月經不調,配穴的使用需結合疾病虛實辨證選穴。此外,合谷與陰谷相配為一組穴,合谷為手陽明經之原穴,有雙向調節作用[21]。陰谷為足少陰腎經合穴,既可祛寒濕邪,利經氣,又可補腎助陽[22]。兩穴體現了上下配穴法,一陽一陰,一升一降,條暢氣血,升降有常,可治療經閉、崩漏、滯產等。筆者查閱文獻發現對兩穴治療婦科疾病研究相對較少。不過,有研究證實按摩合谷可以明顯縮短產婦產程,減輕疼痛及減少產后出血量等[23],配合其他經腧穴常可擴大其治療范圍[24]。對于陰谷-合谷兩穴配合治療月經不調的效果需進一步進行臨床研究。
本研究仍存在不足,對于文獻的篩選原則依據研究者而定,尚未有統一標準,文獻質量存在差距,對于本研究結果可能產生一定偏差。因對于某疾病如月經先期、月經后期等采用針灸治療文獻報道數量較少,且分型不統一,因此其選穴配伍規律仍有待進一步研究。通過本研究發現臨床治療功能性月經不調選穴基本與月經不調的發病機制及相關病因相符合,與潘銀鳳[25]部分研究結果相一致,可為臨床針灸治療本病提供理論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