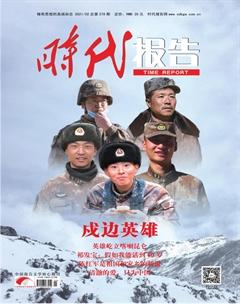愿乘長風破萬里浪
安頻

“耐可乘明月,看花上酒船。”這是李太白《秋浦歌》組詩中的一句。船的歷史,說起來源遠流長。在幾千年前,我們的祖先就發明了船。幾十年前的監利西門淵江邊,就矗立著一座船舶制造工廠,為長江流域的客戶提供了質量過硬的各種型號船只,在湘鄂贛三省名氣很大。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與時代的變遷,船舶制造工廠搬到了新洲圍堤外江邊的新址。這個荊江大堤外的小洲,有20多平方公里,良田連片,風景如畫。在28年前,是一個將近兩萬人的行政區。當時我兼任那里的書記,走遍了整個圍堤及其內部的村莊,看遍了春花秋月,留下了很多感悟與觸動。我這次前來江邊新址,是要采訪湖北中游造船有限公司董事長何純章先生。何先生跟我20年前就相識了,但沒有過多深入的接觸。他曾任監利縣兩屆政協常委、縣工商聯副主席,現任政協委員,還是湖北省荊州市船舶焊工考試委員會常務副主任、湖北省船舶工業行業協會副理事長。他慈眉善目,中等身材,穿著灰色的休閑外套。見面后,他十分熱情地引導我在廠區里面轉,參觀正在同時開工的8艘貨駁工程項目。工地上一片火熱工作景象,只見200多號人(高峰時達到400多人)各司其職,一絲不茍。他詳實地跟我介紹這里的情況。他說起話來聲如洪鐘,表情堅毅,同時又面帶微笑,滿臉自信。看著他一臉神采飛揚的表情,我不禁想起了劉宋初年少年宗愨的故事。宗愨最大的志向是“愿乘長風破萬里浪”,這句話的意思是說,他要利用有利的條件,沖破一切阻力與困難,干一番偉大的事業。我覺得這句話用在何先生身上很適合。他聽后連連點頭,然后飽含深情地講述了自己往日拼搏進取的故事和對公司未來發展的美好愿景……
從木船到船廠的嬗變
民國肇建之后,中華大地上的老百姓沒過過一天安穩日子,不是軍閥混戰,便是外敵入侵。政府沒有能力管老百姓的衣食住行,老百姓要自己謀生活。
監利緊靠長江,在幾千年前就是云夢古澤的一角,經過地質演變,沼澤變成了膏腴之田,然而畢竟是水鄉,還是留下了星羅棋布的湖泊與河流。那時的橋還很少,路基本上沒有修。那么,水上運輸力量——船只便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何先生的父親就是眾多駕船者中的一個。在水上討生活的人,在岸上的日子沒有幾天,幾乎長年累月以船為家。船到哪里,家也就在哪里。這種生活雖然很苦,但好歹還可以解決一家人的溫飽問題,于是也就堅持了下來。新中國成立后,社會趨于穩定,他的父親駕船來到容城鎮,并在那里落籍安了家。
那時,社會上的主要交通運輸工具還是木船。他的父親主要跑內荊河、火把堤、福田、柳關等地的河流,一直到沙市。當時,要修武漢到沙市的這段公路,很多船只從別處運來筑路的石頭。他的父親繼續做著老本行。何先生于1955年在船上出生,可以說從人生的開始,便與水、船結下了不解之緣,并影響他之后的人生。或許是因為他的父親太知道駕船的苦楚,并不希望下一代繼續干這一行,因此很少傳授他駕船的方法。他從小只是摸過槳,沒有獨立駕過船,但在船上生活的時間多。到了進學堂的時候,父母送他讀小學、初中,早上送上岸,晚上到岸邊等他放學回到船上。
這樣簡單而又充實的生活一直持續到1969年。何先生看到家里沒有勞力,父母親駕船又很辛苦。兩個姐姐出嫁了,還有一個姐姐、一個弟弟在家,家庭的負擔很重。他為給家庭減輕負擔,毅然決定輟學跟隨父親護船、卸貨。
1970年,面臨長江、位于監利縣容城鎮一磯頭處的監利造船廠組建成立。1971年,何先生被招工到監利縣造船廠。當時當工人是一件很榮耀的事情,是很多農村青年夢寐以求的。他被分到航運公司下屬的機械修配廠,跟劉大學師傅學車工。那時沒有船塢,只能在露天的船臺上造船。船板被太陽曬到六十多度,在船艙里每做一個小時就必須出來換一口氣。有一些人根本吃不了這個苦,沒干多久就要辭工走人。何先生勸他們說:“你們還是堅持干下去,條條蛇都咬人,哪里有錢多又輕松的事呢?干下去,好歹還可以學一門技術。”但那些人對他的話嗤之以鼻:“技術?哼!冬天冷死,夏天熱死,我們可受不了這個罪!走了,走了!”他不像這些人拈輕怕重,而是勤奮工作、努力學習。因為他深知,吃苦只是暫時的。
造船的鋼板、鋼管全靠人抬,不像現在有龍門吊。何先生、劉大學等人下班回家,每天身上幾乎都被汗浸透了。他們心里也曾打過退堂鼓,但又想到既然選擇了這一行,就要干好,哪怕再苦再累都要堅持到底。
我漫步在老船廠的附近,已看不到半點實物了,僅有幾塊形態各異的大石頭,還沉睡在沙灘上,周圍都已經植上了草坪,在這里觀光游玩的人較多。我面對長江正在回憶有關老船廠的記憶,看到幾位老人在散步,連忙上前與他們搭訕。誰知幾位老者異口同聲地說:“還有沒有造船廠真不知道,但何純章這個人我們始終記得,他是一個有本事的人,也是監利造船的功臣,更是一條硬漢子……”
以改革謀發展的邏輯
監利縣造船廠原是國有企業,國家分配過來的大學生有八人之多,有上海交大的、哈軍工的、湖南大學的,等等。高精尖人才不斷充實船廠的技術隊伍,為船廠造出合格的船舶提供技術保障。何先生不放過任何一個提高自己的機會,與他們打成一片,謙虛地向他們學習,不斷提高自己的能力。1975年何先生榮升車間主任。也正是從這一年起,原本只能造木制機帆船的船廠,開始打制鋼制分節駁,制造鋼制貨輪。
何先生當車間主任手里管著三十幾號人,他待下屬很好,從來不會頤使氣指或者拉幫結派,而是把重心放在選擇用能人、提高技術能力上。俗話說:“人心齊,泰山移。”在集體生活中,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何先生要把這個團隊作用發揮到極致,所以展示領導應有的凝聚力非常重要,這樣才可以將大家擰成一股繩,將工作穩步推進,取得良好的成效。
由于工作特別突出,1982年,廠里調何先生到技術科工作,他不負眾望,工作卓有成效,再一次受到領導的賞識。1983年初,他被調到供應科當科長,后又被選調到住管科當副科長。1984年,他通過成人自考,獲得了武漢工業大學專科文憑,后又接受經委專班的學習,系統地學習了經濟管理、船舶等知識,為后續的事業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當時船廠是湖北省經委、六機部在地方上的定點廠,生產計劃物資,都是由六機部下達調撥的。在這樣的背景下,必須設辦事處在武漢,他作為船廠駐漢辦的代表在武漢利濟路住了6年。何先生發揮螺絲釘的精神,艱苦樸素,抵御外界聲色犬馬的誘惑,不亂花公家的一分錢,將這一工作做得有聲有色。
1989年,船廠進一步擴大生產,何先生再被調回廠任經營科科長,不久就被任命為副廠長。在上任8年后,1997年,他榮升為廠長。他出任廠長時,正值經濟改革進入深水期,按照國家政策,生產計劃與物資供應初步取消,全面進入市場經濟。船廠的情況非常不好,基本處于半停產狀況。廠里的雜草有一米多深,停產達14個月,賬上連一分錢都沒有,廠區的工人基本走光……如何收拾這個爛攤子呢?他先走訪了一些老船工。工人們說:“每個人都很現實,廠子爛成這樣了,又沒有錢,誰愿意繼續留下呢?家大口闊,沒有錢怎么維持?船廠既然沒有事干,只有出門打工了。”他聽了這些話,心里雖然很難過,但渡過難關的決心更強了!他毅然決然地說:“我要盡最大的力量恢復生產,扭轉局面!”
怎樣起步?如何恢復生產?這些都需要弄錢。何先生點起煤油燈召集班子成員籌錢,他拿出了找親戚借的幾千元,與其他人一起湊了將近2萬元。在生產上開工沒有回頭箭,沒法又只好將廠子的一輛小汽車賣了,作為周轉的經費。但還是不能滿足購買材料與開工工資的需要。
船廠依然舉步維艱,連意志堅定的他都想打退堂鼓了,他建議領導去另請高人,但領導對他寄予厚望,無數次地勸說他,做他的工作。他經過反復的考慮,也出于對這個船廠的感情,不愿意看著這個廠破產,于是繼續鼓起奮斗的勇氣。他的一些朋友聽說他答應盤活船廠,紛紛來勸說:“你不要弄了。別人都沒有搞好。你搞得好?拖欠了幾十萬元的工資,還欠外邊近百萬的債,就算你是一個神仙,都無可奈何啊。”但何先生咬定青山不放松,堅持自己的初心。他堅信有上級的支持,有班子成員的團結拼搏,有工人的大力支持,盤活船廠就有希望。
首要任務是要找米下鍋,爭取生產項目。他最先找到了時任荊州市水利局長的老領導易光曙,懇求市水利部門把一些搶險救災的船,優先讓他們船廠造。老領導支持了他,當時這些船的造價只有二三十萬元,賺不賺錢是一回事,關鍵是穩住人心,讓工人們看到曙光。何先生毫不猶豫地接下了訂單,并按照設計要求,精益求精,并進行多項技術創新,做到質優價廉,贏得了業界的一致好評。
俗話說:“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罷艱險又出發。”好的開頭,使他們業務開拓面大大增加。何先生回憶起當時的情況,唏噓不已。他說:“為了找業務,江西、湖南到處跑。住不起好的賓館,就住每晚十二元的雙人間。有一次一個領導接待我們,問住哪里?我們只說住蠻遠,不敢說住的具體地方。要是說了地方,領導如果提出去看我們,那就出了丑,領導會看不起我們,就不會拿業務給我們做了。”艱難困苦,玉汝于成。何先生就是這樣邁著堅定的步伐,一路走過來了。
剛把船廠恢復生產,正要創新發展的時候,1997、1998年特大洪水把廠區淹沒了。船廠完全停產,幾乎沒有辦法生存了。但何先生絕不服輸,要拼命干。他寫了300多封求救信,寄給行業各級部門的主管領導與交通部。最后交通部領導作出批示,轉給湖北省交通廳。由交通廳下撥給船廠60萬元,作為企業生產的啟動資金。上級有關領導明確指出:“這筆錢,你們不能用于還賬、發工資,要先用在生產上。”他馬不停蹄地去省里辦手續,借了一輛破車趕路,卻不料在毛嘴出了車禍,好在幾個人傷得并不重,他們輕傷不下火線,在醫院小住幾天后,就又拼命地工作了。他們將這筆錢用在擴大生產上,又建起了一座碼頭。
“艱難方顯勇毅,磨礪始得玉成。”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他們船廠的名聲大振。荊州管轄范圍內的一些縣、市及周邊一些業主紛紛前來購買船只。造船廠煥發了活力,簽訂了很多訂單。3年內把拖欠工人的工資還完了,把有關外債還完了。企業走上了良性發展的軌道。
歲月如梭,轉眼到了2003年,監利縣政府對工業、企業開始改制。船廠是監利縣十六家企業改制中的第一批。當時的政策,在企業改制上,凡是擔任過企業一把手的,是可以安排新的單位與工作去任職的。但何先生沒有想另攀高技而是聽從領導的勸說“跟著企業下海去闖一闖”,心懷“大我”,放棄了“小我”。
船廠在企業改制領導小組的指揮下,積極配合,改制成功,成立了湖北省荊江造船有限公司。船廠改制是以300多萬的價格轉讓給何先生等人(他們是股份制,20多個中層干部都入股了)。但其中就有200多萬的債務。接手后,何先生及其團隊經過大膽創新,抓住機遇快速發展。很快,就顯示了改革成效,讓大家吃了定心丸。大家堅定了工作的信心,表示將加倍努力快速起航。改制恢復生產不久,在一次行業比武會時,全縣的交通行業都來觀摩。船廠取得了好成績,他在會上發言時飽含深情,講得眼淚流出來了,表示要克服諸多困難,發揚“愚公移山”的精神,努力拼搏。讓船廠充滿活力,讓業務量迅速遞增,讓效益逐年提高,讓影響更加深遠,讓技術不斷提升,誓與長江共生死。他還說:“改制以后,我有飯吃,大家有飯吃。船廠的工作千頭萬緒,最關鍵是要激發工人師傅們的積極性,將每項工作做到極致,為船廠贏得好口碑!那樣的話,不愁沒有事干,不愁沒有飯吃!”
他自豪地說:“把一個破爛的船廠盤下來,一般人是不敢接手的。但是我們做到了。當時如果我們下不了決心接手,現在便沒有什么船廠了。目前,監利的造船業在整個荊州是龍頭。荊州有上百艘的大噸位船,不說建造船,光是維修船這種業務的范圍就很大。如果我們的船廠倒閉了,船壞了,別人就只能跑到宜昌、跑到武漢、跑到湖南等地去修理。路遠了,花費自然更大。”他的一些做法與想法,還是很獨到的,有一種大視野、大格局的家國情懷,不得不使人佩服。
由事業向人格的升華
成功改制后,企業活了,名氣大了,訂單多了,幾乎忙不過來了。他多次利用一些場合給工人師傅們打氣,號召他們忘我工作,保質保量完成生產任務,“現在的所有榮譽、成績都是你們努力取得的。越干越好,越好越干。船廠興旺,大家都有事干,有飯吃。我不僅要讓你們有飯吃,還要讓你們吃好”。
轉眼到了2016年。縣經委派人來宣傳《河道管理法》,并指出凡在長江外灘上的企業必須搬家,要確保荊江大堤的安全,確保洪水來時可以暢通運行。3月中旬,有關領導來廠里傳達上級精神,講了船廠必須搬遷的政策。接著工作專班成立,開始督促搬家事宜。但“搬家”不是兒戲,倘使運轉起來,也不可能像一床被子卷起來便走,這可是一座船廠啊!談何容易!要是急迫去搬,阻力很大,難度很大。
一些客戶聽說船廠搬家,怕影響他們的造船時間和質量,本想給船廠的業務也不給了,船廠業務受到影響。剛好,長江委員會船舶制造公開招標,何先生他們精心準備后,中標了。甲方指定他們到咸寧的一個水庫邊上造船。為了搶進度,保持工期,何先生日夜操勞。一天晚上在造船工地上巡查,不小心踩空,從高高的碼頭上掉下來,結果將肋骨摔斷,肩椎摔“炸”,頭摔破,腰椎摔碎,腿也摔斷了。同事發現后將他送往醫院,在醫院住了一百多天。住院期間他還是放心不下工地的事務,拄著拐棍堅持到現場親自指揮,解決一個又一個的難題,最終這艘船提前完工。
真正“搬家”是在2017年。在外灘拆遷指揮部的決策下,于新洲子堤外——就是現在這個地方,劃了線。由于組織實施搬家,被迫停產,丟掉了大量的業務,耽誤了大量的時間,導致有些股東不理解,大家都埋怨將船廠從城區“燈紅酒綠”的地方,搬到偏僻荒涼的地方。幾個股東認為,搬家是死路一條。搬這個家就把剛上升的業務又毀掉了,把人氣也搞沒了,把人心也拆散了。有的工人說:“我們在這里做慣了,上下班,回去也方便,搬到遠處,住在廠里,一個月難得回去幾次,多不方便呵!”但何先生毫不動搖,只是耐心勸導:“兄弟們,你們的心情,我都理解。其實我比你們更不愿意搬。但這是國家的政策,搬走了,對國家有好處。而且政府又不是不給地方讓我們繼續干。在個人的得失面前,我們必須讓位于集體、國家的利益。這一次吃一點虧,到新地方就會有新局面。只要我老何在,絕對不會虧待你們,抓住機遇,重整旗鼓,快速發展!”股東們、工人們聽后,慢慢想通了,積極配合,遷廠搬家順利開展了。
何先生因摔傷沒有痊愈,在搬家中,是拄著拐棍組織工人開始“運作”,并邊建邊生產的。他言出必行,體諒下屬、帶頭吃苦,凡事深思熟慮,防止意外的發生。賬上錢不多了,全部家當搬運過來有幾十公里,談何容易。
兩臺龍門吊像兩座大山,特別是那個大龍門吊,光一根梁,就有80噸,三十幾米長。陸路上根本走不了,只能走水運。他讓人扶著帶領一群工人排除萬難,分批搬運,想法子把梁運走了。怎么弄的呢?他們把一千五百噸的船拉上坡,再用吊機把梁吊到船上,最后把船搞到河里去。運到新址后,再把船拉上來,拉上來又請大吊機把它吊起來。邊拉邊挪邊遷的時候,他親自帶頭用撬桿撬,不小心把小腿傷了一個洞。他不愿意在醫務室花費時間,醫生幫他敷了膏子,他跛著腿又堅持到現場指揮。終于,這些龐然大物被“鎮”下來了,龍門吊安全運達目的地。
夢想為舟,奮斗作槳。他像拓荒牛一樣,帶領著工人們在新洲江灘上開荒造廠,費盡了無數心思與心血。他以廠為家,遷廠搬家后有四個新年都是在廠里過的。剛來時,就在沙灘扎帳篷,風吹日曬;沒有水、沒有電、沒有路、沒有人煙,點的是蠟燭(有時打火把),吃的是焦糊飯,喝的是長江水(夏天的水要沉淀,冬天的水自己抽上來消毒食用),后來買來柴油機發電。遷了一次廠,何先生瘦了十多斤,脫了一層皮。頭被長江的大風吹了以后經常犯疼,天氣一冷便要戴厚厚的棉帽。有些年輕的新工人,他們吃不了苦,偷偷溜了。一些老工人也有些動搖了。他察覺出苗頭,對他們說:“寂寞、荒涼只是一時的,堅持下去,在這里扎根了,幾年以后就是一個現代化的工廠,將會比老廠還要好很多!”工人們聽后,很信服他的人品與人格,因為他從不放空炮,他用行動證明了他就是“像牛一樣勞動,像土地一樣奉獻”。
夏天蚊子特別多,咬得人渾身是包,癢得人心煩意亂。老伴開始很不理解他的做法,多次勸他不要干了,回家去安享晚年。他的脾氣很倔,根本聽不進去,他說:“我不干了,這個船廠就垮掉了。”老伴見他不開竅,便回娘家不理睬他了。后來老伴見他拼死拼活地在操勞,慢慢也理解了,回到他身邊,做飯洗衣,解除他的后顧之憂。何先生的事業之所以如此成功,與這一位賢內助是分不開的。他曾動情地說:“我的這個老伴,話不多,但很會關心人。有她在,我可以一心一意去造船了,不必擔心柴米油鹽醬醋茶。”
還有一對老搭檔楊永和、鄭國平,也是緊緊跟隨他、支持他的。特別是楊永和,與何先生共事三十幾年,感情很深。他對筆者說:“我們的何總做事,總是搶著第一個干重活、累活、險活,關心下屬,事必躬親,在我們心目中地位很高。工人們過生日,都會給他們加幾碗菜,表達廠里的心意。工會組織活動,聯絡工人情感。何總對家人、親戚、朋友都很真誠、和藹,不喜歡說虛偽的話,不去做欺世盜名的事。我跟何總干了幾十年,事先他都和我商量,特別注重培養人才,是我敬佩的好領導和老師!”
采訪接近尾聲時,何先生告訴我:“到目前為止,國家通過對長江沿線造船企業的治理后,原荊州地區只有兩家船廠了——監利一家、公安一家。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應付船舶的整個維修,是很重要而又煩瑣的工作。船舶跟汽車一樣,每隔6年就要核檢。不一定是大修,但是必須檢查船舶的方方面面。如果你的船平時維護得好,時間久了也必須上岸,到船廠船塢里檢查。船廠存在,對于船舶的維護是有一些便利的。但是現在通過長江整治,船廠數量越來越少了。這就是困難與機遇并存。生產的資質是湖北省軍民聯合辦發放的,在地方只是取得營業執照。所以說,這個船廠是半個軍工企業。上面要求船廠轉型升級,高檔次地提升,其中包括企業的人員設備、設施、信息化、生產流程,等等,都要提升,進一步規范。近期在枝江開會,上面要求我們把提升的步伐加快,這樣一來,就會有大量的投入,這對我們船廠的壓力很大。”
他又說:“但我們有信心做好,鐵人王進喜不是說過:‘人無壓力輕飄飄,有了壓力步步高。但有些問題還是不能解決。譬如我們船廠的高級工程師,沒有達到規定的限數。但是人才不是用錢買來的。比如一個高級工程師,來我們這里,只掛一個名,光給檢查單位看本子是不行的,必須立足長遠,培養永久的高精尖人才。我一生撲在船廠的事業上,嘔心瀝血幾十年,有人打趣說我完全可以評個高級工程師。但我到哪里評?找誰評?過去有機會錯過了,盡管我精通船廠的各項業務,但理論考試不過關呀。我要抓住機遇與挑戰,不惜一切代價引進人才,培養人才。”
他喝了一口茶,又接著說:“古今中外,很多干大事的人,有的都快80歲了,還在競爭、奮斗,還求上進。我還只有65歲,還可以干15年。其實,說為了賺多少錢,這不是根本目的。我覺得監利不能沒有造船重工業,現在留下‘火種,奮力趕超行業老大。目前我們的船廠業務靠前,稅收在監利市20名之列。我有信心、有決心,力爭把監利的這個船廠經營下去,繼續做大做強。現階段要新增加浮船塢,一旦發生了水面事故,它是一個應急裝備。如果一艘船裝了貨,在半路發生了碰撞,馬上要沉了,船老大可以直接上我們的塢,我們幫他拖起來。這個浮船塢就是一種應急載體。前幾年‘東方之星出事,當時要是有一個浮船塢的話,在船還沒完全沉下去的時候,趕快組織救援,也許情況會好一些。”
他說完露出了很欣慰的表情說:“我們船廠跟重慶大學合作制造環保型的船舶,包括電力船、小型燒氣船。這種環保船,不用柴油,全用電力或者液化氣。早在2014年就做過水上燒氣船。這種船加LNG氣,跟加天然氣一樣。壓縮后的LNG氣的一個立方相當于天然氣的六百倍。一千噸位的船,裝四個立方,它可以跑一千公里再加氣。因為最開始國家推廣新能源船,LNG船是邊做邊生產,所以相關的法律法規是逐步完善的。”
他跟船與長江玩了幾十年,沒有什么特別的愛好,主要時間都待在工廠,看龍門吊、看生產景象、看長江往返的一些船只,然后看哪個船是他造的。他連做夢都有大船夢。在他的計劃當中,還要造大船,造出高質量的船。他對造船質量要求很高,每天都親自上船查看圖紙、檢查工藝流程及質量。某一年,有一個新來的人燒電焊,鋼板接縫處燒得不均勻,他責令刮掉重新燒。他對工人們說:“船是在水里跑的,要是漏水怎么辦?生命安全第一,信譽第一。”
他還是一個胸中有大愛的人。在老廠區的時候,助力公益事業捐款助學近兩萬元,幫助農民扶貧致富在三萬元以上。來到新廠區后,去看望三閭村的幾個貧困戶,捐了四千元。在2020年初,新冠病毒肆虐的時候,他捐了一萬元現金給監利縣慈善總會。近兩年,何總先后兩次去新溝鎮雷河村扶貧,共捐善款二萬六千元。
寫到這里,我看到了船廠已經在朝精細化方向走去,必定前途光明。船廠在他手里,多次瀕臨險境,然而他就像船上的舵手一樣,使之轉危為安,讓事業從低谷到高峰,獲得了成功和榮譽。正是古人所謂:“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韌不拔之志。”
時光的表盤上,總有一些耀眼的時刻,標注著奮斗的進程。這些文字只是粗略地描畫了他奮斗的人生軌跡。而要說的話題很多,三天三夜也說不完,要講的故事與經歷十萬字都寫不完。
告別時,我又看到了高大的龍門吊,又想起了那句話“愿乘長風破萬里浪”。是呀,船廠生產了長江上第一艘采金挖沙船;在1991年湖北省縣級船廠中,是第一個建造5000噸級沿海貨輪的;在1993年湖北省縣級船廠中,第一個為香港大輝實業有限公司建造出了163.8英尺的出口船舶;2007年出廠了1600M3絞式挖泥船。歷年來,這些優良船只,深得客戶喜愛,訂貨不斷,產品銷往香港、廣東、福建、江蘇、浙江、山東等十多個省區,贏得了客戶的一致好評。我仿佛在朦朧的江面上,見到了精神抖擻的何先生,他挺立船首,揮舞著旗幟,在大浪中揚帆前進!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這句話是對何先生一路奮進的人生歷程的最好詮釋。同時我也為何先生俯首甘為孺子牛的人格魅力深深感動。衷心祝愿何純章先生與湖北中游造船有限公司快速發展,造福于監利,揚名于湖北乃至全國!
(責任編輯:孫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