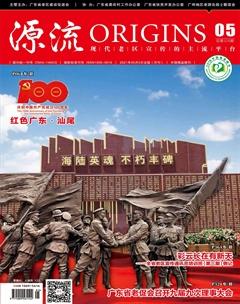海豐紅宮和一個(gè)講解員的故事
梁軍 施培養(yǎng)


海豐的夏夜,街道分外璀璨。紅的海洋蜿蜒數(shù)里,熱烈喜氣的中國紅代表紅色政權(quán),金黃色則象征吉祥豐收,整條文化街與彭湃烈士設(shè)計(jì)的紅黃相間的紅場(chǎng)大門相為呼應(yīng)、融為一體,襯托出紅宮紅場(chǎng)獨(dú)一無二的歷史地位。
紅宮原為建于明代的海豐學(xué)宮,1927年11月18日至21日在這里召開縣工農(nóng)兵蘇維埃代表大會(huì),成立海豐蘇維埃政府。會(huì)場(chǎng)四周和街道墻壁都刷成紅色,會(huì)場(chǎng)內(nèi)用紅布覆蓋墻壁,因此把學(xué)宮改稱“紅宮”。此后,革命政權(quán)的許多重要會(huì)議都在這里召開。
紅宮東側(cè)的紅場(chǎng)舊址,原為“東倉埔”,占地22000多平方米。海豐蘇維埃政權(quán)成立后,彭湃同志號(hào)召在此地興建紅場(chǎng)大門和司令臺(tái)。大門門額上浮塑“紅場(chǎng)”二個(gè)大字,兩邊浮塑“鏟除封建勢(shì)力,實(shí)行土地革命”的對(duì)聯(lián),紅場(chǎng)中央設(shè)有傳聲臺(tái)。
紅宮的大成殿室內(nèi)墻上懸掛的馬列像,還有那一排排擺放整齊的矮凳。在這里,紅色的墻壁,紅色的柱子,紅色的屋脊,這里依然彌漫著當(dāng)年的紅色氣氛。
大成殿的一面旗幟尤其奪目,這面黨的旗幟,是我黨八七會(huì)議時(shí)期的旗幟,它的原件是國家一級(jí)保護(hù)文物。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旗幟就是鐮刀和斧頭還有一個(gè)星,鐮刀斧頭就是工農(nóng)聯(lián)盟,因?yàn)?927年黨的八七會(huì)議決定廢除了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以前國共合作是掛他們的旗幟,現(xiàn)在中國共產(chǎn)黨有了自己的旗幟,明確提出了工農(nóng)聯(lián)盟,鐮刀斧頭,星代表無產(chǎn)階級(jí)先鋒隊(duì)。
時(shí)間穿越回到那個(gè)烽火歲月,當(dāng)時(shí)的報(bào)刊是這樣報(bào)道的:“海豐各處農(nóng)民工人以及貧苦民眾……興高采烈……鼓樂喧天,較之舊歷新年的快樂,當(dāng)更快樂得數(shù)百倍,人人喜形于色,歡呼欲狂……到開代表會(huì)的那一天,更有番特別的情景,自會(huì)場(chǎng)以至各馬路以及各機(jī)關(guān),都是紅燈紅旗彩照耀滿目,而各馬路上的清潔齊整,均由民眾自動(dòng)的掃除得一塵不染,誠有天下升平萬民樂業(yè)的景象。”
每當(dāng)講起這段歷史,羅曉梅的眼眶總是浮現(xiàn)出淚光,這些介紹她已經(jīng)不記得重復(fù)過多少遍了。2000年擔(dān)任紀(jì)念館講解員以來,羅曉梅始終充滿熱情,把弘揚(yáng)彭湃精神、傳播紅色文化作為使命擔(dān)當(dāng),以過硬的解說功底、豐富的歷史學(xué)識(shí)、良好的形象氣質(zhì),不遺余力地向來自全國各地的賓客講述發(fā)生在海陸豐這塊紅色大地上的革命斗爭歷史,被評(píng)為“全國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shè)工作先進(jìn)工作者”。
一頭短發(fā),一身正裝,渾身透露出干練的氣質(zhì)。講起彭湃革命故事時(shí),她兩眼發(fā)光,嘴里滔滔不絕。這位出生在重慶的“辣妹子”總能引來不少游客聚精會(huì)神的目光。
當(dāng)紀(jì)念館舉辦業(yè)務(wù)培訓(xùn)時(shí),她反復(fù)觀看解說輔導(dǎo)錄像,光筆記就有幾十冊(cè)。“解說是活的語言藝術(shù)。”不僅要掌握好基本理論,還要有解說臨場(chǎng)感,培養(yǎng)場(chǎng)上定力。除了在工作中與同事演練切磋外,回到家后,其丈夫與小孩也被她拉來當(dāng)聽眾,請(qǐng)他們邊聽邊提意見。經(jīng)過一段時(shí)間的刻苦訓(xùn)練,她很快掌握了講解本領(lǐng),短短一年時(shí)間便成為了紀(jì)念館的講解骨干。
羅曉梅通過查閱全國各地的資料,對(duì)彭湃同志在中國革命斗爭史上的貢獻(xiàn)作了進(jìn)一步的創(chuàng)新性研究,獨(dú)立系統(tǒng)地編寫出紅宮紅場(chǎng)舊址、彭湃故居、得趣書室等多處紅色遺址的旅游版、詳細(xì)版講解詞,以及幾十萬字的多種類型的講座稿。此外,她還對(duì)現(xiàn)紅宮紅場(chǎng)、彭湃故居陳列的個(gè)別地方提出了自己的修改建議,積極開展“傳幫帶”,培育了一批“紅色文化小小講解員”,讓青少年走進(jìn)海陸豐革命歷史,接受愛國主義教育,讓海陸豐革命精神代代相傳。
“彭湃等革命先烈光輝的一生,涉及了軍事、教育、村官、農(nóng)村、金融等,我立志要做一名學(xué)者型講解員,就必須把上述這些涉及的方方面面都進(jìn)行深入了解,然后根據(jù)前來參觀的客人的不同身份和他們感興趣的內(nèi)容進(jìn)行不同角度的講解。”羅曉梅認(rèn)為,只有因人而異制定不同的講解內(nèi)容,才能讓彭湃精神和紅色文化從紀(jì)念館走向社會(huì),從書本走入大眾人心。
羅曉梅帶著我們走到佇立在紅場(chǎng)左邊的一面紀(jì)念墻時(shí),停下了腳步,紀(jì)念墻上是海陸豐革命烈士英名錄,一共是4883名烈士的名字。
“這是在戰(zhàn)爭時(shí)期犧牲在海陸豐大地的英烈,其實(shí)還有更多的沒有名字的無名英雄。”羅曉梅說,每次經(jīng)過這里,他們都在激勵(lì)著我前行,不敢由絲毫怠慢。“我是一名普通的海豐群眾,可我明白這份工作有很強(qiáng)的使命感和責(zé)任感,我不能讓烈士們的血白流。”
20年來,羅曉梅耳聞目睹了紅宮的變化。她高興地說:“現(xiàn)在來參觀的年輕人越來越多了,而且外地的干部群眾也絡(luò)繹不絕。”
海豐人對(duì)紅是情有獨(dú)鐘的,“紅”是文化、是精神、是靈魂,是紅色海陸豐的生命之紅、奮斗之紅、進(jìn)取之紅,它承載著海陸豐人民對(duì)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與追求。像紅城中學(xué)、紅城電影院、紅城大廈、紅城大道……紅宮紅場(chǎng)、紅花地水庫,赤坑、赤石、赤岸河,這一個(gè)個(gè)赤紅的名字是最好的見證。
這條有著特殊歷史意義的街道,是一條喚起海豐人民靈魂深處永恒記憶的街道,也是全國獨(dú)一無二的紅色文化街。這座曾經(jīng)有著“東方小莫斯科”之稱的城市,是一座歷經(jīng)腥風(fēng)血雨百年滄桑,仍屹立在東方之上的紅城。一條街復(fù)興了一座城,海豐之紅,正是中國之紅的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