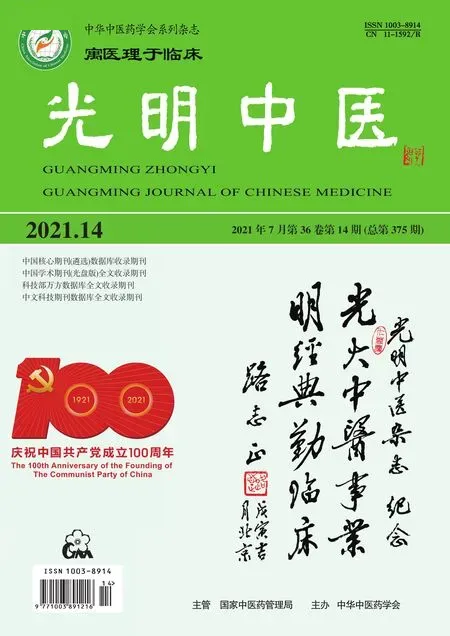基于中醫體質分析針灸治療周圍性面癱臨床療效及預后
戴麗娟 王淑蘭 王 會 張加英 徐炳國
中醫體質學研究推廣了“辨體-辨病-辨證”診療模式在臨床中的應用[1]。周圍性面癱,相當于西醫學的面神經炎,根據面神經不同的損傷部位表現出相應的臨床癥狀,針灸治療本病療效顯著,本研究試從中醫體質方向探討針灸治療周圍性面癱的臨床思路與方法。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選取 2018—2020 年南京醫科大學附屬南京醫院(南京市第一醫院)中醫針灸科門診就診符合診斷標準的患者314例。其中男性184例,女性130例;最大年齡84歲,最小年齡14歲,平均年齡(49.59±17.77)歲;左側面癱156例,右側面癱158例;最短病程1 d,最長病程90 d, 平均病程(4.36 ± 6.74) d。治療前面神經功能分級 House-Brackmann(H-B)量表[2]均在V級-VI級,即面肌無運動或僅有輕度可察覺運動,面部不對稱,眼不完全閉合,額部及口部無運動。
1.2 納入標準參考《針灸治療學》[3]中面癱的有關內容制定:①起病突然;②患側口眼歪斜為主要特點,可見一側面部表情肌癱瘓,同側額紋消失或變淺,不能皺眉、蹙額,眼瞼閉合不全或閉合乏力,鼻唇溝變淺或消失,口角歪向另一側,進食時食物停留于齒頰間,喝水漏水,不能吹口哨等;③符合《神經病學》[4]中面神經損傷節段在莖乳孔以外節段,即莖乳孔下段以外面神經損傷的臨床表現,不伴有味覺減退、聽覺過敏、耳部皰疹、頭暈等癥狀。
1.3 排除標準①所有病例癥狀體征或經CT、MRI等檢查,因中樞神經系統疾病、耳科疾病和外傷等引起的周圍性面癱;②雙側面癱患者;③妊娠期和產褥期女性;④病情危重,難以對治療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做出確切評價者;⑤不能堅持針灸治療,影響療效觀察者。
1.4 中醫體質依據2009 年中華中醫藥學會制定的《中醫體質分類與判定標準(ZYYXH/T157—2009)》制定的中醫體質量表實施[5],該量表由平和質、氣虛質、陽虛質、陰虛質、痰濕質、濕熱質、血瘀質、氣郁質和特稟質9個亞量表構成,共60個條目,各亞量表轉化分數為0~100分。對于同時具有2~3種體質傾向的患者,以“是”的轉化分最高者為標準。
1.5 中醫辨證依據陳氏[6]及患者臨床癥狀表現分為以下證型:①風寒外襲型。伴有畏風無汗,多有受涼吹風病史,舌淡紅苔薄白,脈浮緊或浮緩。②肝郁氣滯型。伴有情志抑郁,善太息,胸脅脹滿,舌質暗,苔薄白,脈弦。③脾虛濕盛型。伴有脘腹脹滿,渴不欲飲,肢體困重,舌淡邊有齒痕,苔白膩,脈濡數。④正氣不足型。伴有少氣懶言,頭暈目弦,舌淡紅,苔薄白,脈沉細弱。
1.6 治療方法
1.6.1 針灸取穴依據本科室臨床經驗取穴:①患側頭維、陽白、瞳子髎、顴髎、迎香、地倉、頰車、夾承漿、雙合谷;②眼針取肺和上焦區;③牽正或翳風穴;④隨癥加減,倦怠乏力加足三里,情志不舒加太沖,脘悶不適加豐隆等。
1.6.2 刺灸方法①面部及四肢部穴位選用佳健牌0.3 mm×25 mm一次性針灸針,發病一周內進針3~5 mm,平補平瀉;發病一周后予稍強刺激,并于針刺后接6805-D電針儀,選連續波,頻率2 Hz,強度以患者耐受為度。②眼部穴位選用 0.2 mm×15 mm一次性針灸針,緊靠眼眶的穴位直刺3~5 mm,不提插,不捻轉,操作結束后按壓針孔3 min,以防出血。③牽正或翳風穴用灸法,選用佳健牌艾灸條兩支,溫和灸30 min,以患者局部皮膚潮紅,深部組織發熱為度,隨時吹掉灸條艾灰,保持艾條紅火狀態,依據患者耐受程度,調整施灸距離。濕熱質及陰虛質不采用。④超過2個療程未愈加用穴位注射,用1 ml一次性無菌使用注射器(山東威高集團醫用高分子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制造),抽取甲鈷胺注射液1 ml(由日本衛材株式會社制造,衛材中國藥業有限公司分裝,國藥準字J20130076),直刺入穴1.5~2 cm,患者有酸脹感,回抽無血液后,慢慢推入藥物0.5 ml左右,以患者有明顯酸脹感為度。⑤每次留針30 min,針后面部閃罐8~10次,每日1次,每周5次,10次為一個療程,每個療程結束后休息5 d,再進行下一療程,共統計3個療程。
1.7 觀察指標①比較不同中醫體質各組臨床療效即治愈、好轉、有效、無效例數及痊愈率。 ②比較不同中醫辨證各組臨床療效即治愈、好轉、有效、無效例數及痊愈率。③比較不同中醫體質患者痊愈療程。④分析不同中醫體質患者無效因素。
1.8 療效評定標準參照面神經功能分級 House-Brackmann(H-B)量表制定。痊愈:所有區域面肌功能正常(H-BI級)。顯效:仔細觀察閉眼時有輕度減弱,額紋基本對稱,口部可有輕度不對稱(H-BII級)。有效:有明顯的功能減弱但雙側無損害性不對稱(H-BIII級)。無效:面部表情肌靜止時不對稱,上額無運動,眼不能完全閉合,口僅有輕微運動(H-BIV-V級)。

2 結果
2.1 不同中醫體質各組臨床療效比較本研究中共收入病例314例,各組治療前 H-B 量表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其中平和質(33.4%)、氣虛質(16.2%)、陽虛質(14.6%)及痰濕質(13.4%)占比較多,治療后痊愈率比較χ2=19.539 (P<0.05),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其中氣郁質(8.0%)、濕熱質(6.1%)、陰虛質(4.1%)、瘀血質(2.6%)及特稟質(1.6%),占比較少,未進行統計。見表1。

表1 不同中醫體質各組臨床療效比較 (例,%)
2.2 不同中醫辨證各組臨床療效比較本研究中共收入病例314例,各組治療前 H-B 量表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其中風寒外襲型(40.5%)、肝郁氣滯型(21.3%)、脾虛濕盛型(19.8%)及正氣不足型(18.5%)。各組治療后痊愈率比較χ2=14.658(P<0.05),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見表2。

表2 不同中醫辨證各組臨床療效比較 (例,%)
2.3 不同中醫體質患者痊愈療程比較本研究中共收入病例314例,其中平和質、氣虛質、陽虛質及痰濕質共244例,各組治療前 H-B 量表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各組治療后痊愈患者所需療程比較F=12.399(P<0.05), 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見表3。

表3 不同中醫體質患者痊愈療程比較 (例,
2.4 不同中醫體質患者無效病例本研究中共收入病例314例,臨床治療無效病例11例,占比3.5%,其中氣虛質1例,陽虛質2例,痰濕質及濕熱質各4例,病例數較少,暫未統計。
3 討論
中醫體質學說是中醫辨證論治體系的一部分,以傳統中醫理論為主導,研究不同體質特征、體質類型的生理及病理特點,在此基礎上分析不同體質對疾病的反應狀態、病變特質及發展預后,從而指導疾病預防及治療的學說[7]。體質與證本質上不同卻又密不可分。體質是證形成的基礎,決定個體對某些疾病的易感性或易罹性,體質既秉承于先天,又關系于后天[8]。故而在疾病的臨床研究過程中,“辨體-辨病-辨證”的診療模式能夠更精確地反映中醫理論對疾病個體的整體認識,從而提高臨床防病治病的能力。

中醫體質學認為不同類型的體質決定了不同個體對某些病因、疾病的特殊易感性和病理過程的傾向性[12]。因此治療上不僅注重調節人體整體機能,更重視個體間體質的差異性[13]。本研究中“辨體”結果提示平和質、氣虛質、陽虛質及痰濕質是周圍性面癱的主要體質影響因素。其中平和質之人為臟腑功能狀態良好的一種體質狀態,陰陽平和,臟腑氣血功能正常,抵御外邪能力較強,患病后恢復速度也較快,多因衛外失固,感受風寒而發為面癱,同時與其他各組比較臨床治愈率高,所需治療療程最短;氣虛體質之人正氣不足,自我調節能力與對抗外邪能力較弱的一種身體素質表現,因為絡脈空虛,風邪入中而發為面癱;陽虛質之人陽氣不足,而致形寒肢冷等癥狀為主要表現的體質,因為溫陽之力不足,感受寒邪發為面癱;痰濕質是由于津液運化失司而痰濕凝聚,以重濁黏滯為主要特征的一種病理體質狀態,素有痰濕,風夾痰邪上擾,阻滯經絡而致面癱。因此在治療過程中針對體質不同選用相應的治療方法,可以縮短療程,提高臨床疾病治愈率。“辨證”結果提示風寒外襲證型占比最多,肝郁氣滯證型、脾虛濕盛證型及正氣不足證型例數相當,其中外感風寒證型治愈率最高,多因外感之邪,病位較淺,針對治療后較易痊愈;正氣不足證型治愈率最低,由于氣血陰陽不足,濡養功能差,故而恢復較慢。臨床治療無效病例分析,以痰濕質及濕熱質例數為多,《溫病條辨》有言:“濕為陰邪,其傷人之陽也,得理之正,故多而常見”。《素問·五運行大論》認為:“其性靜兼,其德為濡”。濕性帶有隱匿性、相兼性,其性重濁、黏滯,有來緩去遲的特點,被濕邪所傷病程長,在轉歸過程中會因時、因人、因兼而變,易成痰兼瘀夾熱,濕、痰、瘀、熱互結[14]。認識到濕性與臨床治療無效的相關性,在治療過程中應當以健脾祛濕、清熱化瘀為治則,配用相應的穴位及刺灸方法,或可進一步提高臨床治愈率。
在本病的臨床治療中,辨體論治與辨證論治相結合,既著眼于面癱所引起的臨床癥狀表現,又不忽視患者不同體質的特異性,因病、因證、因體制宜的治療方案,更有助于縮短療程,提高臨床療效,進一步發揮針灸的優勢[15];同時在診療過程中,讓面癱患者了解自己的中醫體質,參與整體治療過程,更愿意配合調整生活方式,糾正偏頗體質的不當影響,會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推而廣之,“辨體-辨病-辨證”的診療模式,能讓臨床醫師預判疾病的療程和預后,更有利于疾病的康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