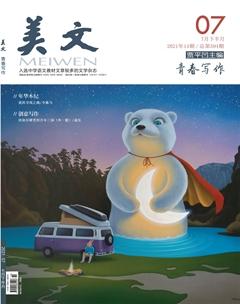余華講中高考作文,沒什么大驚小怪的
何殊我
一、罵文學是時尚
今年三月,作家余華為某教培機構的發布會站臺,進行了一場“如何在中高考中寫好作文”為主題的發言。然后被某知名大V在微博貼出現場圖片,配文“文學已死”,遂輿情洶涌。“寫出了《活著》的著名作家都要出來討生活,盜版害死人,文學確實不能養活人了”“有一種數學家教你做奧數題的感覺”“他老缺錢了還是怎么著”……
緊接著,各種解讀文章出來,觀點無非是嘲諷余華和文學或者嘲弄當下的教育。除了宣泄情緒,對于解決問題于事無補。文學在社會生活中,經常呈現一種吊詭的跡象,誠然很多人對其大有敬畏之心,但有更多人對其是輕慢的、不重視的。大眾眼中,文學似乎是路邊的道旁樹,凈化空氣遮風擋雨的時候很容易被忽略,但是走過路過的人隨意踹兩腳卻容易得很。經常有剛認得幾個字的人,就開始對文學、作家群體橫挑鼻子豎挑眼,諾獎加身都得考慮一下接不接。每次熱點,都是這種認知的應激反應而已,如果不跟風罵兩句,似乎不夠時尚。
首先我要給余華辯護一下,他只是一個功成名就的作家,并不是天上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仙,作家要出作品,不能脫離生活,發布會站臺,也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在我們這個巨大的人情社會,總有抹不開面子的時候。脫離這兩點來指摘,是無的放矢。
余華一直與中小學文學教育保持著密切關系,現在還是北京師范大學的特聘教授,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對中高考寫作發言沒有什么可指摘的。以余華曾經兩次高考落榜為依據,對其進行指責也是非常牽強的,高考每年都有巨大的變化,試問當年的高考評分標準放在今天還能行得通嗎?
余華也解釋了為何會講這個內容,他很早就開始參與作文競賽做評委,跟很多語文老師有共事的經歷,所以對中小學生寫作還是有發言權的。余華提到的作文大賽,就是新概念了。余華曾經長期擔任新概念的評委,當年擔任新概念大賽組委會總干事的李其綱曾在書中回憶了余華還曾經針對一篇文章的評審與其他評委激烈爭執,最終促成了新概念歷史上的“終審法院”的誕生。
二、作家如何文以載道
對余華講中高考作文的輿論熱點,要么是數落當下文學的不堪,要么是嘲弄當下教育的扭曲之處,對于事情本身并無可行性建議。在當下這個泛娛樂化的社會,文學應該如何與教育和大眾互動?
影視大發展,票房不斷創出新高;網絡文學的發展,讓寫作的門檻不斷降低;短視頻娛樂的流行,創意策劃人才奇缺……似乎文學的影響力是無所不在的,然而在泛娛樂化的大潮下,這些只能稱作跟文學相關的職業,在他們的生活工作場景下,文學的工具化屬性得到最大的發揮。
我們要討論的文學,可以用老祖宗們所定義的“文以載道”來表征一下。這幾個字幾千年來一直影響著中國的文脈,特別是經歷了魏晉六朝的奢靡文風以后,讓文能夠和道發生關系,且弘揚道統,是唐宋以來歷代文人們孜孜以求的事情。道,在儒釋道汗牛充棟的著作中都有繁復的定義和演繹,歸結起來,無外乎人的生活、工作中要遵循的社會道義,且此道義要與社會互動。文以載道,文學是“載”的重要形式。
韓愈、柳宗元、周敦頤到近代的俞樾等歷代文人賢士,無論他們是搞哪門學問的,都寫得一手好文章,不少作品在今天讀來仍煌煌其言,今天這些文章更是國人學習語文繞不過去的高山峻嶺。
著書立說之外,為了讓“道”暢通且不“空載”,先賢們可謂是操碎了心。首先,他們不約而同地非常關注教育發展,提倡學風、創辦或者主持書院是不少人的人生標配,如韓愈在潮州拿出薪俸辦學、蘇軾在海南勸學、朱熹修復并主持白鹿書院、俞樾主持紫陽書院、蘅塘退士編選唐詩三百首等,“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合破天荒。”
除了辦學,還要寫文諄諄教導,《師說》《進學解》《送東陽馬生序》這一點從不少文章名字就能看出來,“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每位先賢的命運都不太好,做官不順,常遭貶謫,但是他們無一不是苦口婆心講述“載”的重要性,真真應了李克勤所唱的“命運就算顛沛流離,命運就算曲折離奇,命運就算恐嚇著你,做人沒趣味,別流淚心酸,更不應舍棄”。
那么,余華作為一代知名作家和大學教授,一個關于中高考作文的簡短講座成為輿論熱點,探其根本,不過是社會分工帶來的錯位。文學在現代人的頭腦中雖具有超越現實的作用,可以寄托人格和理想,但對作家群體的認知,越來越呈現出一種兩極分化的態度。
現代作家們不能像古先賢們那樣,相對輕松地游走在政學兩界,在廟堂和江湖都能身體力行“文以載道”。現代社會日益精細的分工下,作家越來越具備職業特質,尤其是隨著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的爆炸式發展,寫作也逐步被拆解為各種技術操作,講出吸引人的故事成為最受歡迎的寫作特質,寫故事收費或者進行影視改編,成為寫作者的最大追求,寫作或者說文學的載道作用不斷被邊緣化。所以一旦作家介入現實生活,立馬會招致非議。
三、作家們,多多講出來吧
近現代社會的情境下,作家并非與中小學教育完全隔絕。葉圣陶、豐子愷等人小說家、畫家、教育家的多重身份,就拿本世紀前二十年興盛的各類中小學文學競賽來說,往往都有陣容非常豪華的作家站臺,他們不光是出席活動拍照留影那么簡單,還要命題、解題且對獲獎文章進行點評,并且再與獲獎學生們進行互動。拋開升學、收費的利益驅動因素,這些或大或小的賽事,在參與其中的作家群體們的操刀下,也確實在普及文學理念、發掘文學新人等方面嘗試頗多,也在一定程度上豐富著中國文壇和社會文化的多樣性。可以說,文學賽事是文學家們“載道”的一個不錯的出口。
近年來隨著教改的步伐不斷加速,在政策要求下,不準收費、不準與升學掛鉤、實行備案制,讓原有的文學賽事逐漸失卻了光環,對家長學生的吸引力大不如昔。但與此同時,伴隨著全國采用同一套部編版語文教材和語文學科考核的權重增加,又為教培市場打開了新世界的窗口,語文培訓成了資本全力奔跑的新賽道。
一時間,各家巨頭和新涌現的玩家紛紛加碼語文培訓,想方設法邀請學術機構、名家給自家業務站臺就有了更大的需求。瀏覽新聞,不難發現,或大或小的機構都會以各種形式為自己的業務增加權威性——砸重金與學術機構合作,邀約名家擔任顧問、講師、出席活動。但是這些合作的背后,是否與業務調性能耦合在一起,且真正讓家長、學生受益,難說。
在線教育這兩年的無序化競爭,背后資本重金砸廣告做市場的策略,也讓事情在起著新變化。教育原本是慢工出細活的,文學原本也是慢的,語文學習的提分難度也很大。市場炒作的短期行為就容易高發,博眼球、制造話題,只要能引來流量,一切都不重要。
就拿余華這次講中高考作文來說,一同站臺的還有劉擎、樊登,發布會的主題是“中高考沖刺——四大專家獻計2021中高考的高端輔導家長會”。每位嘉賓的演講不到二十分鐘,扣題按照角色講了中高考的建議并且非常生硬地做了廣告。這種推介業務的品牌發布會,如此短的時間,是很難談明白問題的。由于其他嘉賓的發言都是政策、行業角度提出的立論,都是大而全的觀點,很難有水花。所以,這個事情本身就是一個品牌公關活動,為了制造話題而生,大眾的熱議,不過是落入主辦方的彀中而已。
四、作家們,請多多地講學生寫作
余華的身份和議題,再加上文學的低門檻,一下子就出圈成為熱點。中考、高考是兩個截然不同的考試形態,放在一起對比簡直荒腔走板。結果,余華招致非議,不斷升溫的輿論將余華推上風口浪尖,熱度蓋過了余華正在宣傳期的新作《文城》。輿論熱議、流量高企,教培公司坐收漁利,在微信推文中還不忘一句“他現身指導中高考作文寫作技巧,在全網引發了一場討論熱潮”,喜不自勝。
這后面,還有一個深層次的問題:文學和教育的割裂。文學的法則是面向成人世界的,教育的根本功用是面向下一代的。原本需要兼顧二者的語文教育,在日常教學中,往往成為照本宣科的工具。教與學都面臨困境的情況下,應付考試就成為了最大的需求。
一旦脫離學習環境,語文素養就成了難題。當下嚴肅文學式微,入眼可見的都是不忍卒讀的新媒體文章、流量影視、網絡文學大行其道,暫且不說其思想價值和藝術成就,大部分文字連基本的行文措辭都不通順,“奶頭樂”式的東西閱讀起來沒什么障礙,卻難逃垃圾宿命。這背后,折射出的就是語文教育的缺失。
從該角度來說,余華講中高考作文的行為,也是在“載道”,只不過呢,活動的商業意味太過濃重,遮蔽了“道”的光彩。在現在這么一個萬物都能上熱搜的時代,文學圈也需要警覺一下,有點品牌意識,然后應該讓更多的“余華”站出來,在合適的場合大聲地講、多多地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