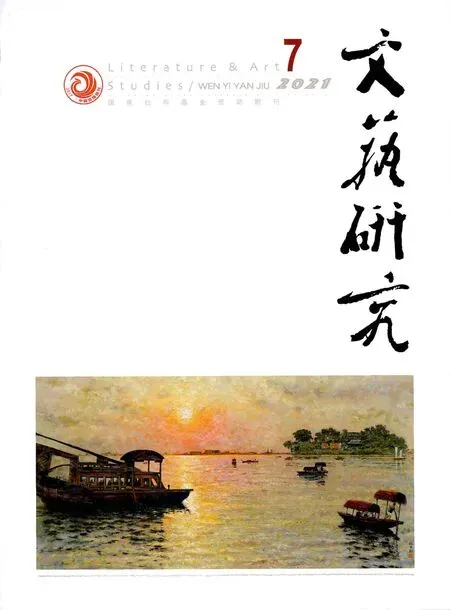知識與技藝:明儒歌法考
胡 琦
詩樂離合或者更廣范地說文學(xué)與音樂的關(guān)系,乃中國文學(xué)史上一絕大問題。雖然詩樂合一之理歷來為人熟知,但面對古樂失傳的無奈,文人學(xué)者不得不望洋興嘆。明代李東陽《懷麓堂詩話》云:“古詩歌之聲調(diào)節(jié)奏不傳久矣。比嘗聽人歌《關(guān)雎》《鹿鳴》諸詩,不過以四字平引為長聲,無甚高下緩急之節(jié),意古之人不徒爾也。”①李氏質(zhì)疑當(dāng)時(shí)人之歌《詩》不合古義,涉及的正是詩歌文本如何轉(zhuǎn)化為歌唱實(shí)踐的問題。
事實(shí)上,在復(fù)古思潮下,明代儒者對詩歌的音樂性尤為重視②,當(dāng)時(shí)出現(xiàn)了通過文獻(xiàn)考索、理論闡釋、吟唱實(shí)踐等方式重構(gòu)“古歌法”的潮流③,這在古代文藝?yán)碚撌泛驮姌肺幕飞隙际且粋€(gè)值得注意的現(xiàn)象。這些論述往往散見于經(jīng)學(xué)注疏、理學(xué)語錄或孔廟祭祀文獻(xiàn)中,雖然資料較前代為多,但學(xué)界關(guān)注尚不充分④,其理論淵源、傳承流布以及與詩辭文本的配合關(guān)系等,都有待梳理和研究。歌詩之法的探討可以從三個(gè)層面展開:一是詩辭的語言聲調(diào)屬性,此系詩律學(xué)研究范疇,主要通過平仄、陰陽等聲韻學(xué)術(shù)語加以分析⑤;二是音高和旋律,此是樂律學(xué)、音樂史研究的焦點(diǎn),可以利用律呂譜、工尺譜等技術(shù)手段進(jìn)行記載⑥;三是文字轉(zhuǎn)化為人聲時(shí)行腔用氣的種種方式,屬于聲樂研究的范疇,現(xiàn)有研究主要討論唐宋以降的詞曲演唱及佛道唱頌,對儒家傳統(tǒng)內(nèi)部的歌唱理論關(guān)注較少,對有關(guān)術(shù)語、概念的解釋也很不充分⑦。本文主要從第三個(gè)層面著眼,考論明儒之歌法,然并非從聲樂理論的角度分析、評騭明人構(gòu)擬的古歌法,而是希望回到當(dāng)時(shí)的思維世界中,關(guān)注這些歌法是在何種知識譜系中得以成立,與儒學(xué)觀念又是如何相互影響的。
一、從經(jīng)解到歌法:宋明以來對《禮記》“七聲”之重構(gòu)
古人關(guān)注歌法的觀念基礎(chǔ)是儒學(xué)內(nèi)部以詩樂為教的傳統(tǒng)。《尚書·舜典》所載“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⑧,是儒家論樂的核心文獻(xiàn)。對此經(jīng)文的闡釋,也成為學(xué)者討論歌法的起點(diǎn)。“永”之本義是“長”,孔傳釋為:“歌詠其義以長其言。”⑨而朱熹解《尚書》,便不滿足于單純以“長”為說:“既形于言,則必有長短之節(jié),故曰‘歌永言’。既有長短,則必有高下清濁之殊,故曰‘聲依永’。”⑩與此相應(yīng),他批評南宋趙彥肅所傳、號稱“開元遺聲”的《風(fēng)雅拾貳詩譜》“一聲葉一字”?太過單調(diào)。李東陽認(rèn)為“平引長聲”的唱法缺乏“高下緩急之節(jié)”,思路正淵源于此。開元遺聲既不足據(jù),學(xué)者自然要上溯先秦經(jīng)典,尋找古歌法的文獻(xiàn)依據(jù),其最要者莫過于《禮記·樂記》對上古歌法的描述:“歌者,上如抗,下如隊(duì),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累累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處描述了“上”“下”“曲”“止”“倨”“句(勾)”“累累”七種歌唱的情形,或可概括為七種聲容。從經(jīng)學(xué)傳統(tǒng)看,對《禮記》此段經(jīng)文的詮釋,早期是以情感為中心。鄭玄注云“言歌聲之著,動人心之審,如有此事”;孔穎達(dá)正義解釋為“言聲音感動于人,令人心想形狀如此”,例如“上如抗”是“歌聲上饗,感動人意,使之如似抗舉也”,“下如隊(duì)”是“音聲下響,感動人意,如似隊(duì)落之下也”,“句中鉤”是“音聲大屈曲,感動人心,如中當(dāng)于鉤也”,等等?,乃是將七種狀態(tài)的描述都理解為歌聲對人產(chǎn)生感動效果的比喻。而宋人則多從聲音本身性質(zhì)層面理解,如衛(wèi)湜《禮記集說》引嚴(yán)陵方氏(北宋方愨)曰:
抗言聲之發(fā)揚(yáng);隊(duì)言聲之重濁;曲言其回轉(zhuǎn)而齊也;止言其闋后而定也。倨則不動,不動者方之體,故中矩,言其聲之常如此。句則不直,不直者,曲之體,故中鉤,言其聲之變?nèi)绱恕@劾酆酰云渎曄嘞祵伲巳缲炛椋云浣K始兩端相貫而各有成也。?
方氏此說,為吳澄《禮記纂言》所采納?;胡廣等編《禮記集說大全》,亦將此段解讀為歌聲之形貌?。可見由“聲”而非“心想”的角度解讀,乃是宋元以降經(jīng)學(xué)中闡釋“上如抗”等七者的趨向。從內(nèi)在情感轉(zhuǎn)向外在形式,便開啟了從技法角度解讀《禮記》歌法的可能。有學(xué)者嘗試從當(dāng)時(shí)歌唱實(shí)踐出發(fā),以今證古:如北宋沈括談到“聲中無字”之唱法,便援引《禮記》為證,認(rèn)為此法“轉(zhuǎn)換處無磊磈”,“古人謂之如貫珠,今謂之善過度是也”?。南宋張炎將慢曲演唱中“大頓”“小頓”“大住”“小住”“打掯”等手法與《禮記》“七聲”對照?。明代唐順之亦將宋以來詞曲演唱中“折聲”“掣聲”“反聲”“丁聲”與《禮記》“七聲”相對照?。這些解說主要以當(dāng)時(shí)的演唱技術(shù)為中心,并未對《禮記》描述的古歌法做出全面的復(fù)原。
明代中期以后,文人士大夫中興起探討古樂、撰著樂書的潮流?。在此背景下,以“七聲”為綱目建構(gòu)歌法,漸漸形成一個(gè)傳統(tǒng),并由經(jīng)典解釋衍生出曲線式的歌譜符號系統(tǒng)。成書于弘治十年(1497)以前的李文利《大樂律呂考注》?,在引述《禮記》“歌者上如抗……足之蹈之也”一段原文后,有按語云:
按,抗,舉也,歌聲高者,如手舉物,雖高,不離于手。聲之下者,如物之隊(duì),隨其淺深而去,且無留滯也。蓋歌聲嫌太高,太高則不和矣,留滯則淫矣。曲,轉(zhuǎn)聲也,如折枝然,即轉(zhuǎn)得分明也。止,聲之定也,欲其如枯木嵯峨不揺漾也。倨,歌聲折轉(zhuǎn)者;中矩,欲其方也。句,歌聲周轉(zhuǎn)者;中鉤,欲其圓也。如抗、如隊(duì),純?nèi)缫玻蝗缯邸⑷玳拢壢缫玻恢芯亍⒅秀^,方圓也;累累貫珠,繹如也。此歌節(jié)奏之妙,和樂亦如之。?
李文利一方面將七種聲容分派入《論語》的“純?nèi)纭薄鞍壢纭薄袄[如”?,另一方面又提出“轉(zhuǎn)聲”的概念解釋“曲”“倨”“句”三者:“曲”是“轉(zhuǎn)得分明”,“倨”是“折轉(zhuǎn)”,“句”是“周轉(zhuǎn)”,情況各別。其后嘉靖十七年(1538),山西遼州同知李文察所著《樂記補(bǔ)說》對《禮記》“七聲”的解釋,則采用“過接”的概念:“倨,一字之過接也;句,一句之過接也;累累,自始至終皆如此過接不斷絕也。”?其著眼在聲、字關(guān)系,近于沈括之說,而與李文利之側(cè)重聲音本身不同,可見當(dāng)時(shí)學(xué)者詮釋《樂記》的不同傾向。
《大樂律呂考注》的“轉(zhuǎn)聲”之說,后來被發(fā)展成為一套較為實(shí)用的歌法。章潢《圖書編》(成書于萬歷五年,1577)和潘巒《文廟禮樂志》(成書于萬歷十年)都引述了一段“孫氏如皋”的歌法論,與沈括關(guān)于“聲中無字”、朱熹關(guān)于“疊字”“散聲”的論述并列。孫氏首述《禮記》“七聲”之經(jīng)文,復(fù)錄李文利《大樂律呂考注》“抗,舉也……中鉤,欲其圓也”一大段解說(僅個(gè)別字句略有出入),接著闡釋道:“此言歌詩有高有下,有作有止,有宛轉(zhuǎn)而曲者,有折轉(zhuǎn)廉隅而中矩者,有周轉(zhuǎn)圓滑而中規(guī)者,其永言中抑揚(yáng)節(jié)奏如此,且累累然如貫珠而不斷絕,以依其永也。歌聲之要,已上數(shù)言形容殆盡,毫無余蘊(yùn)。后學(xué)者不玩究其旨,如所謂宛轉(zhuǎn)、折轉(zhuǎn)、周轉(zhuǎn)(引者補(bǔ))之義,懵不能別,而徒以長言之,無所含蓄,即是念曲而已。烏足以語永言之妙哉!”?“孫氏如皋”疑即嘉靖、萬歷間學(xué)者、原籍如皋之孫應(yīng)鰲。據(jù)《明史·藝文志》及《四庫全書總目》,應(yīng)鰲著有《律呂分解》《律呂發(fā)明》?。《圖書編》亦嘗引“孫應(yīng)鰲《律呂分解發(fā)明》”之說?,惜孫著未見,或已失傳。孫氏將“上”“下”“曲”“止”“倨”“句”都概括為“永言中抑揚(yáng)節(jié)奏”,而“累累如貫珠”則是“依其永”,正是將《禮記》“七聲”與《尚書》的“永言”“依永”之說聯(lián)系起來。從術(shù)語的承遞上看,李文利以“轉(zhuǎn)聲”釋“曲”、“折轉(zhuǎn)”釋“倨”、“周轉(zhuǎn)”釋“句”;孫氏繼承其說,又將“曲”詮釋為“宛轉(zhuǎn)”,使得“轉(zhuǎn)聲”的術(shù)語系統(tǒng)更為周密。
此外,《圖書編》的編者章潢又自有一篇《歌法說》(圖1),將各種形態(tài)繪圖加以說明。他認(rèn)為“歌雖小道”,然“非師指授”則不易習(xí)學(xué),故“擬其形容,悉載前圖”,使“善學(xué)者”可以“細(xì)心尋繹”?。語言描述雖極其詳細(xì),仍不免有難于言傳之微妙;將文字術(shù)語轉(zhuǎn)化為圖像符號,無疑是一種更具象的展示方法。此《歌法圖》包含17個(gè)曲線符號,乃是對《禮記》“七聲”的進(jìn)一步細(xì)化和組合。例如,除了“上如抗”“下如隊(duì)”,圖中還添加了“漸漸向上者,聲外揚(yáng)也”和“微微向下者,聲漸低也”兩者,可以更細(xì)膩地摹狀發(fā)聲方法。圖中將不同聲容相互搭配,如符號①是“句”“貫珠”“倨”的組合,符號②是“倨”“貫珠”“曲”的組合。倘以一種曲線符號對應(yīng)歌中一字,自然便超越了單調(diào)的“一聲葉一字”。這種以曲折線條描繪的歌法,符號形式不同于律呂譜或工尺譜,性質(zhì)或與《漢書·藝文志》所記載的“聲曲折”?、道教《玉音法事》中所用的曲線譜?相近,都是用線條之轉(zhuǎn)折上下表示歌聲的變化。
降及清初,《大成通志》(成書于康熙八年,1669)和《太倉州儒學(xué)志》(成書于康熙四十二年)都收錄了一份當(dāng)時(shí)流傳的孔廟祭祀歌法,將曲線符號與樂歌結(jié)合起來。其文開頭先引孫氏論歌法之語(內(nèi)容與《圖書編》所錄基本相同,唯題作“孫繼皋曰”,恐是傳抄之訛),次用一套曲線符號標(biāo)識歌唱之法,如表1所示?:

圖1章潢《歌法圖》,選自《圖書編》卷一一五

表1《禮記》“七聲”系孔廟祭祀歌法符號
此法顯然屬于《禮記》“七聲”一系,在其基礎(chǔ)上又增加了“長聲”“短聲”“轉(zhuǎn)聲”,共為十種聲法。從形制上看,這些符號或淵于宋代俗字譜。其中表示“上”“下”“曲”“止”“倨”“句”“轉(zhuǎn)聲”的七個(gè)符號,在王驥德《曲律》抄錄自宋代《樂府渾成》的《娋聲譜》和《小品譜》中亦有出現(xiàn)?,學(xué)界一般解釋為工尺減字譜,用來記錄音階?。而此祭孔歌譜則是取其形而變其義,用以描繪歌聲的樣態(tài)。如“上”,歌譜釋為“上,謂出聲也……有從出字而抗,有從度下而抗,有從將收而抗,皆從喉中高揭之”;“曲”是“出字之后,轉(zhuǎn)聲而下,曲折有緒,輕款和靜”;“倨”意為“其聲平出之后,逆折而上,復(fù)持滿而下”?:都是圍繞“字”表現(xiàn)聲音的轉(zhuǎn)折變化。如迎神歌譜:
大(句、長)哉(句、長)孔(下、長、轉(zhuǎn))圣(上、長、止),道(句、轉(zhuǎn))德(下、長)尊(句、轉(zhuǎn)、上)崇(句)。
維(句、上、轉(zhuǎn))持(句、長、曲)王(下、轉(zhuǎn))化(句),斯(句、長、曲、曲)民(句)是(曲、下)宗(句、止)。
典(句、轉(zhuǎn))祀(上、下)有(句、轉(zhuǎn)、曲)常(句、短),精(上、轉(zhuǎn)、累累、累累)純(句、轉(zhuǎn)、累累、累累、累累、累累)并(下)隆(下、止)。
神(句、轉(zhuǎn)、累累、累累)其(句、轉(zhuǎn))來(句)格(上),于(句、轉(zhuǎn))昭(句)圣(上、轉(zhuǎn))容(句、止)。?
此譜中使用頻率最高的是“句”聲,譜中解釋為“此平出聲也,其聲委蛇平吐而有余韻,如鉤之圓滿而長也”?,全詩32字中使用21次(約占66%),乃是最基本的歌法。“句”聲多作一字的開頭聲,之后再配合其他聲法;“長聲”“短聲”“轉(zhuǎn)聲”和“曲”等多作一字之尾音;“止”則多作一句之尾音。此歌譜中對字、聲關(guān)系的處理,顯然以一字多聲為原則,多者一字六聲,寡者一聲、二聲,聲之多者,往往以“累累”聲接二連三構(gòu)成,轉(zhuǎn)折上下的聲音在旋律上也必然包含多個(gè)音階,不限于“一聲葉一字”,自然能更充分地表現(xiàn)歌唱之美。
二、“四氣”與“九聲”:心學(xué)工夫與歌詩之法
在《禮記》“七聲”一系歌法外,明代儒者中另一種影響甚大的歌法,當(dāng)推陽明心學(xué)一系的“四氣—九聲”之法。在王學(xué)的理念中,歌詩不僅具有廟學(xué)中釋菜、釋奠以及鄉(xiāng)射禮等活動的儀式功能,更是儒者修養(yǎng)自身的重要工夫?。陽明歌法之具體內(nèi)容,其弟子所記《稽山承語》稱:“歌詩之法……‘歌永言,聲依永’而已,其節(jié)奏抑揚(yáng),自然與四時(shí)之?dāng)⑾嗪稀!?王畿《華陽明倫堂會語》(成書于萬歷三年)也曾提到陽明歌法以“春夏秋冬”為節(jié)目:
《禮記》所載“如抗”“如墜”“如槁木”“貫珠”,即古歌法。后世不知所養(yǎng),故歌法不傳。至陽明先師,始發(fā)其秘,以春夏秋冬、生長收藏四義,開發(fā)收閉,為按歌之節(jié),傳諸海內(nèi),學(xué)者始知古人命歌之意。?
王畿以《禮記》所載為“古歌法”,而王陽明的“春夏秋冬”四義,則是對古歌之意的重新發(fā)現(xiàn)。然四時(shí)之義如何演為歌唱節(jié)奏,此處言之較簡。詹景鳳在成書于萬歷十八年的《詹氏性理小辨》中,有更為詳細(xì)的解說:
近日王文成以己意教人歌,如四句詩,首句聲微重,象春;次重,以象夏;次稍輕,以象秋;次又輕,以象冬。第四句歌竟,則余音聯(lián)續(xù)不斷,復(fù)將第四句賡歌,微重,以象春起冬盡。恐古所謂聲歌,意不出此也。?
此云“以己意”,點(diǎn)出陽明歌法重構(gòu)“古”法的特質(zhì)。此法主要以“四句詩”為單位,按“微重—重—稍輕—輕—微重”的強(qiáng)弱變化,以吟唱配合整首詩的章法結(jié)構(gòu)。詹氏之前,徽州休寧縣教諭姚坤所編的《刪定射禮直指》(成書于萬歷五年)也記述了類似歌法,用于演唱《采蘩》:“首一句悠揚(yáng)暢達(dá)(取春之意),第二句發(fā)揚(yáng)雄浩(取夏之意),第三句輕清舒緩(取秋之意),第四句上二字舒緩(取冬之意),下二字發(fā)揚(yáng)(取貞下起元意)。”?雖未明言出于陽明,然大旨正相吻合,唯于末句用先舒后揚(yáng)的方法表達(dá)冬去春來,不用重復(fù)賡歌,用意相同而技法小異。相比于《禮記》一系歌法的每個(gè)字轉(zhuǎn)聲,王學(xué)歌法對聲容的描述并不復(fù)雜,其關(guān)注的層面是整首詩的起承轉(zhuǎn)合而非具體的吐字。以四時(shí)為歌法的思路或有更早的淵源。清初毛奇齡云:“宋有一字分四時(shí)歌法,啟口如春,謂甲坼也;縱口如夏,謂恢臺也;收口如秋,謂揫斂也;合口如冬,謂閉必藏也;南渡后儒者言歌法必本此,第其言不知所始。”?以季節(jié)之序比擬發(fā)音之開閉翕張,正為陽明歌法之先聲;不過,“一字分四時(shí)歌法”是對單字吐字的音節(jié)細(xì)分,陽明歌法則是就詩句而言的,內(nèi)涵并不相同。
與王畿、詹景鳳、姚坤等人記述的歌法相類,提倡“三教合一”的林兆恩也有一套本于四時(shí)的歌法,見于《歌學(xué)解》(成書于嘉靖四十四年?)。其法以七言絕句為例,整首詩四句是一個(gè)四時(shí)序列,各句之內(nèi)又自成兩個(gè)四時(shí)序列:
總一章四句,分作春夏秋冬:第一句春,第二句夏,第三句秋,第四句冬。每句上四字,各分作春夏秋冬:第一字春,第二字夏,第三字秋,第四字冬……下三字稍仿上四字,亦分作春夏秋冬。?
林氏歌法對詩歌文句做了很細(xì)致的切分,春夏秋冬的線索從句與句之間貫穿到字與字之間。歌譜以“二字一斷”為基本節(jié)奏單位,庶幾不至急促;每句以“四三”分作兩節(jié),各為一輪四時(shí)。林氏還要求第三句“首二字稍續(xù)上句,末三字各平分,不甚疾遲輕重”,蓋此句不押韻,地位與他句有別;而象征“冬”的第四句在“閉藏已極”之后,末三字“當(dāng)有一陽來復(fù)之義”,尤其第五字要以高聲振起,“發(fā)其坤中不絕之微陽”。《歌學(xué)解》以林氏自作《醒心絕句》之一為例,以歌譜的形式呈現(xiàn)其法,對每個(gè)字的發(fā)聲方法皆有交代,如春是“口略開”、夏是“口開”、秋是“聲在喉”、冬是“聲歸丹田”等,可見其所謂“四時(shí)”,本質(zhì)上又可以歸結(jié)為吐納運(yùn)氣之法?。林氏《歌學(xué)解》撰述時(shí)間在陽明身后,但又早于王畿等人的記述,或系接聞陽明之論而加以細(xì)化者。
林兆恩《歌學(xué)解》的譜法,后又被《虞山書院志》(成書于萬歷三十五年)所載的《歌法》繼承。志中稱之為“四氣”歌法,謂出于王陽明,其歌譜形式、術(shù)語及解說文字皆與林氏相同?,當(dāng)有共同的文獻(xiàn)來源。而“四氣”之外,該志又載有一套“九聲”歌法,以“平”“舒”“折”“悠”“發(fā)”“揚(yáng)”“串”“嘆”“振”九字為目,雖然術(shù)語符號各別,但其內(nèi)涵實(shí)際上與“四氣”完全一致。圖2所示即為王陽明《詠良知》一詩的“九聲”譜和“四氣”譜,用于書院講會,下面略作對比。

圖2虞山書院歌法“九聲半篇”和“四氣半篇”,選自《虞山書院志》卷四
首先,兩種歌法都將七言詩按“四三”節(jié)奏劃分,“九聲”法更以“○”標(biāo)出兩字一個(gè)的節(jié)奏停頓,這種節(jié)奏安排正與近體詩的平仄規(guī)律相吻合。根據(jù)歌譜后所附解釋,“九聲”中有“機(jī)主于出”和“機(jī)主于入”兩類,“平”“舒”“發(fā)”“揚(yáng)”皆屬出氣,“折”“悠”皆屬入氣;如七言之“仄仄|平平|仄仄平”,以“平舒|折悠|平折悠”歌之,出氣、入氣的轉(zhuǎn)換點(diǎn)大致可以對應(yīng)平聲、仄聲的轉(zhuǎn)換節(jié)點(diǎn)。當(dāng)然,出入與平仄的對應(yīng)并不固定。如《詠良知》系仄起平收,志中“鄉(xiāng)約”部分收錄的通俗訓(xùn)諭歌《教訓(xùn)子孫詩》“人家成敗在兒孫,敗子多緣犢愛深”是平起平收,也同樣使用“平舒|折悠|平折悠,發(fā)揚(yáng)|折悠|平折串”歌之。其次,“九聲”與“四氣”的術(shù)語基本上可以對應(yīng)。如以“平”/“發(fā)”、“舒”/“揚(yáng)”對應(yīng)春、夏;“折”“悠”對應(yīng)秋、冬;“九聲”法中將末句第五字標(biāo)為“振”,“四氣”法中也特別說明此字“振其坤中不絕之微陽”。最后,篇章過渡方面,“九聲”法用“串—串串”三聲連綴,“四氣”法亦云第三句“首二字稍續(xù)前句”。凡此種種,皆說明兩法因承密切,對詩歌的處理高度一致,可以視為同一歌法理論在不同術(shù)語系統(tǒng)中的表達(dá)。其小異者,“九聲”譜配合了鐘、鼓、磬等樂器,且在七絕第四句后重唱末句一次,七律則重唱尾聯(lián)一次,此為“四氣”法所無,但合于詹景鳳“復(fù)將第四句賡歌”的記述,亦當(dāng)有所本?。
《虞山書院志》稱“九聲”“四氣”都是“陽明先生法”,后在“射儀”部分又用“九聲”法標(biāo)注射禮所用《采蘩》詩之歌譜,注云“白沙先生歌法”?。然陽明語錄及其弟子記述,言及歌法處均僅云“春夏秋冬”,并未提到“九聲”之說;陳白沙生平著述中亦未發(fā)現(xiàn)關(guān)于“九聲”的記載?。從現(xiàn)有的文獻(xiàn)證據(jù)看,完備、系統(tǒng)的“九聲”法是否為白沙、陽明所作,仍當(dāng)存疑。不過可以確定的是,以春夏秋冬為基本原理的歌詩之法,為陽明及其后學(xué)所提倡,在明代中期以后頗為流行,并且衍生出“四氣”和“九聲”兩種不同的符號系統(tǒng),為儒者講會、祭典中的歌詩活動提供了實(shí)用的技術(shù)指南。據(jù)《虞山書院志》記載,講會中歌宋明儒之近體詩、射禮中歌《詩經(jīng)》,乃至鄉(xiāng)約儀式中歌通俗的七言詩歌,都采用這一套歌法演唱?。
三、清初儒者對“九聲”與“七聲”的整合
“七聲”和“四氣—九聲”兩系歌法在理論淵源、技法細(xì)節(jié)等方面固然相異,但在基本理念上也不乏相通之處。從表述形式上看,由“四氣”到“九聲”,其術(shù)語系統(tǒng)由四時(shí)循環(huán)變?yōu)榘醋謽?biāo)聲,便更接近“七聲”一系。從歌詠實(shí)踐上看,兩系歌法對詩辭文本的處理也時(shí)或不約而同。如“七聲”系的祭孔歌譜往往以“句”聲起首,“九聲”法則多以“平”聲肇始,二者皆為平出優(yōu)柔圓滿之音,大體上可以互相對應(yīng)。又如,祭孔歌譜中雖未明確以“串”聲連綴篇章,但在詩句之間實(shí)際上亦往往緊接兩個(gè)“句”聲作為過渡。例如初獻(xiàn)歌譜:“惟師神明(句),度(句、轉(zhuǎn)、長)越前圣。粢帛具成(句),禮(句、上、轉(zhuǎn))容斯稱。黍稷非馨(句),惟(句、長、轉(zhuǎn))神之聽。”〔51〕同一行的上句末字和下句首字皆用“句”聲過接。這大概是詩句間的承接關(guān)系在歌法中的自然反映。緣乎此,這兩系歌法在明清之際又為儒者進(jìn)一步整合,徽州學(xué)者胡淵所述之歌法即其代表。胡淵字蕊明,號匏更,明諸生,鼎革后絕意仕進(jìn),講學(xué)于歙縣紫陽、休寧還古諸書院〔52〕。乾隆初年所修《還古書院志》中保存有他講學(xué)時(shí)所用歌譜及其所作的《歌法解》。志云:
歌之所由來也遠(yuǎn)已……第古今異宜,昔日之音響節(jié)奏,今人未易曉。故我匏更胡先生,精深古學(xué),講道紫陽、還古兩書院,作《歌法解》,與諸君子訂定歌譜、鼓譜以教童子,俾每歲春秋釋菜講學(xué),用以成禮,是有以裨于講席也。〔53〕
胡氏之歌法,凡標(biāo)十二目:“平”“句”“舒”“抗”“悠”“曲”“倨”“嘆”“隊(duì)”“串”“振”“節(jié)”。不難看出,此法正是組合陽明系“九聲”和《禮記》“七聲”,刪繁撮要而得。其于“九聲”中直接取用“平”“舒”“悠”“嘆”“串”“振”六者(未取“折”“發(fā)”“揚(yáng)”);“七聲”中直接取用“抗”“隊(duì)”“曲”“句”“倨”五者,又將“止”改為“節(jié)”(“節(jié)者,其聲已定,其氣已足,氣收聲止,有如枯木不搖漾也”),“累累”化入“串”(“串者,其聲遞隊(duì)上之末音、聯(lián)下二音,其氣累累如貫珠也”)。對諸聲的解釋文字,也多有與《虞山書院志》《圖書編·歌法述》相類者〔54〕。考其歌譜,所列詩歌有《詩經(jīng)》四言詩和理學(xué)家七絕兩大類。七絕歌法中,以“平舒折悠平折悠,抗抗折悠平抗串。串串平舒折悠嘆,平舒折悠振折悠,(疊唱末句)隊(duì)隊(duì)折悠平折節(jié)”演唱朱熹的《觀書有感》,安排實(shí)與“九聲”法大同小異:其中沒有使用“曲”“倨”“句”三聲,反倒多出了十二目中沒有的“折”,正可見胡淵歌法在七絕部分,除了加入“抗”“隊(duì)”“節(jié)”以豐富聲情,大體上還是繼承了“九聲”法的演繹方式〔55〕。
胡氏“十二聲”的用武之地,主要是《詩經(jīng)》諸篇,包括:《淇澳》三章,章九句;《鹿鳴》取首章,凡八句;《伐木》取首章,凡十二句;《天保》取第五章,凡六句;《有臺》取首章和第三章,各六句;《思齊》取第三章,凡四句;《抑》取第七章,凡十句(以上句數(shù)皆不計(jì)疊唱)。這些詩篇章句結(jié)構(gòu)比較復(fù)雜,正好為聲情模式的變化提供施展的空間。如《鹿鳴》首章之歌法:
呦(平)呦(平)鹿(句)鳴(平), 食(句)野(平)之(舒)蘋(舒)。
我(句舒)有(舒)嘉(抗)賓(抗悠), 鼓(曲)瑟(平)吹(舒)笙(悠)。
吹(句)笙(平)鼓(曲)簧(悠), 承(倨)筐(平悠)是(嘆)將(嘆)。
人(隊(duì))之(平)好(句悠)我(句串), 示(串)我(串)周(振)行(悠)。
人(隊(duì))之(平)好(句平)我(串), 示(串)我(串)周(振)行(節(jié))。〔56〕
胡淵歌法在篇章整體結(jié)構(gòu)上繼承了“九聲”歌法的安排。其一,全詩結(jié)尾疊唱“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兩句,即陽明賡歌之意。其二,此法亦使用“串”“嘆”“振”之聲實(shí)現(xiàn)篇章中的起承轉(zhuǎn)合,如“承筐是將”的“是將”用“嘆”法,呈現(xiàn)“蕭條剝落,遺音微渺”的效果〔57〕;最末“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兩句之間用“串”法接續(xù),“周”字又用“振”法振起。這種模式在其他詩篇中亦有應(yīng)用。如《抑》第七章凡十句,歌法于最末五句“無曰不顯,莫予云(嘆)覯(嘆)!神之格思,不可度思(串),矧(串)可(串)射(振)思”,以“嘆”“振”為抑揚(yáng),“串”聲為接續(xù),又疊唱“不可度思,矧可射思”一次。較短的篇章,如《思齊》第五章凡四句,歌法于三、四句“古之人無斁(嘆),譽(yù)(隊(duì))髦(串)斯(振)士”用“嘆”“振”,又賡歌“譽(yù)髦斯士”一遍〔58〕。
在吐字方面,胡淵歌法融入了許多“七聲”系的“轉(zhuǎn)聲”,塑造了篇中大量的聲情轉(zhuǎn)折,其中尤以“句”法使用最為頻繁,且與其他聲法相搭配。如上引《鹿鳴》首章,便使用了“倨”(1次)、“曲”(2次)、“句”(7次)等聲法,且有“句悠”“句平”“句舒”“句串”等組合。概言之,此法于每個(gè)歌章均先“平”起,以“句”“曲”“倨”三種“轉(zhuǎn)聲”豐富聲調(diào)之變化,結(jié)尾再用“串”法為接續(xù),用“嘆”“振”法為抑揚(yáng),并疊唱以卒章。
胡淵不但在歌譜中綜合使用“九聲”“七聲”兩個(gè)傳統(tǒng),而且在理論闡釋上也有意為之調(diào)和。《歌法解》在定義諸聲時(shí),特意都從聲容、用氣兩個(gè)方面描述。如“句者,其聲周轉(zhuǎn),其氣自抑而揚(yáng)”,“曲者,其聲宛轉(zhuǎn),其氣自若抑若揚(yáng)”,“倨者,其聲折轉(zhuǎn),其氣自揚(yáng)而抑”,等等〔59〕,皆是用氣之抑揚(yáng)分析聲之轉(zhuǎn)變。《歌法解》又將“十二聲”派入春夏秋冬:
其平、其舒,如春之蠢;其抗、其悠,如夏之巨;其嘆、其隊(duì),如秋之揫;其振、其節(jié),如冬之處。其曲、其倨,夏而之秋;其句、其串,春冬之與緒也。所以成陰陽之交,造化乎搏挽之音也。〔60〕
由此可見胡氏有意整合“九聲”與“七聲”兩派歌法為一整體的系統(tǒng)。不僅如此,他更雄心勃勃地欲將律呂知識也納入歌法系統(tǒng),將“十二聲”與十二律呂對應(yīng),如表2所示〔61〕:

表2胡淵《歌法解》“十二聲”與十二律呂對應(yīng)表
這一對應(yīng)關(guān)系,似乎比附的色彩比較重,恐未必能真正用于歌唱。例如,在此系統(tǒng)中,聲之高者“抗”位于仲呂,聲之下者“隊(duì)”反而在更高的無射,似有次序顛倒之嫌。朱載堉《律呂精義》所構(gòu)擬的“上如抗”,其最高音在清太簇〔62〕;李之藻《頖宮禮樂疏·協(xié)律歌譜》構(gòu)擬了數(shù)種“上如抗”,最高音或在清黃鐘,或在南呂〔63〕,從律呂高下上看,都比《歌法解》合理。如果說綰合“四氣”與“九聲”“七聲”,將用氣的出入抑揚(yáng)與發(fā)聲的高下平折相關(guān)聯(lián),還有一定的合理因素,那么將“聲氣”與“律呂”相對應(yīng),在理據(jù)上就顯得不足。不過,這種“牽強(qiáng)”的對應(yīng)關(guān)系,正可以說明其調(diào)和異說、力求整齊的潛在意圖。
相比之下,康熙間李塨對古詩歌法的構(gòu)擬,同樣是整合“九聲”“七聲”以成,但沒有刻意追求術(shù)語的整齊。其《小學(xué)稽業(yè)》載《詩經(jīng)·周頌·酌》之歌法,包括“平”“徐”“發(fā)”“揚(yáng)”“嘆”“句”“矩”“折”“轉(zhuǎn)”“串”“過”“上”“隊(duì)”“止”“永”“收”〔64〕。《酌》詩句式參差,且不用韻〔65〕,相對于四言為主、用韻齊整的詩篇,節(jié)律頗不好把握。李塨對其歌法的構(gòu)擬,先用點(diǎn)號(、)點(diǎn)出其“板”(強(qiáng)拍),規(guī)劃節(jié)奏。而在諸聲的運(yùn)用方面,則以“平”聲最為常見;各句多以“平”聲領(lǐng)起,經(jīng)過上下轉(zhuǎn)折變化,最后以“止”“收”“永”等聲收結(jié)。句間連接之聲,除了“串”,還有“轉(zhuǎn)”;句內(nèi)連接,則有“過”聲。李塨批評“前儒律呂諸書及文廟樂,一字一音,或一字首尾共幾音,字字如一,無清濁、無高下、無疾徐、無節(jié)奏,則從古未有是歌、未有是樂也”,故他在節(jié)奏安排、高下轉(zhuǎn)折上頗費(fèi)經(jīng)營。李氏自道其擬譜之旨云:“古歌樂失傳,不得已,妄效《樂記》‘上如抗,下如隊(duì),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累累乎端如貫珠’之言,及《唐樂笛子譜》,明陳白沙、王陽明歌詩法,臆撰如右。歌用宮調(diào)五聲、七聲皆可。”〔66〕在此,李塨非常清楚地交代了其歌法構(gòu)擬的知識資源。其中《唐樂笛子譜》即《唐樂篴字譜》,系明代朱權(quán)所纂,李氏當(dāng)?shù)弥诿纨g〔67〕;而所謂從《樂記》、陳白沙、王陽明所得者,應(yīng)是上文所述的“七聲”“九聲”兩種歌法系統(tǒng)。與胡淵類似,李塨也綜合使用兩系術(shù)語;同時(shí)他提及旋律問題,認(rèn)為用宮商角徵羽五聲,或是再加上變宮、變徵皆可,這表明歌法與樂調(diào)本身是相對獨(dú)立的,并不必將歌法之某聲對應(yīng)律呂之某聲。這也正反映了明儒“四氣—九聲”和“七聲”兩系歌法在整體上的取向。
結(jié) 語
明清儒者的歌法構(gòu)擬主要從兩個(gè)角度展開:“七聲”歌法以吐字為核心,展現(xiàn)聲容的曲折變化;“四氣—九聲”歌法,則以篇章結(jié)構(gòu)為指歸,關(guān)注氣息的出入運(yùn)行。二者的出發(fā)點(diǎn)和側(cè)重點(diǎn)雖有不同,但本質(zhì)上皆是人“聲”高下疾徐的表現(xiàn),以“氣”在喉口唇齒乃至丹田的運(yùn)行作為生理基礎(chǔ),屬于今人所謂“聲樂”的范疇,展現(xiàn)出不同于律呂工尺的另一種古代樂學(xué)傳統(tǒng)。不滿“一聲葉一字”“平引長聲”式的歌唱,主張“永言”必有長短高下之節(jié)奏,正是這些歌法的共同理念基礎(chǔ)。與詞曲演唱理論相比,此類歌法帶有鮮明的經(jīng)學(xué)、理學(xué)色彩,寄寓了儒者關(guān)于古典樂教的理想,同時(shí)也涉及文獻(xiàn)知識與實(shí)踐技藝的互動。劉宗周云:“陽明歌法,備春夏秋冬,開口定輕微,從之必重暢,舒暢后必急疾,急疾后必?cái)浚?fù)悠揚(yáng)振起。這聲氣自然而然,豈是強(qiáng)安排者?今梨園傳奇皆然,陽明亦有所本。”〔68〕認(rèn)為陽明歌法與戲曲演唱皆是出于自然之聲氣運(yùn)轉(zhuǎn),或許正暗示了“古”與“今”、雅樂與俗曲之間,可以存在某種一以貫之的“理”。“七聲”“九聲”兩系歌法是否從明代的俗樂或宗教演唱中汲取了靈感或知識資源,還待進(jìn)一步研究。然就明儒歌法系統(tǒng)內(nèi)部的流傳而論,我們亦不難窺見“當(dāng)代”如何層累地增飾、改寫了“古典”——不論是對“四氣—九聲”心學(xué)義理的闡發(fā),對“七聲”具體情貌的探討,抑或是牽合眾說而成的十二聲系統(tǒng)。在歌法流轉(zhuǎn)的過程中回溯經(jīng)學(xué)議題與經(jīng)典文本是考辨探賾的常見方式,對“歌永言”“累累乎端如貫珠”的理解,對十二律呂相關(guān)知識的研究,往往會成為學(xué)者采掇取用的資源。然而有趣的是,在以返回原典為標(biāo)榜的歌學(xué)考索中,有關(guān)歌法的知識傳遞,反而不斷踵事增華,即以各種論述結(jié)構(gòu)來容納進(jìn)新的、當(dāng)代的因素。在歌法這一技術(shù)色彩濃厚的知識領(lǐng)域,學(xué)者對“古法”的理解、對相關(guān)知識與理論的建構(gòu),既是“復(fù)古”,也是“察今”,除了文本的研讀,更需要通過親身實(shí)踐以體驗(yàn)其技法的妙諦。
① 李東陽著,李慶立校釋:《懷麓堂詩話校釋》,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9年版,第20—24頁。
② 張健《音調(diào)的消亡與重建:明清詩學(xué)有關(guān)詩歌音樂性的論述(上)》(周興陸主編:《傳承與開拓——復(fù)旦大學(xué)第四屆中國文論國際學(xué)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鳳凰出版社2018年版,第424—442頁)對明代詩學(xué)中的音樂理論做了全面考察,將其分疏為“音樂學(xué)”和“語言學(xué)”兩條途徑,并特別強(qiáng)調(diào)朱熹、李東陽詩論的重要地位。
③ 李舜華《從禮樂到演劇:明代復(fù)古樂思潮的消長》(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18年版)論述了明人對古樂的探討,偏重于樂學(xué)理論。孫之梅《明代歌詩考——兼論明代詩學(xué)的歌學(xué)品質(zhì)》(《文學(xué)評論》2012年第1期)考察了明代文人的歌詩活動。
④ 學(xué)界對明儒中陽明學(xué)一系的歌法及其在書院教育中的應(yīng)用已有關(guān)注,如鶴成九章《飛動梁塵的圣歌聲——關(guān)于明代書院的歌儀》[李弘祺編:《中國的教育與科舉》,陳翀譯,(臺灣)喜馬拉雅研發(fā)基金會2006年版,第363—385頁]對虞山書院的歌詩活動做了較詳細(xì)的個(gè)案研究;程嫩生《明清書院歌詩活動》(《求索》2016年第6期)介紹了有關(guān)歌詩、歌譜的概況;束景南《王陽明佚文輯考編年》(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813—819頁)收入了所謂“陽明九聲四氣歌法”并對其流傳做了考辨;張昭煒《王陽明九聲四氣法的三個(gè)層次》(《世界宗教研究》2015年第1期)、鹿博《氣的介入:中晚明歌教的緣起與呈現(xiàn)》(《中國文化論壇》2017年第9期)深入探討了“陽明歌法”的內(nèi)容及其心學(xué)內(nèi)涵。但陽明系歌法的發(fā)展過程仍有待梳理。此外,明人對《禮記·樂記》的經(jīng)學(xué)闡釋以及孔廟祭祀樂歌對古歌法的構(gòu)擬,學(xué)界鮮有討論。
⑤ 如王力《漢語詩律學(xué)》(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蔣寅《古詩聲調(diào)論的歷史發(fā)展》(陳平原等主編:《學(xué)人》第11輯,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杜曉勤《六朝聲律與唐詩體格》(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7年版)。
⑥ 如楊蔭瀏《中國古代音樂史稿》(人民音樂出版社1981年版)、卞趙如蘭(Rulan Chao Pian)《宋代樂學(xué):文獻(xiàn)與研究》(Sonq Dynasty Musical Sources and Their Interpretati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張世彬《中國音樂史論述稿》[(香港)友聯(lián)出版社1975年版]、陳萬鼐《中國古代音樂研究》[(臺灣)文史哲出版社2000年版]。
⑦ 參見楊蔭瀏:《中國古代音樂史稿》第二十七章《〈唱論〉和〈中原音韻〉》、第三十二章《明、清戲曲的發(fā)展一——南北曲》;陳萬鼐《中國古代音樂研究》第十五章《宗教音樂三種》。此外,王小盾《論漢文化的“詩言志,歌永言”傳統(tǒng)》(《文學(xué)評論》2009年第2期)論及宋代以后文人關(guān)于“永言”的主張,主要就詞曲創(chuàng)作而言。劉承華《中國古代聲樂演唱美學(xué)的歷時(shí)性展開——從〈師乙篇〉到明清“唱論”的歷史演進(jìn)軌跡》(《南京藝術(shù)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5年第2期)從現(xiàn)代音樂學(xué)的角度闡述了《禮記·樂記》中有關(guān)歌法論述與明清詞曲演唱的理論聯(lián)系,但對明清儒者如何理解、詮釋《禮記》歌法則未有論述。
⑧⑨ 孔安國傳,孔穎達(dá)等正義:《尚書正義》,阮元校刻:《十三經(jīng)注疏》,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276頁,第276頁。
⑩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雜著·尚書》,朱杰人、嚴(yán)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第23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172頁。
? 朱熹:《儀禮經(jīng)傳通解·詩樂》,《朱子全書》第2冊,第527頁。
?? 鄭玄注,孔穎達(dá)等正義:《禮記正義》,《十三經(jīng)注疏》,第3350頁,第3350頁。
? 衛(wèi)湜:《禮記集說》卷一〇〇,《中華再造善本》影宋嘉祐、熙寧間刻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版。
? 吳澄:《禮記纂言》卷三六,《中華再造善本》影元元統(tǒng)間刻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版。
? 胡廣:《禮記集說大全》卷一八,明內(nèi)府刻本。
? 沈括著,胡道靜校注:《夢溪筆談校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91頁。
? 張炎:《詞源·音譜》,顧廷龍主編:《續(xù)修四庫全書》第1733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65頁。
? 唐順之:《風(fēng)雅頌不必過為分別》,《荊川稗編》卷四二,明萬歷九年刻本。
? 參見李舜華:《從禮樂到演劇:明代復(fù)古樂思潮的消長》第五章第一節(jié)《嘉靖朝的銳意更制與諸家樂書的蔚興》,第195—217頁。
? 李文利門人范輅《大樂律呂元聲引》云:“吾師自弘治庚戌秋掌教吾庠……間以此語人……丁巳歲教授思南,不逾年而沒。”(李文利:《大樂律呂元聲》卷首,《續(xù)修四庫全書》第113冊,第133頁)由此可知李文利卒于弘治十年丁巳,《大樂律呂考注》之作,必在此前。
? 李文利:《大樂律呂考注》卷四,《續(xù)修四庫全書》第113冊,第193頁。
?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68頁。
? 李文察:《樂記補(bǔ)說》,《續(xù)修四庫全書》第114冊,第84頁。
? 章潢:《圖書編》卷一一五,明萬歷四十一年刻本。“周轉(zhuǎn)”乃據(jù)潘巒《文廟禮樂志》卷三(明萬歷十二年刻本)補(bǔ)。觀上下文意,此處應(yīng)是“宛轉(zhuǎn)”“折轉(zhuǎn)”“周轉(zhuǎn)”三者并列。章氏弟子萬尚烈《刻章聘君先生圖書編丐敘》(《圖書編》卷首)稱,《圖書編》“肇于嘉靖壬戌,成于萬歷丁丑”,即成書于萬歷五年。萬歷三十六年,章氏卒;后至萬歷四十一年,是書始得刊行于世。《文廟禮樂志》卷首有潘巒自識和許孚遠(yuǎn)《文廟禮樂志序》,據(jù)前者可知此書成書于萬歷十年,據(jù)后者知其正式刊行于萬歷十二年。
? 《明史》,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362頁;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333頁。趙廣升《孫應(yīng)鰲著述考(下)》(《蘭臺世界》2016年第18期)認(rèn)為此書已佚。
? 章潢:《諸家統(tǒng)論》,《圖書編》卷一一六,國家圖書館藏抄本。按,此引文不見于明萬歷刻本。此外,《文廟禮樂志》卷首所列“考證諸書”亦有“《律呂分解》”。
? 章潢:《圖書編》卷一一五。
? 《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755頁。
? 佚名:《玉音法事》,《續(xù)修四庫全書》第1293冊,第545—562頁。
? 楊慶:《大成通志》卷八,清康熙間刻本;俞天倬:《太倉州儒學(xué)志》卷四,《四庫未收書輯刊》第2輯第26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60—62頁。按,孫繼皋,無錫人,萬歷二年?duì)钤?肌睹魇贰贰端膸烊珪偰俊返仁芳匆娖溆袠仿深愔觥?/p>
? 王驥德著,陳多、葉長海注釋:《曲律注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80—281頁。
? 丁紀(jì)園:《〈渾成集〉中宋代〈娋聲譜〉與〈小品譜〉考釋》,《中國音樂學(xué)》1991年第4期。
???〔51〕 楊慶:《大成通志》卷八。
? 王守仁:《訓(xùn)蒙大義示教讀劉伯頌等》,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99頁。
? 朱得之:《稽山承語》,轉(zhuǎn)引自陳來:《〈遺言錄〉〈稽山承語〉與王陽明語錄佚文》,《中國近世思想史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0年版,第728頁。
? 王畿:《華陽明倫堂會語》,吳震編校整理:《王畿集》,鳳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160頁。
? 詹景鳳:《詹氏性理小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112冊,齊魯書社1995年版,第607頁。
? 姚坤:《刪定射禮直指》,明刻本。卷末有萬歷五年姚氏上呈書冊之公文。
? 毛奇齡:《皇言定聲錄》卷七,清嘉慶刻《毛西河先生全集》本。
? 林兆恩弟子張洪都《林子行實(shí)》云,嘉靖“乙丑七月,著《宗孔心要》《玄宗大道》《性空宗旨》及《歌學(xué)解》等集”(《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63冊,書目文獻(xiàn)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2頁)。
?? 林兆恩:《林子全集·元部·歌學(xué)解》,《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63冊,第322頁,第322—323頁。
????〔53〕〔54〕〔55〕〔56〕〔57〕〔58〕〔59〕〔60〕〔61〕 趙所生、薛正興主編:《中國歷代書院志》第8冊,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9頁,第76—79頁,第80頁,第76—77、80、82—85頁,第681頁,第681—682頁,第685—686頁,第683—684頁,第682頁,第685頁,第682頁,第682頁,第682頁。
? 參見黎業(yè)民整理:《陳獻(xiàn)章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
〔52〕 《中國歷代書院志》第9冊,第562頁。
〔62〕 朱載堉撰,馮文慈點(diǎn)注:《律呂精義》,人民音樂出版社2006年版,第892頁。
〔63〕 李之藻:《頖宮禮樂疏》卷七,明萬歷間刻本。
〔64〕〔66〕 李塨:《小學(xué)稽業(yè)》,《續(xù)修四庫全書》第947冊,第147—148頁,第148頁。
〔65〕 王力:《詩經(jīng)韻讀》,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12年版,第357頁。
〔67〕 毛奇齡:《竟山樂錄》卷二,清嘉慶刻《毛西河先生全集》本。
〔68〕 吳光主編,何俊點(diǎn)校:《劉宗周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2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