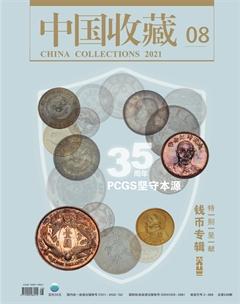紅色制幣為蘇區建設立功
程興強

川陜省蘇維埃政府石印局得漢城遺址
1932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撤離鄂豫皖革命根據地,12月進入川陜邊區。12月29日,川陜省臨時革命委員會在四川通江縣城成立。
徐向前元帥在《歷史的回顧》中記述:“1933 年2月中旬,在通江召開了150名代表出席的川陜省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此次會議通過的《川陜省蘇維埃臨時組織大綱》,規定了在川陜省財政委員會下設立工農銀行(后更名為川陜省蘇維埃政府工農銀行),開始籌備印鈔,1933年3月開始發行蘇(維埃)幣。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回顧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在建立川陜省蘇維埃政府時期的制幣史,不僅是學習黨史,也是研究和傳承紅色錢幣文化的重要機遇。
首要任務是印制布幣
川陜省蘇維埃政府工農銀行下轄兩個制幣機構,即石印局與造幣廠,兩者間是無隸屬關系的平級機構。石印局印制蘇維埃布幣、紙幣,造幣廠制造蘇維埃銅元、銀幣。
川陜革命根據地博物館原副館長杜中在《川陜根據地的印刷事業》一文中提到:“石版印刷:巴中最早只有兩家。”1933年6月,這兩家石印鋪被川陜省蘇維埃政府沒收,成為蘇維埃政府石印局的一部分,首要任務就是印制蘇維埃布幣。

川陜省蘇維埃政府工農銀行發行的貳串、叁串布幣
另一邊,1933年初,鄭義齋主持在苦草壩上街里籌建起了石印局。最初石印局(印布幣)設在苦草壩上街饒文華住宅,局長是周北海,司務長是高仕敏。不久,其轉移至得漢城李儒金家的大瓦房里繼續生產。這時規模還很小,只有一架石印機,幾個工人,開始印制蘇維埃貳串、叁串布幣。據李儒金回憶:“石印局剛開辦時,我記得看到的一架石印機,機上一塊石版有半個方桌大,兩個人扳輪子搖動機器,一個人用一個滾筒在石版上滾油墨,鈔票的版式都謄在石版上。鈔票用紙和布都印過。印好的鈔票先拿到總經理部,就是川陜省工農銀行總行辦公的地方去蓋好章,然后交到剪票房,剪成一張一張的鈔票,這種鈔票大多是交給經濟公社拿去買貨供應軍民。一元銀幣可以換三十到三十二串票子。”
《川陜根據地的印刷事業》一文中也談到:“1933年8月1日,全省第二次工農代表大會召開,正式成立石印局,設址巴中縣城文星街。并將部分逃走在外、無人營業店鋪中的寬布、紙張等印刷材料沒收撥給石印局。石印局有五張石版,印制條件比苦草壩印刷廠好些。由于根據地的擴張和鞏固,故省石印局大量印制了淺藍、英丹藍、淺綠等顏色、面額不同的布幣,內部兌換的伍串、拾串的大面額布幣也從此問世,但市面流通不多。”對于川陜省蘇維埃政府石印局的正式成立時間,杜中先生考證的是1933年8月1日。不過也有另一說法,如《通江現代史資料選》中就記載:“1933年11月中旬,成立川陜省石印局”。
成為蘇票印制的絕唱
1934年3月中旬,中共川陜省委、川陜省蘇維埃政府有計劃、有組織地從通江城撤離了一批指揮及后勤機構,向苦草壩得漢城方向搬遷,其中就有蘇維埃石印局、造幣廠、兵工廠、紅四方面軍總醫院等單位。造幣廠設在得漢城的城坡里,石印局再次回到得漢城山梁上的李儒金家大瓦房里繼續生產。1934年底或1935年初,蘇維埃石印局撤離得漢城遷往旺蒼壩,其在得漢城的生產時間應該是10個月左右。
在這個蘇維埃石印局得漢城二期生產期間,布幣的產量逐漸降低,但增加了紙幣的產量。中共川陜省委組織部長、川陜省蘇維埃政府副主席余洪遠回憶說:“紙幣印制的時間比較晚,大約1934年六七月才出來。”

川陜省三串紙幣正面與背面圖
據《通江蘇維埃志》記載:“紙幣廠初時僅12個工人,印量很少。1934年夏,因布幣停止生產,原廠(布幣廠)工人和機器一并參與印制紙幣,當時廠內共有工人30余(名),機器10余架。以道林紙為主要材料,用紅、綠、黃、藍等色套印圖案,票面額有一串、三串、一元三種。到1935年元月共印紙幣60萬元。”
據此可以推斷,1934年七八月間,貳串、叁串布幣應該是逐步停止了印刷,即便以后還有零星生產,其生產時間也不會延續到1934年底。布幣停止生產是因為布的來源問題和蘇區對布匹的需求劇增,導致供需矛盾突出。《通江黨史資料叢書》記載:“1934年粉碎敵人的六路圍剿,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形成貨幣貶值,白布要三十串一尺,印制布幣需用的布多于日常生活用布,因此,布幣的印刷就停止了。”
1934年底至1935年初,紅軍開始逐步撤離通(江)、南(江)、巴(中)地區,蘇維埃石印局與兵工廠也于此時開始向旺蒼轉移。到達旺蒼后,原工農銀行總行負責剪票的工人被另行分配到被服廠工作,蘇維埃石印局也就此停止了蘇票的印制生產。因此,蘇維埃石印局得漢城二期的生產活動,成為了川陜省蘇維埃政府蘇票印制的絕唱。
在通江開始試制
關于川陜省蘇維埃造幣廠,其最早于何時何地制造蘇維埃硬幣?是否利用過白區貨幣加蓋蘇維埃印記?是否生產過1933年版蘇維埃銀幣?蘇維埃大二百文銅元采用何種工藝?蘇維埃造幣廠的生產流程什么樣?諸如此類的未解謎團已經困擾了學界及錢幣收藏界多年。
受當年戰爭的影響,川陜省蘇維埃造幣廠也經歷了多次搬遷。目前有史可查的廠址是通江得漢城、南部縣謝家河、通江城郊西寺、通江得漢城城坡里張家四合院、通江苦草壩紅四方面軍羅坪兵工廠,以及旺蒼五峰鄉桂花村張光才家院子等。
川陜省蘇維埃政府最初的造幣情況,多位原紅四方面軍老干部的回憶中都曾談及:早在宣達戰役以前,蘇維埃造幣廠就已經開始制造蘇維埃錢幣了。有回憶甚至指出:1933年七八月間,其就開始在通江苦草壩試制蘇維埃銅元、銀幣和錫錢。
原西北軍委供給部軍需科長(分管造幣工作)的李汎山回憶:“布票子是以串為單位的,串以下還需找補,為了買東西找補方便,造幣廠又壓了一種錫錢,就是錫小錢,在蘇區流通,作找補用。錫錢的面額現在記不起了,壓錫錢的地點大致在通江縣和苦草壩。”“1933年,紅軍打下達縣,把劉存厚造幣廠的機器和材料用人力從達縣抬到通江,以后我們就在通江壓銀元、銅元了”。
綜合其他資料筆者認為,1933年七八月間,蘇維埃造幣廠于通江苦草壩得漢城開始試制蘇維埃錫錢、大二百文銅元和蘇維埃銀幣,但錫錢、銀幣并不成功,而蘇維埃大二百文銅元則逐漸開始小批量生產。

通江西寺造幣廠舊址中國人民銀行巴中市中心支行供圖
1980年7月1日,原川陜省蘇維埃閬(中)、蒼(溪)、南(部)中心縣委常委羅家鎬在接受人民銀行四川省分行金融研究所訪談時回憶:“在南部謝家河,國民黨原有一個造幣廠……解放時留下幾十名工人和管理人員,還有銅和機器。我們就利用這些人和東西,做了模子,壓過鐮刀斧頭二百文銅元,但數量不多,時間是1933年下半年。”
從川陜省蘇維埃各種銅元的制造時間上判斷,羅家鎬所說的“鐮刀斧頭二百文銅元”,筆者認為就是川陜省蘇維埃大二百文銅元。但對于蘇維埃大二百文銅元中哪些是謝家河造幣廠制造的,迄今仍然沒有確切的結論。
實現規模化生產
1933年8月中旬至1933年10月下旬,紅四方面軍對川北地方軍閥分別發起了儀南、營渠、宣達3 次進攻戰役,繳獲了川北地方軍閥多家造幣廠的機器設備。同時,川陜省蘇維埃政府廣泛動員招募了一批原川北地方軍閥造幣廠的技術師傅和熟練工人來到通江,結合川陜省蘇維埃得漢城造幣廠的設備和人員,于1933年11月18日在通江城郊西寺正式成立了川陜省蘇維埃政府造幣廠,從此開始了川陜省蘇維埃金屬貨幣的規模化生產。
《川陜根據地南充地區革命文化史料集》中記載:“紅軍自9月25日起,把軍閥李煒如設在新政市的造幣廠的全部鑄造機器運往通江縣得勝山西寺。這時,開始鑄造紅軍銅幣,為蘇維埃建設立功。”
這一期間,造幣廠制造了大量蘇維埃大二百文銅元,同時還少量制造了蘇維埃銀幣。
曾在川陜省造幣廠和石印局工作過的王開一回憶說:“西寺是一座縣上有名的大廟子,造幣廠在這里大量鑄造了鐮刀斧頭圖案的大二百文銅元。”在筆者等人目前收集的5272枚川陜省蘇維埃銅元實物和圖片樣本中,蘇維埃大二百文銅元就有1932枚,占比蘇維埃銅元總量的3 6%有余。由此可見,蘇維埃西寺造幣廠實現了蘇維埃銅元的規模化生產。
而1934年2月15日,中共中央機關報《斗爭》曾有這樣的報道:“川陜省工農銀行于去年(1933年)12月4日正式開幕了。造幣廠、銅元廠也同時開鑄,每天出銀元很多,成色很好。”
關于西寺制造銀幣,王開一曾說:“我記得銅元和銀元只在城郊西寺和鄉下城坡里鑄過。”是否可以理解成,西寺和城坡里都制造過蘇維埃銅元及蘇維埃銀幣?
版別中的奧妙
得漢城城坡里造幣廠遺址至今尚在,其位于四川省巴中市通江縣永安鄉四村四組張家四合院。得漢城地勢險要,易守難攻,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紅軍到達川北后,在此建立了眾多工廠和后勤機關。
因人才、技術、設備的優化配置,也得益于紅四方面軍兵工廠的技術指導,城坡里造幣廠的產品質量有了很大提高。首先是在制模工藝上有了重大改進,原來長期使用的、以敲打法為主的制模工藝被雕刻法制模工藝所取代;其次,碾片機被廣泛運用到了金屬板材的平整工序中來;還有兵工廠總技師何揚州設計制造的印花機,基本解決了印花壓力問題。其間,蘇維埃政府工農銀行又設計出了新的銅元樣式,用以替換原來的蘇維埃大二百文銅元,此后生產的蘇維埃鐮刀鐵錘銀幣、新版的蘇維埃赤化全川小二百文銅元、蘇維埃五百文銅元等,其精美程度遠勝于川北任何一家地方軍閥造幣廠所制造的錢幣。與此同時,城坡里造幣廠還開始了大規模的白區銀幣仿制生產。

川陜省蘇維埃大二百文銅元

川陜省蘇維埃壹圓銀幣

蘇維埃赤化全川小二百文銅元
據王開一回憶:“在城坡里造幣廠所壓的坯子,當時任務緊,如果造幣廠趕不及印花,有時也集中起來,用船運到對岸羅坪的兵工廠去代為加工壓字印花。”這里所說的錢幣坯子,王開一沒有說明是銀幣還是銅元,抑或二者都有。而根據對川陜省蘇維埃各類錢幣版式的研究分析,蘇維埃大二百文銅元雖然產量較大,版式多,但幾乎所有版式之間都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其工作鋼模以混合搭配的方式將整個版式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版式體系。因此可以說,蘇維埃大二百文銅元是具有時間傳承關系的得漢城、西寺、城坡里三個造幣時期生產的產品。
蘇維埃赤化全川小二百文銅元、五百文銅元與蘇維埃銀幣則不同,這3種錢幣都分別存在兩個鋼模互不搭配、版式完全獨立的版式體系,這種現象應是由兩個造幣地點獨立封閉造幣所致。并且每種錢幣中的兩個版式體系中,必定有一個是羅坪兵工廠制造的,而其另一版式體系則是城坡里造幣廠制造的。
對此筆者等人的推論為:蘇維埃銀幣中的無島類系列,是西寺造幣廠與城坡里造幣廠制造的;蘇維埃赤化全川小二百文銅元中的有齒系列、五百文銅元中的簡體聯系列應出自城坡里造幣廠;蘇維埃銀幣中的有島類系列、赤化全川小二百文銅元中的無齒系列、五百文銅元中的繁體聯系列,則是羅坪兵工廠制造的。
在旺蒼繼續投入生產
1935年初,城坡里造幣廠按照西北軍委、中共川陜省委、川陜省蘇維埃政府的要求,有組織、有計劃地開始向旺蒼轉移,并在旺蒼五峰鄉桂花村張家大院設廠繼續投入錢幣生產。
原川陜省蘇維埃工農銀行保管科長楊文局回憶:“長征時隨紅軍轉移,到旺蒼壩以后停止了印鈔。”這里所說的印鈔,無疑包括了印制布幣和紙幣。這也說明到旺蒼之后,連紙幣都已經停止了印制。

蘇維埃五百文銅元

蘇維埃造幣廠仿制的白區銀幣程興東供圖
1934年1月26日,鄭義齋在《干部必讀》第71期上發表《在大舉消滅劉湘中目前幾件緊急工作》一文中強調:“今后我們要實行‘不浪費一個子彈殼,每個紅色戰士都要了解搜集子彈殼的重要。”銅材匱乏,進而影響到蘇維埃兵工廠產能不足,讓前方將士始終難以獲得充足的彈藥補充。原紅四軍指導員屈全清在1959 年接受訪談時回憶:“紅軍到地(通江),川軍的鋼洋、銅元、麻錢都用,半年后紅軍就用自己的錢了。紅軍的銅元只用了一年多,以后就收回去,以供前方造子彈、手榴彈之需,只用布幣、紙幣。”
那么,蘇維埃造幣廠在旺蒼期間生產什么錢幣呢?綜合上述資料后筆者認為,這期間沒有生產蘇維埃系列布幣、紙幣、銅元、銀元,僅僅是仿制白區銀幣。
總而言之,通過上述探討可以看到,蘇維埃貨幣的發行,結束了軍閥混戰時期川陜邊區混亂的幣制局面,統一了蘇區幣制,為壯大紅軍隊伍、鞏固蘇維埃政權、發展蘇區經濟、改善人民生活都做出了卓越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