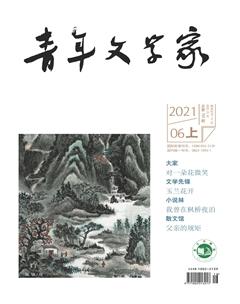父母親的結婚照
馮愛霞
結婚,是終身大事,結婚照,更是彌足珍貴。家中就珍藏著一張1957年的父母的結婚照。泛黃的二寸照片上,父親身穿綠色軍裝,頭戴大蓋帽,肩挎駁殼槍,目光炯炯,腰身挺拔;母親身著綠色大襟襖,鄉土短發,拘謹端莊。
1947年,16歲的父親在沂蒙精神的感召下,走上了一條紅色道路,足跡遍及大半個中國。革命勝利后,父親被選送到炮兵學校學習。畢業后的三天假期,父親帶著政治任務,響應自由戀愛號召,回家省親并找伴侶。
父親回家的消息,傳遍了整個北汶村,村民把門樓圍得水泄不通。奶奶用手摩挲著兒子的臉,老淚縱橫,曾經以為兒子犧牲了,把眼睛都哭瞎了。
當媒人上門向姥姥問親時,23歲的母親從門縫里瞅到,曾經鄰家干癟的小男孩,十年后,竟戴著大蓋帽,身穿軍裝,英俊瀟灑地出現在門口。傾慕之情油然而生,便含羞應下了這樁無任何彩禮的婚事。第二天,便隨父親千里迢迢來到了昌樂駐軍部隊。經組織批準,登記結婚了。母親說:“那是個禮拜天,一大早就去照相,心突突亂跳,臉也不會笑了。中午到供銷社買了三大件,臉盆、暖壺和痰盂,還有糖果和花生。晚上,請來了戰友,由首長當證婚人宣讀證詞,先向毛主席像敬禮,就像開茶話會一樣,莊重又喜慶。”這簡單又質樸的婚禮,讓母親幸福回味了一生。
母親沒上過學堂,但好學上進。父親教母親寫字,母親為節省紙張,就用樹枝在地上畫。當母親歪歪扭扭寫出“秦玉貴”三個字時,激動得看個不停。民兵打靶,母親又第一個報了名,由于經驗不足,動作不協調,經常吃零分“大餅”,常焦急地落淚。父親說:“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常指導母親怎樣練習射擊。母親也常拿著一根木棍當槍使,單眼閉合練瞄準。經過刻苦訓練,年終的打靶比賽,5發子彈,竟打出了1個10環、2個9環、2個8環的好成績。這件事,母親從年輕講到年老,陶醉地說:“你爸是哼著曲兒回家的,樂呵呵地說,‘家屬打靶比賽,你立了頭功,都傳到我的耳朵去了。”每每講到這兒,母親的臉上就微微泛起紅暈。當我們在學習中遇到困難時,她就教導我們“只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
20世紀60年代前后,我的大姐降臨了。父親由于公務繁忙,對母親少有陪護。出院的日子到了,沒等到父親,焦急的母親就抱著剛出生的大姐,走起了四十里山路。荒山野嶺,不時傳來狼嚎的聲音。驚恐之余,突然,從路溝躥出一人,披頭散發,咿呀亂叫,嚇得母親抱著嬰兒狂奔,那人卻緊追不舍。筋疲力盡之時,終于遇見一位老大爺,他大喊一聲,那人止住了腳步。老漢說:“不用怕,他是我們村的,雖是瘋了,但不打人,是餓壞了想要東西吃。”母親知情后,由氣憤到憐憫,把僅帶的干糧遞給了他。
兩年后,部隊動員家屬回家。隨之,在低矮的土房內,哥哥出生了。滿月后,母親一邊照顧兩個孩子,一邊下地掙工分。幾個寒來暑往,組織又批準母親返回了部隊。父親時常愧疚,在她最需要的時候,因公未能照料。但母親卻說:“公家的事,就是大事。”
當我的二姐出生后,母親再也不打算要第四個孩子了。也許吉人自有天相,八年后,我來到了人世間。父親老來得女,常把我扛在肩頭,母親更是忙碌,下班后做飯、縫衣、納鞋底。有一次,我到小伙伴家里玩,看到他的母親在吃飯,4歲的我吃驚地說:“我的母親從不吃飯。”他們哈哈笑著,讓我回家觀察。原來,母親都是先讓我們吃,自己最后再吃。
擁有一臺縫紉機,是母親夢寐以求的事。在父親多次向組織申請下,終于爭取到一個名額。當父親把蜜蜂牌縫紉機帶回家時,母親激動地摸了又摸,視為珍寶。深夜里,母親的身影常映在墻上,仿佛一幅動畫,并時常為左鄰右舍縫縫補補。
20世紀70年代中期,父親軍轉干回到地方。每到一處,都披星戴月,扎根地方,造福群眾,他不怕別人麻煩自己,總怕自己麻煩別人。當父母走到人生終點時,還叮囑我們:“一切從簡,別誤了公家的事,不要給組織和他人添麻煩。”我的父親母親,如奔流長河中的浪花朵朵,隨風遠去了,但那濤聲,依舊在我們耳畔回響。
歲月變遷,時光流轉。父母的結婚照,如同一個時代的縮影,刻錄著滄桑,散發著清香,也見證著我們一步步地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