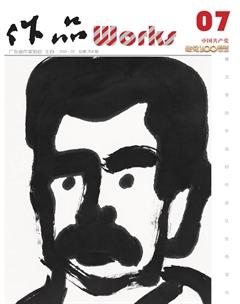評馮友蘭的新形上學(評論)
杜國庠
前 言
馮友蘭氏數年來發表五種著作,建立了他的“新形上學”體系和新道統。首先以《新理學》宣布了所謂“全新底形上學”的體系,自許為“最哲學底哲學”;最近以《新原道》建立了他的新道統,自命為獨接“中國哲學的精神”;中間三種——《新世訓》《新事論》及《新原人》,大抵運用他的玄學觀點去衡量事物或指導人生,以鼓吹其所謂“內圣外王之道”,以擴大其所謂“無用”的哲學的“大用”。短短幾年,共成五著,其辛勤著述,自成家言,固堪欽佩;但是為了“持標新統”,不惜抹殺史實,厚誣古人,為了鼓吹“玄風”,不惜提倡“風流”,是認“任誕”,則不免有損學人的風格。而且這種形上學,崇尚“玄虛”,足以阻礙科學的發展,標榜道統,也復違背民主的精神,對于今后和平建國的大業,實不相宜,故略加批評,勢非得已。
一
凡哲學都有它相適應的方法論。方法不正確;不會產生正確的哲學。反之,正確的哲學,也要求著正確的方法。因為事物運動的規律,總括下來便是事物的法則,把握這種規律反而用以對付事物,便成為方法。——兩者都以同一客觀現實為根據的。
那么,馮氏所謂最玄虛的哲學“新理學”,用的是怎樣的方法呢?為了下文敘述的方便,讓我們先引用他自己敘述“新理學”的構成的一段話吧。他在《新原道》說:
“在中國哲學史中,先秦的道家,魏晉的玄學,唐代的禪宗,恰好造成了這一種傳統(即所謂‘不著形象,超乎形象的傳統。——素)。新理學就是受這種傳統的啟示,利用現代新邏輯學對于形上學底批評,以成立一個完全‘不著實際底形上學。
“但新理學又是‘接著宋明道學中底理學講底。所以于它的應用方面,它同于儒家的‘道中庸。它說理有同于名家所謂‘指。……它說氣有似于道家所謂道。……它說了些雖說而沒有積極地說什么底‘廢話,有似于道家,玄學及禪宗。所以它于‘極高明方面,超過先秦儒家及宋明道學。它是接著中國哲學的各方面的最好的傳統,而又經過現代的新邏輯學對于形上學的批評,以成立的形上學。它不著實際,可以說是‘空的。但其空只是形上學的內容空,并不是其形上學以為人生或世界是空底。所以其空又與道學(當是‘道家誤植。——素),玄學,禪宗的‘空不同。它雖是‘接著宋明道學底理學講底,但它是一個全新底形上學。至少說,它為講形上學底人,開了一個全新底路。”(第一一三至一一四頁)
這里馮氏自稱“新理學”為“全新底形上學”,是不是“全新底”,可暫不管它,但是形上學則千真萬確,因為它集道家、玄學、禪宗及宋明道學的“玄虛”之大成。因此,“新理學”就需要一種和它相適當的方法,即馮氏所謂“過河拆橋”的方法。他說:“‘過河拆橋是大不道德底事。但講哲學即非此不足以達到‘玄之又玄的標準。”(旁點是我加的,下同。——素)這方法是怎樣的呢?馮氏說:“哲學始于分析,解釋經驗,換言之,即分析解釋經驗中之實際底事物。”又說:“哲學中之觀念、命題及推論之系形式底,邏輯底者,其本身雖系形式底,邏輯底,但我們之所以得之,則靠經驗。我們之所以得之雖靠經驗,但我們既已得之之后,即見其并不另需經驗以為證明。其所以如此者,因此種觀念、命題及推論,對于實際并無所主張,無所肯定,或最少主張,最少肯定。”(《新理學》緒論)即是“內容空”的。也是“形式底,邏輯底”。比方說,經驗是“橋”,不從“分析解釋經驗”開始,便得不到所謂“形式底”觀念,例如“理”,好像沒有橋就不能到達彼岸。但“既已得之之后,即見其并不另需經驗以為證明”,便可再“不著實際”,“不管事實”了,好像已過了河,無須用橋,便把橋“拆”掉了。其始“仍是以事實或實際的事物,為出發點”;其終,則成為“哲學可以說是不切實際,不管事實”的(《新理學》第一二頁)。所謂“過河拆橋”,就是這個意思。
馮氏說:“它說理同于名家所謂‘指。”“指”是公孫龍所用的術語。這里所謂“名家”,自然指的是公孫龍。可見這種方法,正是公孫龍的衣缽真傳。公孫龍的名學的特點,在“離堅白”。他的《堅白論》正是運用這種方法,從分析實際的事物一一具體的“堅白石”出發,而獲得抽象的“堅”和“白”這類共相。公孫龍于《指物論》稱之為“指”。這就是馮氏所謂“名家所謂‘指”之“指”,也即“新理學”之所謂“理”。所以說:“在中國哲學史中,公孫龍最先注意此點。公孫龍所主張之‘離堅白,即將堅或白離開堅白石而單獨思之也。此單獨為思之對象之堅或白,即堅白之所以為堅或白者,即堅底物或白底物之所以然之理也。”(第一章第四節)在公孫龍,“指”是能夠自己轉化為“非指”,即轉化為“物”的。所以說:“且夫指固自為非指,奚待于物,而乃與為指?”(《指物論》)無須待什么“氣”去“依照”才成為“實際底事物”,也未說到什么“指世界”,都和馮氏不同。馮氏所以賞識這種方法,其故在于“非此不足以達到‘玄之又玄的標準”。
不過,馮氏在前面引文中再次提到所謂“現代新邏輯”,似乎對于他的“新理學”的成立頗為重要。其實所謂“現代新邏輯”,本質仍然還是形式“邏輯”,其所謂“新”,無非多加幾個“如果”而使命題更形式化罷了(《新理學》緒論第四節),而馮氏之所以特別賞識它的緣故也在這里。
由于這種“過河拆橋”的方法論,把橋拆了,斷絕了兩岸的往來;拋棄了經驗,脫離了現實,使理論和實踐完全脫節。這就使他的哲學變成僵硬的沒有血肉的空殼,不能從現實的寶藏得到充實;同時他的理論也不能從實踐獲得檢證,這是一。因為拋棄了經驗,脫離了現實,他的哲學方法便不得不與科學的方法,成為兩橛,無力促進科學的發展,這是二。因此,他的哲學也就無法發揮他所謂“大用”,即無法指導人生。雖然他又從儒家檢得了一條所謂“道中庸”的尾巴,硬裝在所謂“極高明”的玄學體系上面,湊成“極高明而道中庸”的標語,但到底還是形式的東西,在腦子里“思”——“思”,似乎是“言之成理”,一旦到了實踐,還是要碰壁的。因為“玄虛”到底不是人生的道路,這是三。以下試把這幾點略為展開。
二
在《新原道》中,馮氏拈出“極高明而道中庸”這一標語,以示他的“新理學”的本領,并作他批評中國各派哲學的準繩。他認為“中國哲學是超世間底。所謂超世間的意義是即世間而出世間。”他說“這種境界以及這種哲學,我們說它是‘極高明而道中庸。”即是說,“這種境界是最高底,但又是不離乎人倫日用底。”也即是“超越人倫日用而又即在人倫日用之中”的(《新原道》第二頁)從上節的引文看來,他一方面接受了名家公孫龍的哲學方法,利用所謂“現代的新邏輯學”,批評了先秦的道學,魏晉的玄學,唐代的禪宗及宋明的理學,使這個玄虛的——“不著形象,超乎形象”的“傳統”,益發玄虛,而獲得了“四個空底觀念”——所謂理、氣、道體及大全的觀念。說是“它于極高明方面超過了先秦儒家及宋明道學”。另一方面,它卻又“接著宋明道學中底理學”,硬把儒家所謂“人倫日用”的實踐哲學接上去,說是“于它(新理學)的應用方面”,它同于儒家的“道中庸”,又用這去批評禪宗所謂“擔水砍柴,無非妙道”,還不徹底。正因為它是各方“接著”的緣故,所以便不免有接不攏來的弱點。在方法論上,尤其表現得明顯:所謂“極高明”,既唯恐其玄虛,而所謂“道中庸”,則又不能不踏實,故雖用了“而”字訣把“高明”和“中庸”拴在一起,實際上還是解決不了問題。
這里我們先來看看馮氏的所謂“極高明”方面。他說:
“在新理學的形上學的系統中,有四個主要底觀念,就是理,氣,道體及大全。這四個都是我們所謂形式底觀念。這四個觀念,都是沒有積極底內容底,是四個空底觀念。在新理學的形上學的系統中,有四組主要底命題。這四組主要底命題,都是形式命題。四個形式底觀念,就是從四組形式底命題[得]出來底。”(《新原道》第一一四頁)
怎樣得出這幾個“主要底觀念”呢?就是上面所說的“過河拆橋”的方法。拿“理”這個觀念來說,他說:“在新理不賓形成學的系統中,第一組主要命題是:凡事物必都是什么事物,是什么事物,必都是某種事物。有某種事物,必有某種事物之所以為某種事物者。借用舊日中國哲學家的話說:‘有物必有則”。
“……一切山所共有之山之所以為山,或一切水所共有之水之所以為水,新理學中稱之為山之理或水之理。有山則有山之理。有水則有水之理……”
到這里為止,橋尚未拆,這種“有物必有則”的見解,我們可以同意。但再下去,情形完全顛倒,便是“既已得之之后,即見其并不另需經驗以為證明”的階段了。他說:
“有某種事物必有某種事物之所以為某種事物者。這就是說:‘有某種事物,涵蘊有某種事物之所以為某種事物者。……‘有某種事物之有,新理學謂之實際底有,是于時空中存在者。‘有某種事物之所以為某種事物之有,新理學謂之真際底有,是雖不存在于時空而又不能說是無者。……”
“‘有某種事物,涵蘊有某種事物之所以為某種事物者。從此命題,我們又可推出兩命題。一是:某種事物之所以為某種事物者,可以無某種事物而有。二是:某種事物之所以為某種事物者,在邏輯上先某種事物而有。”(《新原道》第一一四至一一五頁)
于是,“總所有底理”的“理世界”成立了。而且“理世界在邏輯上先于實際底世界”了。我們姑且不說,事實上沒有這個“理世界”;也姑且不說,任何“邏輯”都必有其實際的根據,邏輯其實就是實際的一種反映。但從邏輯上說,馮氏這邏輯也有些可疑。老實說,他是以邏輯的姿態,在玩文字的花樣。
在剛引的文句里,在所謂“有某種事物必有某種事物之所以為某種事物者”,或在“有某種事物,涵蘊有某種事物之所以為某種事物者”之中,第一個“有”字,即“有某種事物”句中的“有”字,是表示存在的意思。第二個“有”字,即“必有……”或“涵蘊有……”的“有”字,則是表示領有的意思,字形一樣,意思不同。在這里,第二個“有”字表示著“其事物之所以為某事物者”為它(“有”字)的主語(即“某種事物”)的屬性,和它不可分離的(如果可以分離,就不能說是“某種事物之所以為某種事物者”。——素)。所以,實際上,“某種事物之所以為某種事物者”之有無,必然要以“某種事物”之有無(即存在與否)來決定。故在邏輯上嚴格地說,也不能有“某種事物之所以為某種事物者”的獨立存在的問題,因而也不能說它“先某種事物而有”。但是,馮氏卻利用著兩個“有”字的字形相同,第一步:把“必有”變成“涵蘊有”。第二步:把“涵蘊”和“有”分離,把“有”字冠于“某種事物之所以為某種事物者”之上,使它采取“有某種事物”的句式。第三步:便分開來說:“有某種事物”之“有”,如何如何;“有某種事物之所以為某種事物”之“有”,又如何如何。第四步:便“推”出了“某種事物之所以為某種事物者,可以無某種事物而有”。第五步:(這是最后的一步)便達到了“某種事物之所以為某種事物者,在邏輯上先某種事物而有”這一命題。于是他所企圖建立的“理世界”的一切準備工作,通通完畢,只待“總括”一下,便可揭幕。這種偷天換日的手法,是文字的游戲!也是“邏輯”的玩弄!
三
光有理是不能說明實際的事物的。馮氏也承認“理不能自實現。必有存在的事物,理方能實現”。于是他又“對于事物作理智底分析”,由這樣的一組命題:“事物必都存在。存在底事物必都能存在。能存在底事物必都有其所有以能存在者”,而得到他所謂“氣”——“真元之氣”。據他說:這“氣”是“一不能說是甚么者。此不能說是甚么者,只是一切事物所有以能存在者,而礤本身,則只是一可能底存在。因為它只是一可能底存在,所以我們不能問:甚么是它所有以能存在者。”這種只是“一不能說是甚么”的,“只是一可能底存在”的“氣”,實際上是沒有的。它只是觀念上的東西。因為要“不著實際”,要“超乎形象”,所以只好這樣地給它規定。所以馮氏說:“我們不能說氣是甚么。……說氣是甚么,即須說:存在底事物是此種甚么所構成者。如此說,即是對于實際,有所肯定。此種甚么,即在形象之內底。”(《新原道》第一一五至一一六頁)可見所謂“理智的分析”者,并不是客觀地運用“理智”去“分析”,而是為了滿足主觀預定的要求去規定。
可是,“理不能自實現”,“氣”又“只是一可能底存在”,“可能底存在”,還不是“能存在底事物”,還不能“實現理”。這不是“發現”了“理世界”,同時又失掉了“實際底世界”嗎?那么,怎樣辦呢?為了補救這個缺點,馮氏又提出一個形式底主要底觀念——“道體”。他說:“第三組主要命題是:存在是一流行。凡存在都是事物的存在。事物的存在,是其氣實現某理或某某理的流行。實際的存在是無極實現太極的流行(他說“氣……亦稱無極”;“總之,所有底理,……名之曰太極”)。總之,所有的流行,謂之道體。一切流行涵蘊動。一切流行所涵蘊底動,謂之乾元。借用中國舊日哲學家的話說:‘無極而太極”。“存在是一流行。凡存在都是事物的存在。……一切流行涵蘊動”。這些命題,還是根據經驗,是可以同意的。但這“流行”或“動”,是有了“事物”以后的“流行”或“動”,怎樣能使“理”“氣”成為“事物”呢?怎樣能使“無極而太極”“而”得起來呢?這里馮氏還是用他玩弄“邏輯”的手法,提出一個命題:“事物的存在,是其氣實現某理或某某理的流行”。這樣,輕輕地把“事物的存在”改變為“其氣實現某理或某某理的流行”。接著便說明道:“存在者是事物,是事物者必是某種事物,或某某種事物。是某種事物或某某種事物,即是實現某理或某某理(注意:不是‘即有某理或某某理!——素)。實現某理或某某理者是氣。氣實現某理或某某理,即成為屬于某種或某某種底事物。沒有不存在的事物。亦沒有存在而不是事物者。亦沒有是事物而不是某種事物者。所以(這‘所以來得突兀!——素)凡事物的存在都是其氣實現某理或某某理的流行。”(《新原道》第一一七頁)這里只說到“其氣實現某理或某某理”,但未說明“氣”何以能夠“實現”理。所以馮氏又說:“因為流行就是動,就邏輯方面說,于實現其余底理之先,氣必實現動之理。氣必先實現動之理,然后方能有流行。……事實上雖沒有只是流行底流行,但只是流行底流行卻為任何流行所涵蘊。在邏輯上說,它是先于任何流行。它是第一動者。”(同上)我們且不問這“第一動者”是不是“上帝”或“創造者”,也不管它稱為甚么“氣之動者”也好,“乾元”也好,終歸還是沒有解決問題。因為:就從邏輯上說,“于實現其余底理之先,氣必實現動之理。氣必先實現動之理,然后方能有流行。”但是“實現”是一事,也是一“動”。所以,“實現動之理”的“氣”,必先已是能“動”的“氣”;不可能“只是一可能底存在”的“氣”,這樣地推下去,“氣”至少必有“動”之性。這就和馮氏的所謂“氣”者矛盾了。這個矛盾的弱點,也許是馮氏所感到頭痛的。他在《新理學》中,就說過如次的話:
“氣至少必有‘存在之性,……他至少須依照‘存在之理……”
“……因至少‘存在之理,是常為氣所依照者。”(第七十五頁)
“氣又至少必依照動之理。我們于上面說,氣之依照理者,即成為實際底事物,依照某理,即成為某種實際底事物。‘依照是一事,亦即是一動。故氣于依照任何理之先,必須依照動之理,然后方能動而有‘依照之事。否則氣若不動,即不能有依照之事。”(第八十五頁)
到了《新原道》,他雖以“實現”代替“依照”,但是這個問題還是沒法解決。到了不能解決問題的時候,他就索性乞靈于神秘主義。
馮氏說:“理及氣是人對于事物作理智底分析,所得底觀念。道[體]及大全是人對于事物作理智底,總括所得底觀念”(《新原道》第一一九頁)。但是翻過下一頁,他便宣布大全,道體及氣都是“不可思議”“不可言說”的觀念了。請看他說:
“嚴格地說,大全的觀念,與其所擬代表者,并不完全相當。大全是一觀念,觀念在思中,而此觀念所擬代表者,則不可為思之對象。大全既是一切底有,則不可有外。……如有外于大全者,則所謂大全,即不是大全。……如以大全為對象而思之,則此思所思之大全,不包括此思。不包括此思,則此思所思之大全為有外。有外即不是大全。所以大全是不可思議底。大全即不可思議,亦不可言說,因為言說中,所言說底大全,不包括此言說。不包括此言說,則此言說所言說之大全為有外……。不可思議,不可言說者,亦不可了解。不可了解,……只是說其不可為了解的對象。”
“由此方面說,道體亦是不可思議,不可言說底。因為道體是一切底流行。思議言語亦是一流行。思議言語中底道體,不包括此流行。……即不是一切底流行。……即不是道體。”
“氣亦是不可思議,不可言說底。不過……與大全或道體之所以是如此不同。……氣所以是不可思議,不可言說底,因為我們不能以名名之,如以一公名名之,則即是說它是一種甚么事物,說它依照某理。但它不是任何事物,不依照任何理。所以于新理學中,我們說:我們名之曰氣。我們說:此名應視為私名。但形上學并非歷史,其中何以有私名;這也是一困難。所以名之以私名,亦是強為之名。”(第一二〇頁)
所謂“不能以名名之”,實質上還是關涉到上面所說的邏輯上那個矛盾的弱點的困難。予此,可見馮氏的系統是以“理智的分析”“總括”始,而以“神秘主義”終,這是所謂“理智”的破產,也是所謂“現代的新邏輯學”不可避免的破綻!
四
馮氏一方面喜愛玄虛,但另一方面卻不能忘情于世務。所以既主張“極高明”又強調著“道中庸”。他在《新原道》說:“新理學中底幾個重要觀念,不能使人有積極底知識,亦不能使人有駕馭實際底能力。但理及氣的觀念,可使人游心于‘物之初。道體及大全的觀念,可使人游心于‘有之全。這些觀念,可以使人知天,事天,樂天,以至于同天。這些觀念,可以使人的境界不同于自然,功利,及道德諸境界。”(第一二二頁)所以,他自夸“它(新理學)所講底,還是‘內圣外王之道,而且是‘內圣外王之道的最精純底要素。”(第一二三頁)這就告訴你:只要你想學做圣人,你就得學會他那一套“最玄虛的哲學”——“新理學”。因為:依他說,圣人是“在天地境界中底人”。天地境界,他分為四個遞升的階段:“知天,事天,樂天,同天”。人要做到至圣,就要能夠處于“同天”的境界。首先就要“知天”,要“知天”,就必須了解“新理學中底幾個重要觀念”。因為所謂“天”,就是“大全”,而“理,氣,道體”等,則為了解“大全”的預備觀念。現在先從《新原人》中引他一段解釋“同天境界”的文字:
“在天地境界中底人的最高造詣,是,不但覺解其是大全的一部分,而并且自同于大全。如莊子說:‘天地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死生終始,將如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得其所一而同焉,即自同于大全也。一個人自同于大全,則‘我與‘非我的分別,對于他即不存在。道家說:‘與物冥。冥者,冥‘我與萬物間底分別也。儒家說:‘萬物皆備于我。大全是萬物之全體,‘我自同于大全,故‘萬物皆備于我。此等境界,我們謂之為同天。此等境界,是在功利境界中底人的事功所不能達,在道德境界中底人的盡倫盡職所不能得底。得到此等境界者,不但是與天地參,而且是與天地一。得到此等境界,是天地境界中底人的最高底造詣。亦可說,人唯得到此等境界,方是真得到天地境界。知天事天樂天等,不過是得到此等境界的一種預備。”(《新原人》第九十六頁)
這種見解,只是揉雜莊孟的思想而以之附會其所謂“大全”罷了,并沒有一點兒“新”的因素在里面的。那末,怎樣才能得到“同天境界”呢?他的方法,還是用“思”。他說:
“或可問:人是宇宙的份子。即對于宇宙人生有覺解者,亦不過覺解其是宇宙的份子。宇宙的份子,是宇宙的一部分,部分如何能同于全體?”
“于此我們說:人的肉體,七尺之軀,誠只是宇宙的一部分。人的心,雖亦是宇宙的一部分,但其思之所及,則不限于宇宙的一部分。人的心能作理知底總括,能將所有底有,總括思之。如此思即有宇宙或大全的觀念。由如此思而知有大全。既知有大全,又知大全不可思。知有大全,則似乎如在大全之外,只見大全,而不見其中的部分。知大全不可思,則知其自己亦在大全中。知其自己亦在大全中,而又只見大全,不見其中底部分,則可自覺其自同于大全。自同于大全,不是物質上底一種變化,而是精神上底一種境界。所以自同于大全者,其肉體雖只是大全的一部分,其心雖亦只是大全的一部分,但在精神上他可自同于大全。”(《新原人》第九十六至九十七頁)
偉哉,“思”也!只要那么一“思”,便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就可“在精神上”“自同于大全”,就可處于“同天境界”,真可說是廉價的“精神勝利法”了!但是不成。依他說:“嚴格地說,大全是不可思議底。”“不可思議底亦是不可了解”的,就是說,大全“不可為了解的對象”。因為“大全無所不包,真正是‘與物無對,但思議中底大全,則是思議的對象,不包此思議,而是與此思議相對底。所以思議中底大全,與大全必不相符。……所以對于大全,一涉思議,即成錯誤。”(《新原人》第九十八頁)那么,所謂“由如此思而知有大全,……知有大全,則似乎如在大全之外只見大全,而不見其中的部分,……則可自覺其自同于大全”云云,不成錯誤,便是戲論。這是一。依他說:“新理學雖說: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即是‘總一切底有,謂之大全。大全就是一切底有。——素)但并不肯定,一切事物之間,有內部的關聯或內在底關系。新理學所謂一,只肯定一形式底統一。”(這也是他的形式主義在作祟。——素)如此,即使人可能“自同于大全”,又怎能使人發生“與物渾然一體”之類的情感而出于實踐?這是二。
在《新原人》中馮氏又援引佛家的“證真如”或道家的“得道”為證,說“‘證真如的境界以及‘得道的境界,都是所謂同天的境界。”(《新原人》第九十七頁)但是佛家的所謂“真如”與道家的所謂“道”,都是指所謂“本體”說的(所謂“本體”是有內容的,不是形式的。——素)。所以在“理論”上到了“證真如”和“得道”的境界,精神與本體合一,便算“證”了“得”了,雖然實際沒有所謂本體,但話還說得過去。而在“實踐”上,他們可以玩弄精神去求“證”求“得”。正如顏習齋所說:“今使竦起靜坐,不擾以事為,不雜以傍念,敏者數十日,鈍者三五年,皆可洞照萬象如鏡花水月;做此功至此,快然自喜,以為得之矣。”(《存人編》)這種仿佛迷離的自己催眠訓練得來的境界,自可以自欺欺人,自“以為得之”。但在主張純“形式底觀念”的馮氏,又怎能援引他們來相比擬呢?即以儒家而論,就是說過“萬物皆備于我”的孟子,關于仁,也還說是“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與孔子所說的仁為“愛人”一致。也“仁民”與“愛物”有別,不是籠統地說“仁”,而是推己及人,由近而遠的。由這種“推己及人”的想法,也可能發生“痛癢相關的情感”。張橫渠所謂“民吾同胞,物吾與也”,還有孔孟的余風。其所謂“乾稱父,坤稱母”,“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之類,猶是利用這種家人長幼的觀念,去引起其人的“痛癢相關的情感”。至于程明道所謂“仁者渾然與物一體”的說法,早已深受二氏(道釋)本體論的影響,而把“仁”看成仿佛二氏所謂“道”或“真如”的東西。不是孔孟所謂“仁”。這樣地了解“仁”尚可勉強地說“仁者渾然與物一體”。但在馮氏,其所謂“理智底總括”所得來的“大全”這一觀念,則只是一個“空底觀念”。既無內容,也“并不肯定,一切事物之間,有內部底關聯或內在底關系”,又怎能使人“思”它一下,便發生趨赴實踐的“情感”呢?所以,附會也無用處,形式的觀念,究竟不能引起熱烈的情感。
馮氏似乎也感到這種弱點,所以,索性承認“同天地境界,本是所謂神秘主義底。”(《新原人》第九十八頁)可是對于“理智”猶有余變,終于又作了一個神秘的聲明,“不可思議底,不可了解底,是思議了解的最高底收獲。哲學底神秘主義是思議了解的最后底成就,不是與思議了解對立底。”(《新原人》第九十八至九十九頁)我覺得這樣說或許更真實些:即神秘主義是形式主義最后的歸宿。
但是實踐的問題,還是要解決的。所以他說:“哲學雖有如此底功用(即‘可以使人知天事天樂天以至同天的功用。——素),但只能使人知天,可以使人到天地境界,而不能使人常住于天地境界。欲常住于天地境界,則人須對如此底哲學底見解,‘以誠敬存之。”(《新理學》第一一七頁)這種神秘主義的境界,除了利用宗教性的信仰的辦法“以誠敬存之”之外,也就難得“常住”的了。他在另一地方也露出了馬腳,他說:“如用一名以謂大全,使人見這可以起一種情感者,則可用天之名。”(《新理學》第三十八頁)原來如此!
五
馮氏的哲學,不但無力指導人生,而且也無力促進科學。這也是他“過河拆橋”的方法論之必然的結果。凡是能夠指導科學的哲學,必定是概括了以前科學所達到的成果,而且不斷地在吸收它們的新成果的哲學。這樣,哲學就不能“不管事實”,不能“不著實際”。要管事實,要著實際,它的方法就得從實際概括得來,才能與實際運動的規律和諧一致;它的理論就要經得起實際的考驗,才能一步步接近客觀的真理。這樣的哲學方法,同時也就是科學的方法。這樣,才真正是“一行”,而不是“兩行”。
然而“新理學”的方法,卻是“過河拆橋”的方法。它雖也從經驗出發,但“既已得之(觀念等)之后,即見其并不另需經驗以為證明”,便舍棄經驗,脫離現實。它的觀念命題都是“空底”無“內容”的,所以由它看來,人便成為抽象的人,既是“人之所以為人”的人,把人的社會歷史的性質抽“空”了。由它看來,事物的運動,也只是抽象的“一動”,它們到底怎樣地動,它是不管的。這種方法,對于科學是無能的,是和科學的方法相反的。但是馮氏卻得意地說:“老子作為道與為學的分別,講哲學或學哲學,是屬于為道,不屬于為學。”(《新原道》第一二一頁)因此他認為哲學,與科學的知識不在“同一層次之內”:“科學底知識,雖是廣大精微,但亦是常識的延長,是與常識在同一層次之內底。”(《新原道》第二十二頁)又說:“哲學與科學不同,在于哲學底知識,并不是常識的延長,不是與常識在同一層次上底知識。”(《新原道》第二十四頁)這樣,他的玄學與世務的矛盾,終于發展成為他的“新理學”與科學的矛盾了。于是他武斷說:“凡哲學(其實只是玄學——他的新理學——素)都是‘失人情底。因為一般人所有底知識,都是限于形象之內,而哲學(玄學。——素)的最高底目的,是要發現超乎形象者,哲學(玄學。——素)必講到超乎形象者,然后才能合乎‘玄之又玄的標準。”(《新原道》第三十七頁)其實哲學并不是“失人情”的,真正的哲學也不需要講到“合乎“玄之又玄”的標準”。他這樣說只是因為他自己的哲學方法是和科學方法相反的玄學方法。治哲學是一套方法,治科學又是另一套方法。所以,他的所謂“極高明”與“道中庸”,畢竟還是“兩行”不是“一行”。故雖“而”了,但仍不能使它們統一。就是說,馮氏的“新理學”,對于他所見的“高明與中庸的對立”的問題,也并沒有解決。
他這種玄學的方法,對于科學是無能的最好的標本,就是他的《新原道》。這本著作,目的在于建立一個新道統,即“欲述中國哲學主流之進展,批評其得失,以見新理學在中國哲學中之地位。所以先述舊學,后標新統。異同之故明,斯繼開之跡顯。庶幾世人可知新理學之稱為新,非徒然也。”(《新原道》自敘)其所以以中國哲學史論的姿態出現,無非想借歷史的“敘述”,以證明其正統之獨承。所以他說:“中國哲學的精神的進展,在漢朝受了逆轉,……到玄學始入了正路。……在清朝又受了逆轉,……到現在始又人了正路。我們于本章(即《新統》章。——素)以我們的新理學為例,以說明中國哲學的精神的最近底進展。”(《新原道》第一一三頁)這就是說:到了“新理學”,“中國哲學的精神”才“又入了正路”。這是何等武斷!這是何等僭妄!
照常理論,歷史既經成為一種科學,哲學史乃至哲學史論,都不應在例外。在馮氏,既認為科學的知識和哲學的知識不同,不在“同一層次之內”,治中國哲學史自應該用科學的方法,從中國哲學的史實出發,概括出各個思想派別,追蹤它們的遞嬗發展,借以發現中國哲學史發展的規律,然后可以“批評其得失”。這樣,我們才能得到一部科學的中國哲學史。可是馮氏在《新原道》中怎樣做了呢?他卻用他的形上學的觀點,去割截中國哲學的史實,以適合他建立落后的道統的企圖,凡中國哲學史實可以附會歪曲者則附會歪曲之,不能附會歪曲者則抹殺拋棄之。結果,他這本《新原道》,雖然附標著“中國哲學之精神”的標題,但實際至多只能說是表現“中國玄學之精神”的玄學史論(我說“至多”,因為他對于中國玄學家也不無曲解之處。——素)。證據呢?有的是。例如:關于儒家,附會孔子所謂“天”為他所謂“知天”的“天”,明明儒家是“于實行道德中求高底境界”(《新原道》第一十八頁),他卻“知天,事天,樂天,同天”地附會得不亦樂乎。而對于后期儒家的大師荀子,則抹殺不談。次如名家,只敘述公孫龍的學說,對于戰國后期名學如《荀子》《墨辯》之類,只得毫無內容的二十七個字。至于整個時代被抹殺拋棄者,則為漢朝和清代,幾乎使中國學術歷史四分之一變成了空白。他的理由很簡單,就是漢人的思想,“都不能超以象外”;“清朝人很似漢人,他們也不喜歡作抽象底思想,也只想而不思。”于此可見《新原道》作者是多么富于武斷附會的勇氣。于此可見玄學的方法論怎樣有害于學術。至于指導科學,談也不要談了。
如果我們舍去這種“經虛涉曠”的玄學作風,采取“實事求是”的科學立場,則由科學到哲學,由常識到理論,由人生觀到宇宙觀,一句話說,由為學到做人,都可以用一貫的科學的方法去從事的。比方說,人們以“實事求是”的精神,研究自然,一樣地可以認識自然是偉大的,知道了其中各部分的聯系,便可以根據物質運動的法則,去征服自然,使它替人類服務。人們以“實事求是”的精神,研究社會,一樣地可以知道社會是進化的,知道了它的發生和發展的途徑,便可應用社會的運動的規律去改造社會,使它更適于人類的繁榮。……這樣地得來的知識,這樣地得到的宇宙人生觀,對于人們做人做事上的幫助,總要比“最哲學底哲學”有力。有內容的知識,自然能夠使人們的服務的情感更熱烈,使人們奮斗的意志更堅強,絲毫用不著那種“以誠敬存之”的宗教式的修養方法;因為人們在為學做人的過程中,便已同時是在修養了。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八日于上海
責編:梁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