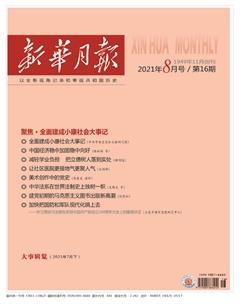王元:純粹數學的美麗與哀愁
宋春丹
5月14日,中科院院士、中科院數學所原所長王元在北京病逝,享年91歲。
在中科院數學所里,人們都稱呼王元為“元老”。一則出于其名,二則因為他在中科院數學所剛成立時就入職,是中國數學界尤其是數論方向的先驅人物。
王元曾說,好的數學與好的藝術一樣,美學是第一標準。在他看來,數學美的本質在于簡單,如中國古人論文:理當則簡,品貴則簡,神遠而含藏不盡則簡。
曾任中國科學院數學與系統科學研究院研究員、與王元有過20年合作的方開泰告訴記者,王元擅長用簡單語言描述復雜問題,即“大道至簡”。
方開泰說,華羅庚、王元、潘承洞、陳景潤是中國數論研究的一支梯隊,將哥德巴赫猜想研究做到了目前世界最好的水平。數論研究的特殊在于,可能做了幾十年也拿不出成果。方開泰自己從事的統計學領域有大問題有小問題,都能發表論文,只是雜志層次不一樣而已,而數論領域要么是重大突破,要么是零。搞數論既賺不到錢,通常也“沒用”,但一旦有用就是大用。
王元曾引述英國數學大師哈代(華羅庚在劍橋大學深造時曾師從哈代)的一句“絕話”:沒有應用的數學才是好的,好就好在它沒有應用,否則它就變成其他學科的附庸,沒有獨立存在的必要了。
“哥德巴赫猜想”天團
“哥德巴赫猜想真是美極了,現在還沒有一個方法可以解決它。”
1953年,華羅庚在自己舉辦的哥德巴赫猜想討論班上對學生如是說。這種討論班是國外很普遍的一種教學方法。華羅庚說,辦這個班并不是要他們在這個問題上做出成果來,而是因為哥德巴赫猜想跟解析數論中所有的重要方法都有聯系,可以以此為切入點來學習。
討論班由學生輪流報告指定的論文,華羅庚則不停地提問,有時主講人被問得講不下去,只能長時間站在講臺上思考,這叫做“掛黑板”。有些報告材料在討論班上就得到了簡化,所以討論班進行得很慢,但參加者收獲很大。

年輕的王元每天工作16個小時,辦公室和寢室合二為一。他形容自己像初生牛犢一樣硬沖,卻一無所獲,一度陷入自卑和動搖。那種感覺,就好像一個人困在一間黑屋子里,看不到一點光,不知道門在哪里。
1954年,波蘭數學家訪華,帶來了一些波蘭數學家的論文,當晚王元就用布倫方法改進了其中關于數論函數的一篇論文的部分結果。波蘭數學界很重視,要求與他合發論文。當時正值中央向全國提出“向科學進軍”的口號,這件事被國內媒體大張旗鼓地宣傳。
嘗到甜頭的王元還想多發幾篇論文,華羅庚提醒他:“搞數學研究就像是賽跑,要有速度,還必須有加速度。”這個提醒讓他沒有為路邊的一時風景而停駐。
堅持獲得了回報。在華羅庚的指導下,他將西方數學家塞爾貝格的篩選方法與蘇聯數學家布赫夕塔布的迭代法結合起來,改進了布赫夕塔布1940年的證明結果“4+4”,于1955年成功證明了“3+4”。此后他再接再厲,又于1957年春證明了“2+3”。這是當時世界上最好的證明結果。這時,王元才26歲。
華羅庚很高興,說:“真想不到你在哥德巴赫猜想本身就做出成果了,你要是能再進一步就好了。如果不能,你這輩子也就是這樣了。”沒想到一語成讖,王元此后在攻難題方面沒能再進一步。
中科院數學所原副所長李文林告訴記者,王元是第一個走到哥德巴赫猜想研究前列的中國數學家。他最大的特點是會審時度勢,能在適當的時候選擇正確的研究方向,這既出于對自己的正確估計,也出于對科學形勢的準確判斷。而這對于一個數學家而言至關重要。
華羅庚原本計劃討論班分四個單元,但只完成了前三個單元,“反右運動”就到來了。
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華羅庚在張勁夫等中科院領導的保護下過關,但從此在數學界被看成“漏劃右派”靠邊站了。在之后的“拔白旗、插紅旗”運動中,他又成為數學所集中批判的“大白旗”。他從廈門大學調來的陳景潤則成為最頑固的“小白旗”之一,被發配到中科院大連化學物理所“刷試管”,1962年氣候回暖后才在華羅庚支持下調回。
經常來參加華羅庚的哥德巴赫討論班的還有北大數學力學系研究生潘承洞。1960年他研究生畢業,王元猜測他可能已成為內部掌握的“小白旗”,因此北京沒有單位要他,分到了山東大學。
王元說,華羅庚的討論班與英國數學家達文波特的討論班在數論方面處于同一水平,達文波特的討論班出了三個菲爾茲數學獎得主,華羅庚的討論班卻過早夭亡。如果當時有條件從全國各地選拔人才,應該能出更多的人才。
數論組被取消,人員流散,只有少數人私下堅持“理論脫離實際”的純粹數學研究,尤其是陳景潤和潘承洞。
1962年,潘承洞對匈牙利數學家瑞尼的研究工作做了改進,試圖證明“1+5”。他不斷給王元寫信,告知自己的研究進展。
王元說,潘承洞心胸開闊,淡泊名利,不與人爭,在數學界有口皆碑,他很喜歡與潘承洞交往。但他對潘承洞的證明是懷疑的。他說,一個數學家做了一件研究工作而受阻后,往往不會輕易相信這方面的進展,這是對自己的迷信和偏見,他在證明了“2+3”后就陷入了這種“思維怪圈”。
他對潘承洞的證明提出質疑,潘承洞則加以解釋,彼此的信都寫得很長。那段時間潘承洞給自己的未婚妻只寫了兩封信,卻給王元寫了60多封信,可見“拼搏之激烈”。
最后,在無可爭辯的情況下,王元承認了潘承洞的證明結果。1963年,潘承洞又證明了“1+4”。
與王元和潘承洞不同,陳景潤喜歡一個人鉆研。華羅庚熟知弟子們的秉性,曾說“就讓他一個人去搞”。1965年,陳景潤的工作有了突破性進展:他用篩法證明出了“1+2”。
1965年蘇聯數學家阿· 維諾格拉多夫和意大利數學家龐比尼分別證明了“1+3”,不僅奪走了中國人的紀錄,而且人們普遍認為,用篩法證明“1+3”已經到頭了。但陳景潤硬是對篩法“敲骨吸髓”,證明出了“1+2”。國外證明“1+3”用的是高速計算機,而陳景潤是單槍匹馬,完全用手工計算的。
陳景潤請王元和北大教授閔嗣鶴審閱論文。
王元立即明白了陳景潤的想法,只有關于阿· 維諾格拉多夫定理的證明這一處沒有看懂(事實上后來維諾格拉多夫修正了自己的證明),因此認為需要慎重一些。
閔嗣鶴1954年曾在北大數學力學系開設數論專門化班,潘承洞就是這個班上的學生。閔嗣鶴常鼓勵學生去參加華羅庚的數論討論班,數學所數論組的年輕人也把閔嗣鶴看成老師。當時已重病在身的閔嗣鶴冒著心臟病隨時發作的危險夜以繼日地演算,審閱了這篇長達200多頁的論文,并鄭重寫下:命題的證明是正確的,論文篇幅過長,建議加以簡化。
關肇直也支持陳景潤發表證明結果。王元在《華羅庚》里寫道,作為黨派往數學界的領導干部,關肇直的影響力與華羅庚相當或僅略次于華羅庚,他們既有合作又有矛盾,矛盾被傳聞夸大了一些。關肇直以前一直不支持研究經典數學,認為這是少數數學家的脫離實際的狹小圈子興趣,至多不過是一種智力游戲而已,哥德巴赫猜想尤其如此。但這次正是他極力支持發表陳景潤的成果。許多人感到不解,王元認為,可能關肇直內心深處對經典數學的看法存有矛盾,或許還懷疑有人壓制陳景潤,因而覺得應該出來主持公道。
陳景潤搭上了“末班車”。1966年5月15日出版的《科學通報》公布了他的證明結果(論文并未發表),這期之后就因“文革”的到來而停刊了。
“文革”十年
1966年8月20日,數學所召開了批判華羅庚的大會。事前數學所革委會籌委會負責人召集華羅庚的學生越民義、萬哲先、陸啟鏗、吳方和王元開會,要求他們作一個聯合發言,并指定萬哲先起草發言稿,王元來念。
也有人找陳景潤做工作,要他在會上講一講怎么被引上“白專道路”的,說他作為“修正主義苗子”也是受害者,現在覺悟還不晚。但陳景潤遠遠躲開了。他后來說,自己當時也分不清誰對誰錯,反正什么話都不多說一句。
王元認為,數學家不怪才是正常的,陳景潤的“怪”是當時的政治氣候造成的。他看似整天“神魂顛倒”,實際上是用裝傻來保護自己,始終頑強地堅持研究工作。
一個運動接一個運動,王元已經多年不進圖書館,不讀書,也不看數學雜志了。直到“九一三事件”后,人們才從狂熱走向冷靜,悄悄鉆進業務之中。1972年,部分學術雜志開始恢復出版。
1973年,陳景潤將他經過七年打磨的論文全文投給《中國科學》。論文被送交閔嗣鶴和王元審查。
王元看到,陳景潤已將原有論文作了相當的簡化。200多頁的論文,只剩下不到30頁。論文的證明結構易于了解,但為慎重起見,王元讓陳景潤從早到晚給他講了三天。陳景潤在黑板前講,他不斷地提問,直到每一步都清楚無誤。
王元在運動中被打成“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反革命小集團”成員之一,陳景潤是“白專典型”,支持論文的發表是有風險的,但經過反復思考,王元寫下了審稿意見:“未發現證明有錯誤。”
他后來坦言,如果不是政治形勢所迫,這句話其實遠遠不夠。當時沒有給陳景潤的論文以充分的評價,一直是他心中的一大遺憾。
1974年,英國數學家哈勃斯坦和西德數學家李希特合著的《篩法》一書出版,在付印前加入了“陳氏定理”作為最后一章,并且寫道:“從篩法的任何方面來說,它都是光輝的頂點。”
1978年2月,全國科學大會召開前夕,《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了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陳景潤一夜成為民族英雄。
1982年,因對哥德巴赫猜想證明工作的貢獻,王元、陳景潤和潘承洞共同分享了“文革”后首屆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這是中國解析數論學派的鼎盛一幕。方開泰說,王元、潘承洞和陳景潤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上如同接力,一個比一個做得更好。
只是華羅庚本人,卻再也沒有回到數論領域。
早在1965年王元就發現,華羅庚的心思已不在純粹數學上,對研究數值積分這種應用數學也一點興趣沒有了,而是一心撲在向工農兵群眾宣傳“雙法”(即以改進工藝為主的“優選法”與改善組織管理的“統籌法”)上。他事前沒有跟任何人商量,突然就決定了。
一位法國數學家曾說:“一種數學理論應該這樣清晰,使你能夠向大街上遇到的第一個人解釋它。在這之前,這種數學理論還不能認為是完善的。”但只有華羅庚真的嘗試這樣做。他的足跡遍及全國,推廣“雙法”。為了讓普通工人能明白,他對這兩種方法作了簡化,以最易懂的語言進行講解。王元等學生都不愿意放棄自己的工作追隨他,他也表示諒解,自己義無反顧地干了近20年。
但華羅庚對純粹數學的愛并不是真的消退了。王元記得,“文革”中華羅庚有次住院時曾有過一點關于哥德巴赫猜想的想法,他希望王元和潘承洞與他合作,二人均未回應,因為都深知個中滋味。
“文革”結束后,華羅庚又萌發了將學生調到一起搞純粹數學的念頭,但思考之后放棄了。他不無感慨地說:“其實,過去我把你們組織起來,一邊搞普及一邊搞理論,還是有可能的。現在當然不談了。”
為華羅庚做傳
1982年,胡耀邦給華羅庚回信,建議他工作不可過重,可以寫寫回憶錄,把一生為科學奮斗的動人經歷留給后人。王元主動提出要執筆此書,他認為只有自己對恩師尤其是對他的數學工作最為了解。
1985年,華羅庚身體已相當虛弱。他把王元叫到家中,遞給王元一份自己草擬的傳記參考提綱,上面主要是他的數學工作。不久,他就去世了。
王元覺得,傳記如果這樣去寫,可能只會對數學工作者有些參考價值,一般人是不會去讀的。他決定要盡可能全面地寫,包括歷史背景以及華羅庚的歡樂、彷徨與劫難。
為了不受任何約束,他沒有申請任何經費,沒有與出版社簽約,也不找助手,而是獨自一人開始寫作。他只能利用業余時間寫,計劃每年寫出一至兩章。
那時沒有上網條件,所有材料都是他在圖書館里一點一點搜集的。他還利用到香港中文大學訪問的機會查資料。整個過程如同大海撈針。
這本書他寫了兩稿,第一稿約40萬字,寫完后全部推倒重來。這是他的習慣,第一稿只是理清思路和建立框架,第二版才可定稿。
對當時的人和事,他都反復加以核實,務求真實。對一些敏感問題,他也沒有回避,包括自己參與念批判稿的那段歷史。他寫道,雖然這在“文革”中實屬小事,連華羅庚本人也早忘記了,但他自己每每想起這件事就覺得無限內疚。他說:“作為學生對恩師的攻擊,即使是為了保命亦終究是可恥的。”
他還探討了華羅庚在盛年從學術主流退出、20年如一日搞數學普及之謎。他認為,華羅庚的選擇并非一時的權宜之計。華羅庚在“文革”中雖然也受到了批斗,但很早就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保護,完全可以關起門來在家搞純數學,但他的決心并沒有動搖。
王元說,華羅庚深知做數學理論研究工作是何等困難,對年紀大的數學家尤其如此。“數學家大致到35歲為止”是一句人所共知的魔咒,華羅庚的老師哈代就說過:“比起任何其他藝術或科學,數學更是年輕人的游戲。如果一把年紀的人喪失了對數學的興趣并將它拋棄,由此造成的損失對數學和他個人而言都不會很嚴重。”
早在20世紀50年代華羅庚就曾感嘆,一個數學成果要在歷史上留下來是多么難,有時候整個數學領域都會被淘汰掉。他在一篇“檢討”中寫道:自己的保守思想與在科學研究工作上走下坡路是分不開的,每年看的文章不過一二十篇,學術思想水平停滯在三四十年代。
王元覺得,這些話多少反映了華羅庚的心境。對此,他自己也頗有體會。他曾告訴記者,做科學是極端殘酷的,做不出來時人會有要瘋掉的感受。做完哥德巴赫猜想“2+3”的證明后他想好了退路:這個成果夠他“用”五年時間,五年以后做不出新的成果,他就去大學教書了,哪怕是一所外地的三流大學。
只是那時他可能萬萬沒有想到,他會花近10年時間,來為老師寫一本傳記。
1994年,30萬字的《華羅庚》由開明出版社出版。
“如果停止學習,名氣再大也一錢不值”
方開泰回憶,他與王元的合作開始于1975年。
那年,冶金部委托所屬北京鋼鐵研究院鑒定合金結構鋼國標的合理性,因為要處理復雜的生產數據,鋼鐵研究院求助中科院數學研究所,方開泰參加了該項目。這項研究需要計算大批五重積分,如果用傳統方法,當時的計算機速度幾乎不可能實現。
方開泰想到了華羅庚與王元1965年合作發表的《積分的近似計算》,這種高維求積公式的數論方法在國際上被命名為“華-王方法”。他向王元求教,王元從書架上拿出一本論文集,向他詳細講解了算法簡單的“好格子點法”。方開泰試驗后,對這種高效方法欽佩不已。
1978年,七機部三院的工程師在三個導彈指揮儀的項目中遇到困難。受計算機運算速度所限,解微分方程組需要一天時間,遠遠達不到實際需要。方開泰想到數論方法可能有幫助,就找到王元,王元同意共同開發,約定每周見面討論一次。
三個月后,王元和方開泰算出了第一批“均勻設計表”,在內部資料《概率統計通訊》上發表,同時向《應用數學學報》投稿。投稿時,王元堅持用方開泰一人名義,不參加署名。
作為兩人合作成果的“均勻試驗設計的理論、方法及其應用”2008年獲得了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一等獎空缺),被認為開創了一個新的研究方向。
1983年,張壽武考入中科院數學所攻讀碩士學位。當時,王元認為自己研究的經典解析數論已難有出路,鼓勵張壽武自由選擇方向,他選擇了當時國內少有人問津的算數代數幾何問題。王元對這個領域并不熟悉,但是他給予了張壽武足夠的自由和鼓勵,只是告訴他該怎樣做研究。

張壽武碩士論文答辯時,王元說:“我也不知道你在說些什么,一個字也聽不懂,但考慮到你每天很早就來辦公室,很用功,這個碩士學位就送給你了。”
后來成為新一代華人數學家領袖的張壽武評價自己的導師王元是一位“極為開明的”老師,度量、氣派了得。王元則說,其實后來張壽武是自己的老師,自己總是向他請教。因為如果不去關注、學習前沿的新東西,那名氣再大也一錢不值。
除了中科院研究員,王元幾乎沒有社會兼職。1984年他擔任了中科院數學研究所所長,與副所長楊樂一起,使數學所成為中科院對全國開放的兩個所之一,廣泛邀請國內的訪問學者和進修人員來所工作。但他堅持只做一屆,1987年就不再擔任所長職務。他是最早申請退休的院士之一,也是主動提出不連任的政協委員。
20世紀80年代,王元和潘承洞常常有機會見面。有一次,解析數論學者十幾人去青島進行學術交流。王元回憶,每天看著潮起潮落,平靜時,海天一色,孤舟點點;風起時,驚濤拍岸,聲若悶雷。潘承洞是高度近視,王元會扶著他去海邊散步。兩人常常憶起當年書信交鋒、一起攀登哥德巴赫猜想高峰的幸福時光。
王元是全國政協委員,潘承洞是全國人大代表,開兩會時,兩人就約好在人民大會堂進門休息廳的右側見面。開院士會時,則共住一間,一起聊聊天。
晚年,王元因心臟、前列腺等疾病動過幾次手術,為了恢復健康,他從1996年開始練書法。他從臨顏真卿、柳公權,再到專臨王羲之、王獻之、毛澤東,還向書法家歐陽中石求教。他每天早晨5點起床練字,冬夏不輟。
1996年3月18日晚,陳景潤病危。王元和楊樂趕到北京醫院去看陳景潤,這是他們的最后一面。第二天中午,陳景潤與世長辭。
王元在致中科院學部聯合辦公室的信中說:“景潤兄走了,四十年相處,常記于心。”他說,自然科學是英、美、俄的“領地”,他們十分傲慢,對發展中國家甚至日本采取歧視態度,在學術論文中提到他們以外的工作已不容易,在專著中提到就更難了,若在教科書上提到,則除非不提就不行了。而陳景潤的工作是在他們的大學教科書上被提到、在他們的專著上寫出全部證明的,是永留史冊的。
1997年底,潘承洞也去世了。王元在《回憶潘承洞》中寫道:“陳景潤才走了一年多,潘承洞又走了,留下了一片空白,一片凄涼。”
現在,王元終于又跟他們在一起了。他們可以在數學熱愛者與卓越者的圣殿里,沒有阻隔地共享數學的純粹與永恒之美。
(摘自《中國新聞周刊》2021年第19期。作者為該刊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