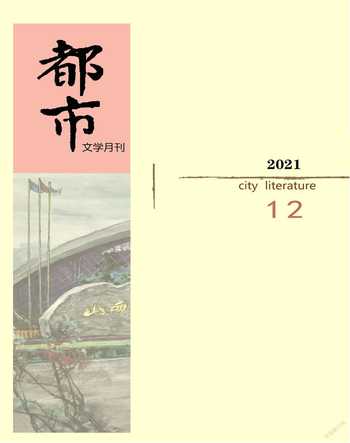人性的不徹底和幾乎無事的悲哀
郭劍卿
是的,《秋季到太原來看雨》(原刊于《都市》2021年第11期)這篇小說會讓你聯想到那首老歌。“潮濕清冷的街頭,踽踽獨行的孤獨者。”可是我們的主人公走不進戴望舒春天的雨巷,臺北冬季的憂傷浪漫更是遙不可及。一個北方黃土高原的內陸城市,景觀原本乏善可陳:春天是風沙,夏天少雨,秋季呢,金色樹葉飄落的時候還有些詩意。這個時候,偏偏作者讓你“來看雨”,這是一種怎樣的心情?敘述者“我”哼著那首篡改了歌詞的舊曲,引我們走進這個下雨的秋季,走近我們的主人公。他的人生樣貌大致由“我”的敘述加上同事的議論勾勒出來。作者截取的橫切面選擇了王晉偉42歲生涯中的兩件大事:買房和結婚。一個農村出身的“北路家”,靠自己18年的省吃儉用在省城的黃金地段擁有了一套新居。王晉偉可謂“成功人士”,由此贏得“我”的刮目相看:“人家單憑一己之力就在上風上水地段置辦下了新房,又焉能妄自斷言人家不會贏得肖麗萍的垂青?”然而,暗戀18年、精心策劃的求婚大戰遭遇“滑鐵盧”,按照王晉偉的性格邏輯和生活軌跡,他的失敗有理有據水到渠成。
小說一開始,作者就給了王晉偉一堆頭銜:“一名未婚青年,一條光棍漢,一位大齡單身知識分子,一員擇偶困難戶,一個選擇性心理障礙者”,這頭銜沒有一頂是可炫耀的,統統指向一個失敗者的人生意象,增加著他的失敗指數。木訥內向、朋友很少,是個令人費解的角色。一個看上去很正常的世界里,他是眾人眼里不正常的怪人。最怪的莫過于相親時請對方一人進餐并且開發票給他報銷;相親不成向對方索賠巧克力,以致讓同事大跌眼鏡:“天哪,我真弄不懂他到底是個啥人。天底下還有這樣做事的嗎?”如此下來,“我”不得不毫不留情地對他直言相告:“42歲的人了,奔‘五張的人了,愛情一片空白,婚姻無從談起,人們都咋看待你?是不是心里沒數?要是真不知道,要是你心里真沒數,那我現在可以代表大家告訴你:你是個古怪的人,你不是一個正常人,把話再說得難聽點,你就是個不正常的人。”從小說美學的角度看,這樣直白的寫法并不討好,王晉偉的“乖僻”惹怒了作者,竟使作者忘記了應該隱藏自己的態度,好在,我們的主人公早已麻木不仁,“他望著我苦笑一陣,像喝酒一樣舉起茶杯一飲而盡”。
以往的小說中,劉寧小說的主人公們生活的空間聚集在城市的邊緣地帶,修車攤、燒烤攤、小賣部、理發店、按摩店、殯儀館,賣花鳥魚蟲的椅角旮旯,養鴿戶居住的頂層舊樓;小人物的卑微悲涼愛恨生死,構成了劉寧筆下的“傳奇”。這篇小說中的主人公某些方面算得上“成功人士”,工作認真且多次評優獲獎,已經解決了中級職稱,正在向副高“而奮斗”;然而從另一方面看,王晉偉依然屬于“乏善可陳”的“邊緣人”。他的生活圈兒很小。如他所言:“你知道的,我這個人,能信賴的朋友不多。”人際交往僅限于學校同事和他所教的那個班級。不抽煙不喝酒不吃肉不請客穩穩攢錢買房,終于從單身宿舍喬遷到了黃金地段的新居,最后卻又回到單身宿舍;原因很簡單,精心策劃的婚戀攻堅戰告吹,王晉偉舍不得自己享受,寧愿把新房做賺取房租的出租屋,自己住回單身宿舍,“一個月收50元管理費,住一年也就是600元,水電暖齊全,卻不另外計費。對于無房戶來說,相當劃算。王晉偉現在又搬回來住了,把自己的新房空出來再租出去,一里一外,他的月收入至少提升了三成。”盡管木訥的王晉偉這筆賬算得不錯,但是在周圍人眼里,買房成功和婚姻失敗正負相抵,王晉偉就把自己活成了一個另類。
不知怎么的,我想起魯迅先生《在酒樓上》寫到的呂緯甫,那是差不多距今天一百年前的一個小知識分子,面對唯一可信賴的朋友回望自己的人生軌跡,自嘲“飛了一個小圈子,便又回來停在原點”,“不過繞了一點小圈子”。我們這位王晉偉,是連自嘲都沒有的。他提著那桶學校免費的純凈水走進單身宿舍,悄然無聲無怨無悔。“出師未捷身先死”,這句比喻用在王晉偉身上,其實并不匹配,恕我詞窮。這場由“我”精心策劃、請“我”出山做大媒的攻堅戰,從始至終就是媒人的一場旁敲側擊,主人公壓根就不在場缺席。小說結尾,“我”上演“一個人的戰爭”宣告失敗,熱心仗義的敘述者由憤憤不平歸于意興闌珊:“不平誰呢?不平啥呢?切莫多情自憂擾,別人的生活,永遠是別人的生活。”
曾幾何時,文學評論希望作家給出問題原因進而給筆下的人物指明出路。今天人們終于清楚,對于“非文學”的現實生活,作家所能做的也只是用文學方式呈現出來。作者無奈著人物的無奈,接受著他們的“無疾而終”。他用文學的方式呈現著他們非文學的生存,你會發現,劉寧是站在“王晉偉們”的邏輯中推己及人,背后秉持的是“人物本位主義”。
這讓我又想起張愛玲在《封鎖》的結尾,作者兀自發問那只爬了一半又縮回巢里的烏殼蟲,“整天爬來爬去,很少有思想的時間吧?然而思想畢竟是痛苦的。”人性的不徹底、靈魂的灰暗和乏味,這就是“秋天到太原來看雨”的尷尬。那首歌或許本該是我們的主人公來哼唱,然而——那是不可能的。為什么呢,顧城的《感覺》活畫出這位主人公的內心:“天是灰色的/路是灰色的/樓是灰色的/雨是灰色的”,你會覺得,精神世界“在一片死灰中”的人,怕是沒有歌聲的吧。
這個影子一樣灰色的人物讓我聯想到他的“近親”。將近一個世紀前,葉圣陶筆下那一群小鎮灰色人物系列;契訶夫小說里走在兩條路上的年輕知識分子:“一條是苦悶和凋萎,另一條是庸俗和墮落”(汝龍譯《契訶夫小說選集·出診集》,上海譯文出版社1982);果戈理筆下“幾乎無事的悲劇”(《魯迅全集·且介亭雜文二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人物,他們并未遠去,穿越時空在劉寧的小說中依然存活著。
這是逼真的白描,寫實如同“非虛構”的一篇小說。仿佛就是你我身邊的張三李四。唯其如此,這樣無趣寡淡的生活,卻催生出極具文學性的“熟悉的陌生人”,這是劉寧用心觀察所得,卻又不僅僅停留于觀察,無奈焦躁悲憫審視的復雜意味糾纏其中,這樣的小說并不好寫。普希金評價果戈理的小說是“含淚的微笑”,如今我們不妨移植到劉寧的這篇小說當中。作者看似油腔滑調冷嘲熱諷半真半假,卻是“用平常事,平常話,深刻地顯出“小知識分子的“無聊生活”。無可奈何的悲憤,“在玩世的衣裳下,有含譏的輕妙的小品,”裹起來聊且當作“看破”,如魯迅先生所言,“這些極平常的,或者簡直近于沒有事情的悲劇,正如無聲的語言一樣,非由詩人畫出它的形象來,是很不容易覺察的。然而人們滅亡于英雄的特別的悲劇者少,消磨于極平常的,或者簡直近于沒有事情的悲劇者卻多。”(《魯迅全集·且介亭雜文二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魯迅先生能看懂那含淚的微笑,卻希望人類的表情包能被“健康的笑”替代。而長出這樣的笑容,需要的是博大的胸襟,強健的體魄,“榨出皮袍下面藏著的‘小和無聊。我以為,這才是《秋季到太原來看雨》的“亮點”所在。
這篇小說還是讀者熟悉的口風,我曾說過,讀劉寧的小說是一件令人振奮且愉悅的事。如果說人有三寸不爛之舌,劉寧的筆頭也可稱“三寸不爛”,敘事語言的把控拿捏,把人與事編織得風生水起,寫景也常如靈光乍現精彩紛呈。劉寧用個人化的語言寫雞毛蒜皮和小人物的難解之謎,有一種陌生化的新鮮可讀。他的小說擅用比喻,大多鮮活不俗,讓人意外讓人莞爾,充滿了奇思異智。只不過,《秋季到太原來看雨》調侃之外多了一絲苦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