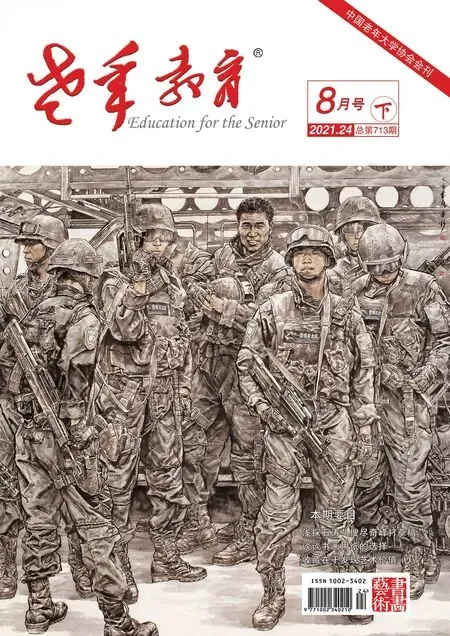愛在丹青
□ 如 一
自虞至清,閨閣耽畫,代不乏人。而夫婦唱和,翰墨風流者,自宋有趙德甫、李易安;元則趙子昂、管仲姬;明有陳老蓮、胡華鬘,錢牧齋、柳如是;清則羅兩峰、方婉儀,華新羅、方白蓮。近世則以梅影書屋吳湖帆、潘靜淑夫婦金石丹青唱和為最,謂之人間風雅無雙;除此之外,還有劉海粟和夏伊喬、謝稚柳和陳佩秋、陳少梅和馮忠蓮、張伯駒和潘素、黃苗子和郁風,等等。從他們生命旅程的點滴中,我們能感受到融入他們彼此骨子里的丹青之愛。
吳湖帆和潘靜淑:綠遍池塘草
吳湖帆是20世紀中國畫壇集繪畫、鑒藏于一身的大家,妻子潘靜淑是位富家千金,知書達理。潘靜淑既無金玉紈綺之好,又不喜應酬,從小在深深庭院中接受傳統的淑女教育,讀書習字,吟詩作畫。在吳湖帆7歲、潘靜淑5歲時,二人定下娃娃親。潘靜淑雖長相并不出色,但卻是吳湖帆一生的摯愛。
吳湖帆尤好蓄書畫,潘靜淑亦喜歡作畫,他們徜徉于吳家深深庭院中。有時同賞一幅古畫;有時摩挲著博古架上的古代青銅器皿;有時共讀一篇詩歌,沉浸在詩意的氛圍里;有時共同完成一幅畫作,將其視作兩人愛情的表征;有時為了吳湖帆購買一幅心儀已久的古畫,潘靜淑寧愿為其舍去珍愛的首飾去湊錢。
1939年6月29日,潘靜淑突患腹疾,遽然不治,三日而歿。潘靜淑的離去,使吳湖帆傷痛之極。他在《故妻潘夫人墓狀》中寫道:“嗚呼痛哉!金鏤長埋,佳城永閉,我心碎矣,君靈知否?”為表奉倩傷神之意,他從此更名為“倩”,自號“倩庵”。后又請篆刻家陳巨來為潘靜淑刻名章10余方,鈐于其遺物之上,以示悼念。潘氏下葬于滬西虹橋公墓,吳湖帆特請葉恭綽題寫“梁景佳城”四字。極度悲痛中的吳湖帆,先后填詞數十首,哀婉凄約,潘氏的遺物幾乎被他寫遍。他還毫不猶豫地賣掉自己心愛的1000余方漢印,將所得的4000元出版《梅景書屋畫集》,以表達對亡妻的無盡哀思。
劉海粟和夏伊喬:滄海伊人
夏伊喬早年隨父母移居印度尼西亞,家境殷實,自幼學畫。1943年,她放棄優渥的生活,在劉海粟最為困難的時候來到他身邊。夏伊喬的出現,給劉海粟的生活增加了新能量。
夏伊喬把自己大半生的精力都花在劉海粟身上,在照料好海老之余,她才見縫插針地拿起畫筆作畫。劉海粟畫名在外,常常被邀請去外地參加活動,其間自會有人為其整好桌子、鋪好紙筆。而夏伊喬卻沒有這樣的待遇,在很多人眼中,她只是陪同而來的“劉海粟夫人”,但她卻毫無怨言。其實,夏伊喬擅畫山水、花鳥,作品秀逸清麗,遒勁瀟灑。她由衷地喜愛著繪畫,當劉海粟在畫桌上揮灑時,她便在旁邊創作自己的作品。
20世紀八九十年代,夏伊喬陪伴劉海粟暢游神州,二人留下許多作品。2016年,上海中國畫院展出許多1956年畫院籌備之初未曾公布的史料,其中就包括當時擬邀請為畫院畫師的一批有名望的藝術家名單,在吳湖帆提名的“甲字畫家廿五人”中就有劉海粟和夏伊喬的名字。此時,夏伊喬作為畫家的身份才公布于世。可見,為了劉海粟,夏伊喬放棄了自己的愛好和追求,一生無怨無悔地追隨在他身邊。
黃苗子和郁風:亦師亦友“雙子星”
黃苗子和郁風可謂書畫合璧,但他們卻自稱是“行走在藝術世界里的小票友”。20世紀三十年代,黃苗子和郁風在上海第一次見面。在黃苗子的記憶里是在葉淺予家中見的面,而郁風則記得是由叔叔郁達夫帶著她在霞飛路的漫畫俱樂部相識,但這已經不重要了。
黃苗子說:“我這一輩子得到最大的益處就是朋友。我原來只是中學畢業,沒有什么學歷,都是靠長輩和朋友的幫助,才有了一些學問。”1957年,為研究唐代畫圣吳道子,黃苗子特地去廣州中山大學拜訪陳寅恪先生。當時,陳先生眼睛已經看不清楚,要跟著一條白線去課堂。黃苗子記得:“陳老的頭腦十分清醒,博聞強識。他指導我,讓我查《新唐書》第幾卷第幾頁一些有關唐代壁畫的材料,《舊唐書》第幾卷第幾頁也有——都是如數家珍。”
其實,除了長輩和朋友在事業上的幫助,郁風才是他藝術上的良師益友。郁風曾笑著道:“我經常是他的第一個批評者,他寫了字,我其實不懂,但我從藝術角度、直覺、構圖等方面,給予不客氣的評價。他有時候聽,有時候也不聽。我的畫,他也批評。后來,他總說自己畫畫是跟我學的,其實不是。我們先后在澳大利亞生活了10年,那里地廣人稀,住的房子很大。我們也有一個很大的工作室,有三個工作臺,中間一個大桌子,我畫完以后的顏料都不用收起來,他寫完字就‘偷用’我的顏料畫畫。”這對亦師亦友的“雙子星”就像一對神仙眷侶,羨煞旁人。

《萱草》黃苗子 郁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