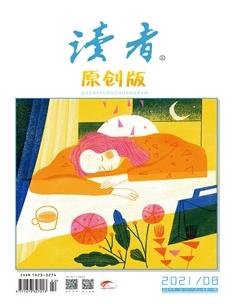到小城去
謝鶴醒

一
最近幾年,我的旅行計劃常不被他人理解—與那些豐富多彩、變幻萬千的大城市相比,我更喜歡小城。它們更接近我的喜好—低調、緘默,內在有力量;同時也足夠陌生,與自己過往的人生經驗毫不沾邊。
這樣才格外令人興奮,幻想自己身處賈樟柯導演的長鏡頭里,迎面而來的一切都是驚喜,路過的每一處細節都值得捕捉。
在小城,連鎖品牌剛起步,“網紅經濟”尚未成熟,一些在都市練就的生活經驗很可能毫無用武之地,需要重新建構一種短暫的生存方式,這常常令我有種“穿越”的錯覺。但旅途不是生存,本就不必追求高效率、模式化,“慢”反而讓我重溫了記憶中生活的本真味道。
在大城市過慣了匆促喧鬧的日子,深深覺得小城獨有的“降噪”功能,令人心動不已。
二
隔三岔五到小城逛逛,最值得“點贊”的,就是能明顯感受到國家的發展進步。
2012年我從成都去宜賓,普快列車整整走了7個小時。三江匯流之處,空氣氤氳繚繞,鮮有游人,滿城飄著五糧液酒糟那獨特的味道……我氣鼓鼓地又坐了7個小時車回到成都。
2020年夏,好友提議去宜賓過周末。這次,我們從成都東站坐城際列車,到宜賓只用了一個多小時。合江門廣場邊,放暑假的少年三五成群在練習滑板,一片生機;翠屏山公園修建了蜿蜒盤旋的空中步道,給游覽增添了不少樂趣;五糧液工業園區宏偉大氣,聽說為了環保,酒糟已經被加工成飼料,走在宜賓的大街小巷,再也難覓曾經那若隱若現的味道了。
2018年的國慶假期,我一個人去亳州。先從西安坐了兩個小時的高鐵到鄭州,又換乘普快列車,晃蕩了4個多小時才抵達。舟車勞頓令我煩躁不已,卻意外發現恰逢當地“文化旅游年”活動,所有星級景點門票一律10元,于是開心地在小城里逛了兩天。無論是古跡遺址、中藥文化,還是城市規劃之類,都讓我驚喜連連。翻閱城市宣傳冊,內容之翔實、印刷之精美、選題之新穎讓我忍不住感嘆。合上書頁,多希望這里的對外交通能夠再便捷些,讓更多外省游客慕名而來。
如今,不過兩年多光景,從西安到亳州的高鐵已經開通,單程不過三個半小時。
我以前總以為河北是旅游業“洼地”,直到去了邯鄲,被一家區域性連鎖餐廳“小放牛”吸引。第一次嘗試就欣喜萬分:無論是菜品特色、味道,還是環境、服務質量,都不輸大城市里的知名餐飲品牌;最人性化的是所有菜都可以點半份,對于我這種“獨行俠”十分友好。買單時忍不住問店員哪里還有分店,得知并未走出本省,不禁遺憾……
前不久,偶然看到“小放牛”將新店開到北京的新聞,官方宣傳海報上巨大的“我們進京啦”,展示滿滿的喜悅和自豪—果然,是金子總會發光。
三
因為職業關系,我格外關注城鄉的發展變化。在區域發展不均衡局面日漸緩解之時,互聯網語境下的多種可能給年輕人帶來了更多元化的選擇與思考:身邊越來越多的朋友回到家鄉建設小城。
飛速發展難免帶來城市的同質化,但這里面也有非常珍貴的一面:我們不必時刻覬覦北上廣深,不必非要奔向新一線城市、省會城市。一位研究生室友回到家鄉張家口做了教師,另一位室友考了德陽某地的公務員,我們仨憧憬著在北京冬奧會之前相聚張家口,結伴兒去崇禮滑雪。當初相熟的生科院高才生,有的考了家鄉的事業編,現在兼職賣眼鏡;有的去了四川某地當獸醫,業余時間研制起了獨家秘方的牦牛肉干……
他們中有些是放不下故鄉的牽掛,有些是滿腔熱血要去陌生小城揮灑,但無一例外都是昂揚的、幸福的。如果用大城市的奮斗心態在小城市生活,會發覺,夢想的實現與地域的關聯越來越淡。
而我,著迷于用腳步丈量廣闊的祖國大地,解鎖一座又一座風格各異的小城。
想起有一次我心血來潮,拖著好友去烏海,坐了一夜綠皮火車,清晨醒來,滿眼荒蕪。沒有人知道,我是因為一句“到沙漠看海”的旅游宣傳語而去的。站在清澈透明的黃河邊,好友忍不住抱怨干燥的空氣令他鼻炎復發,但也不得不承認,走在一望無際的尚未竣工的新建植物園里,看得出這座城市努力轉型的氣魄與決心。
這正是許多小城吸引我的原因—其實城市和人一樣,不是誰生來就有一手好牌。幸福都是奮斗出來的:潛力無窮,絕處逢生。
我當然知道,以過客的姿態看陌生的小城,所有的美好或不堪都容易放大。但我想,城市的魅力正是在于發現—走的地方越多,越能發現自己的淺薄,也越期盼發現更多的精彩角落。